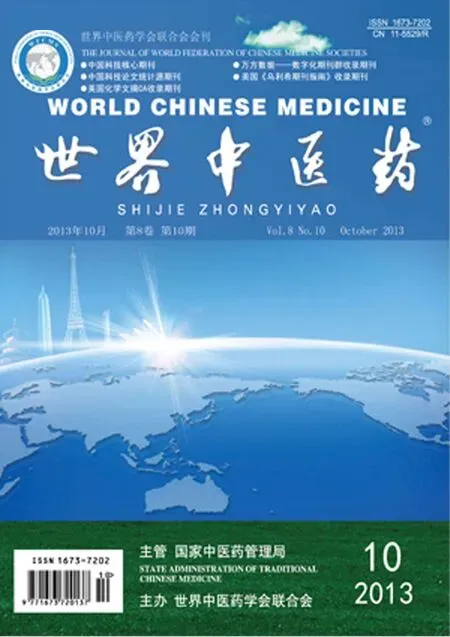淺談周圍血管疾病的中醫辨證內涵
王雁南 陳柏楠
(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周圍血管病科,濟南,250011)
淺談周圍血管疾病的中醫辨證內涵
王雁南 陳柏楠
(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周圍血管病科,濟南,250011)
我國周圍血管疾病專業是以50年代中西醫結合辨證治療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為開端而發展起來的,在古代文獻中沒有系統記載,其專業發展歷程是在現代醫學環境下,創新應用中醫理論和中醫西結合的最佳范例。筆者根據臨床工作經驗,總結了現代周圍血管疾病的整體辨證中包含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整體辨證與局部辨證相結合、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辨病機論治四項具體內容,是對傳統中醫整體辨證內涵的延伸和拓展,對充實現代周圍血管疾病的理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周圍血管疾病;中西醫結合療法;辨證
中西醫結合治療周圍血管疾病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以辨證治療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為開端,各地醫師逐步積累臨床經驗,病種不斷擴大,發展至今天的周圍血管疾病專業,并建立了中醫、中西醫結合的專業學術團體。現代的周圍血管疾病大多在古代文獻中沒有系統記載,是隨著西醫學病理生理的發展,在明確疾病診斷后,由現代中醫醫師在遵循中醫學整體辨證理論的基礎之上,建立起周圍血管疾病的中醫辨證體系,是在現代醫學環境下,創新應用中醫理論和中醫西結合的最佳范例。隨著現代血管腔內技術的快速發展,需要我們不斷調整、完善中醫整體辨證論治思路,提高治療水平。筆者就近年來的臨床工作經驗,對周圍血管疾病的整體辨證談幾點自己的體會。
1 辨病與辨證相結合
“病”即疾病,是包括病因、病機、轉歸預后的完整病理過程。“辨病”是對疾病總的特點和基本矛盾的概括,具有“整體性”和“特異性”的特征。中醫和西醫均有“病”的概念。“證”是中醫特有的概念,是對疾病某一階段病因、病位、病性、病勢、病機的綜合性概括,具有“階段性”和“非特異性”的特征。“病”重點在全過程;“證”重點在現階段,辨病與辨證是分別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對疾病進行診斷[1]。實際上,中醫學自古以來就一貫重視辨病與辨證的有機結合,《黃帝內經》時期即確立了辨病論治的原則,并產生辨證論治思想的萌芽;東漢張仲景奠定辨病論治體系下辨證論治的基礎[2-3]。但是周圍血管疾病專業是新興學科,在傳統中醫中沒有確立完整的疾病體系,僅作為其他疾病的合并癥狀有零星記載和相應的辨證治療,因此該學科自建立之初便是西醫辨病和中醫辨證相結合,相伴發展成長。所以,我們在這里講的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指的是西醫的辨病和中醫的辨證相結合。在臨床工作中,既要明確疾病的西醫診斷,又不忽視中醫學的辨證,以病為綱,先辨病,后辨證,病證合參。辨明疾病,洞悉疾病的病理機制、所處的病理階段,有利于準確掌握疾病的病情和轉歸。辨證,則是中醫治療疾病的基本方法,通過詳細了解病史、癥狀和體征,運用中醫辨證方法,明確疾病的中醫病因、病機、病勢、病位,才能制定相應的治療原則,選擇恰當的方藥。周圍血管疾病的中醫病名多以癥狀命名,如脫疽、脈痹、股腫等,而西醫同類疾病中往往會出現類似的癥狀,因此單純以中醫癥狀命名很難區分不同病理改變的疾病。例如同為中醫的“脫疽”,在《靈樞·癰疽》中記載為:“發于足指,……其狀赤黑,死之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則死矣。”西醫學中的血栓閉塞性脈管炎、閉塞性動脈硬化癥、糖尿病壞疽、壞死性血管炎等疾病均可出現相同癥狀,但其病理改變則有著根本的區別,是完全不同的疾病,有著截然不同的治療原則和預后。因此,現代臨床中應當先辨西醫的病,再辨中醫的證,二者結合可以取長補短,準確掌握疾病的發病原因、病理變化和轉歸,同時重視中醫辨證,既有整體觀念、動態觀念,又不忽視局部變化,充實診斷的完整性和治療的全面性。
2 整體辨證與局部辨證相結合
整體辨證思想是中醫診斷疾病的基本原則,旨在通過綜合分析望、聞、問、切四診獲取的資料,對疾病某一階段的病機、病位、病勢作出判斷,反映了人體的整體狀態,是辨證治療的基礎。局部辨證通常是指圍繞病變部位進行辨證的方法,是外科常用的辨證方法。當局部病變表現突出,或全身癥狀不典型時,通過局部辨證判斷病變的病因、病機、性質,更能體現專科特點。周圍血管疾病的整體辨證和局部辨證結合包含兩個層次,其一,全身狀況的整體辨證和肢體局部癥狀的局部辨證相結合。周圍血管疾病多有明顯的局部癥狀、體征,采集局部的四診信息非常重要[4],通過望、聞、問、切,明確局部病變的病位、形態、寒熱、虛實,結合整體辨證,重視外科疾病辨膿、辨腫、辨潰瘍、辨痛、辨麻木等方法的運用,才能準確把握患者在某個階段出現的局部癥狀和全身反應的主次關系,辨明陰陽、真假和消長轉化,綜合判斷疾病的性質、輕重和預后。例如“臁瘡”,因多發于小腿臁部而得名,往往經久難愈和繼發感染。臨床中需要非常重視辨別潰瘍局部的形態、深度、肉芽色澤、滲液性質及瘡周情況,并結合患者全身狀況,整體與局部辨證并重,辨明患者的陰陽氣血盛衰,制定相應的治療原則,進行辨證治療,合理應用外治療法。其二,病灶局部與病灶肢體的整體相結合辨證。這類情況多發生在有潰瘍或壞疽的肢體,尤其在糖尿病肢體動脈閉塞癥中常見。往往一方面存在瘡面肉芽灰白、水腫等氣血虧虛的征象,另一方面又同時存在瘡周組織紅腫、疼痛、皮溫高等實熱表現。此時需要重視病灶局部辨證和包含病灶周圍環境在內的整體辨證相結合,補正虛、祛邪實,標本兼治,才能取得比較理想的臨床效果。
3 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之際,是歷代醫家通過自身醫療實踐所總結的、能夠指導臨床規律與法則的集合[5]。受古時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和限制,當時的醫家在對人體組織結構、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進行力所能及的觀察推測和自身體悟的同時,對人類生活的周圍事物進行了廣泛的觀察和分析,并將觀察結果與人的生理、病理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藏象學說及病因病機學說等的形成,莫不是注重宏觀觀察的結果。通過宏觀觀察,古代醫家能夠總體地動態地觀察和把握人體的生命活動規律,“觀其外以測其內”;并把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包括人類都看成是由無形可見的“氣”及其運動構成的。中醫學正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中建立了自己的生命觀、疾病觀,并依據宏觀整體理論指導養生延壽和防病治病[6]。“微觀辨證”的概念最早由沈自尹于1986年在《微觀辨證和辨證微觀化》一文中明確提出。微觀辨證是指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從細胞、分子及基因等微觀層次上辨別證,其吸收了現代醫學科技的先進技術,深化和擴展了宏觀四診,逐步形成微觀辨證學[7]。微觀辨證在證的本質研究、證的模型構建、證的微觀分類、辨證標準、辨證分型甚至辨證施治中均具有重要作用[8];同時也是宏觀辨證(四診)的必要和有益的補充,它豐富了中醫診斷學的內涵,改變了無證可辨的窘境[9]。隨著科技的發達,人類借助現代儀器及檢測方法對肉眼無法識別的細胞、分子、基因等進行觀察,是對宏觀觀察的延伸,可以彌補宏觀辨證證據的不足,擴大醫生觀察的深度和廣度。臨床中應當在遵循中醫基礎理論的前提下,逐步將這些微觀證據納入中醫辨證體系中,擴充“證”的物質內涵[10],實現“宏觀辨證”與“微觀辨證”相結合,可以提高疾病的早期診斷水平,提高用藥的針對性和準確性[11]。但是微觀辨證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微觀辨證并不是簡單地追求用某個或某組微觀指標與“證”劃上等號。任何一個微觀指標決不可能全面闡釋“證”的本質,但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疾病證候的變化趨勢[12-13]。所以實行“微觀辨證”必須強調多指標合參、同步觀察,這樣才能對各種“證”的認識更趨全面,減少片面性,才能使“微觀辨證”研究不斷深化,符合現代中醫的發展方向。
4 辨病機論治
病機是研究疾病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機理并揭示其規律的中醫基礎理論分支學科。病機理論源于《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的“病機十九條”奠定了臟腑病機、六氣病機理論基礎[14]。盡管臨床疾病種類繁多,臨床征象錯綜復雜,各個疾病、各個癥狀都有其各自的病機,但都離不開邪正盛衰、陰陽失調、氣血失常、經絡和臟腑功能紊亂等病機變化的一般規律。辨證論治被認為是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現代臨床中也多遵循古法,四診合參,通過分析、綜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為某種性質的“證”[15]。然后根據“證”來施治,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筆者認為,辨證的過程中除了辨明當下的“證”之外,還要辨明病機的來龍去脈,即明確正邪、氣血、陰陽及臟腑功能是如何變化、發展到現在的“證”,其預后又可能是怎樣的變化趨勢,針對病機,重視氣血陰陽、寒熱虛實的動態變化,從而在施治時加以兼顧,真正地做到“上工治未病”。比如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急性期,常常應用深靜脈置管溶栓的治療方法,臨床療效顯著,從中醫的辨證角度看,該方法屬于祛邪法,應用現代介入技術直接祛除瘀血,然則祛邪易傷正,正虛則易戀邪,因此,術后的治療除了活血化瘀的基本原則之外,還需要注意顧護正氣,調理陰陽氣血平衡,預防血栓復發。
總之,中醫學的整體觀念內涵博大精深,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應當拓展和充實“證”所包含的內容,不斷延伸和發展整體辨證的內涵,更快地融合現代科技成果為己所用,并不斷去。
[1]董正華.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是《傷寒論》的基本診斷模式[J].陜西中醫學院學報,2005,28(6):5-7.
[2]仝小林.論癥、證、病結合辨治模式在臨床中的應用[J].中醫雜志,2010,51(4):300-303.
[3]陳以平.提倡辨病論治,力主微觀辨證[J].中國中西醫結腎病雜志,2012,13(5):377-378.
[4]張臻,闕華發.中醫藥內外合治術后合并細菌感染之難愈性創面臨床觀察[J].新中醫,2012,44(1):62-63.
[5]陳曦,張宇鵬,于智敏,等.關于中醫理論體系框架研究的若干思考[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3,19(1):3-6.
[6]孫廣仁.中醫基礎理論[M].2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60 -61.
[7]郭振球.主訴辨治法與微觀辨證及其學科群的和諧發展[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25(3):161-163.
[8]梁文杰,方朝義,丁英鈞,等.實驗診斷學在微觀辨證中的價值評析[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4(32):543-546.
[9]譚碧珠,李德輝,廖銳,等.對無癥狀疾病的辨證論治淺解[J].時珍國醫國藥,2013,23(9):2285-2286.
[10]韋祎,唐漢慶.中醫宏觀辨證的微觀解讀[J].廣西中醫藥,2010,33(2):40-42.
[11]劉明,趙永利.閉塞性動脈硬化癥中醫證型與TASCⅡ分型的相關性[J].中國中西醫結合外科雜志,2012,18(6):563-565.
[12]秦紅松,陳柏楠,李彥州,等.糖尿病肢體動脈閉塞癥股動脈內膜-中膜厚度、血流速度及脈動指數與中醫證型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9,29(8):754-755.
[13]李建鵬,王崢.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辨證分型與血管內皮功能相關性探討[J].遼寧中醫雜志,2011,38(5):915-916.
[14]譚達全.中醫病因病機理論研究方法的再思考[J].湖南中醫雜志,2012,2(1):2-5.
[15]王健.中醫病因病機研究的思路與方法[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2,18(6):581-583.
(2013-05-07收稿)
Thoughts the Connotation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 tiation in Peripheral Vessel Disease
Wang Yannan,Chen Bainan
(Department of Peripheral Vascular,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inan 250011,China)
The study of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was develop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integrative treatment of Buerger in the 1950s in China.Without any record from ancient literature,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of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is the best examples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 theory integrate with western medicine.Based on clinical experience,this article summed up the four parts of overall syndrome inmodern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combina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combination of overall syndrome and partial differentiation;combination ofmacro syndrome and microcosmic syndrome;treatment based on pathomechanism.The four parts ar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connotations of TCM holistic syndrome,aswell asbeing significant in enriching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in themodern theoretical system.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Integrative Medicine;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10.3969/j.issn.1673-7202.2013.10.008
山東省中醫藥科技發展計劃重點項目(編號:2009Z004-2);山東省中醫藥科技發展計劃(編號:2011-081)
陳柏楠,E-mail:drchenbain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