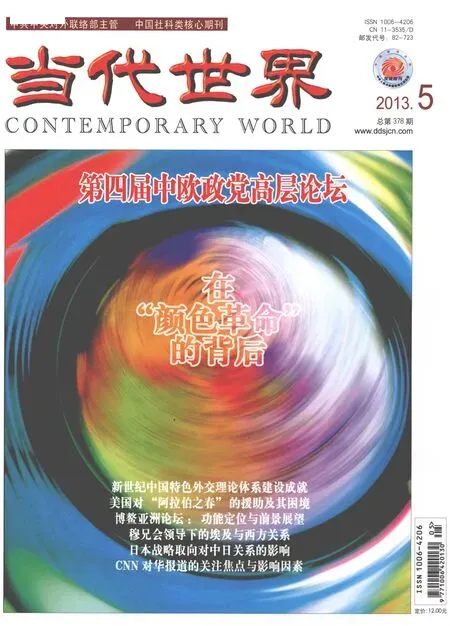日本戰略取向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 時永明/文
目前,中日關系因釣魚島問題陷入僵局。中日兩國在四十多年前可以擱置釣魚島問題,從而實現兩國關系的戰略性突破,四十多年后卻不能如當初設想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反而搞得劍拔弩張,其中問題到底何在?日本首相安倍妄言是因為中國的“反日教育”。然而,縱觀中日建交后四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正是日本在推進“政治大國”戰略中的右翼取向,從各個方面侵蝕和破壞著中日政治關系發展的根基。如今,當日本國內政治生態和亞太戰略環境都進入到一個歷史性關口時,中日之間的各種矛盾終于集中在釣魚島問題上爆發出來。而安倍的政策又恰恰是利用釣魚島問題來實現其國內外政治目標,這使中日關系面臨陷入對抗性格局的危險。
一、日本右翼的“脫戰后”戰略不斷傷害中日友好關系
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由于歷史問題而使得雙邊關系變得復雜敏感。1972年兩國建交時以“友好體制”,而不是利益協調或戰略合作的體制,作為處理兩國關系的基本戰略形態。
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日本擺脫戰后體制的思想也開始膨脹。當時,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后政治總決算”和“政治大國”戰略正是這種思想的代表。由于戰后日本政壇中存在著一批與舊帝國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政治人物,所以日本的“脫戰后”進程,并不是像德國那樣建立在對戰爭罪行的清算上,相反是建立在帶有濃厚的舊帝國思維的“國家主義”的復興上。也正是基于舊帝國的思維方式,日本的“政治大國”戰略,突出強調了要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建立強大的國家軍事力量,依托軍力在國際社會發揮政治作用。為了推進“大國”戰略,右翼勢力不斷地在歷史問題、地區安全戰略以及兩國關系基本準則三個方面沖擊中日關系。
1、右翼勢力希圖借歷史問題重塑國民精神嚴重沖擊中日關系
日本右翼要在國民中重樹國家主義精神,其主要手段就是通過對歷史的翻案和對青少年的教育。中日建交后,首先沖擊兩國政治關系的事件就是教科書問題。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審定的供全國高中和小學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取消了對日本向外侵略等問題的“批判性的記述”,而“沿著使過去日本的作法正當合理化、肯定現狀的方向”進行了修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對日本侵華戰爭歷史的篡改。此后右翼勢力一直在教科書問題上做文章,干擾著中日關系的發展。1997年,右翼學者團體組建了“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推動編纂發行歪曲歷史的教科書。右翼勢力歪曲歷史的行動在日本國內也曾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制。但在日本右翼的大力推動下,近年來“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旗下育鵬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和《新公民教科書》的采用率迅速提高,到2012年時采用率已達到4%。右翼教科書影響的增加,反映了日本社會認知的變化,這對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思想認同所造成的破壞是深遠的。
在試圖通過教育來影響后代的同時,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在不斷地用自己的言行來影響日本社會。他們時常有人跳出來發表一些否認侵略罪行的言論,更重要的是他們長期有組織地積極參拜靖國神社。該神社供奉的是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帝國戰死的軍人。由于神社祭祀著兩千多名二戰戰犯,特別是在1978年該社將14名二戰甲級戰犯“合祀”,因此被東亞國家視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
日本右翼試圖通過悼念所謂為國家犧牲的人來重樹國家主義精神。1981年日本一些議員組成了“大家一起來參拜靖國神社議員聯盟”,要求每年8月15日都要參拜靖國神社。1985年5月,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首次在參拜問題上沖擊中日關系。而后是1996年7月橋本龍太郎以同樣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到了小泉純一郎執政時,參拜更是變成了一種日本右翼與亞洲國家進行意志較量的行為。小泉執政五年,不顧亞洲國家的反對,也無視日本福岡和大阪高等法院宣布其行為違憲的判決,六次參拜靖國神社。
正是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問題上不斷挑戰國際公理,刻意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行為,使中日關系的發展屢受嚴重沖擊。
2、日本政治大國戰略加劇中日戰略猜疑
日本“政治大國”戰略的目標是要在軍事和政治上成為世界一極。但其實現目標的過程卻不得不依賴于美國的支持。因此,冷戰后在日美軍事同盟已經完全不符合時代潮流的情況下,日本卻積極配合美國的霸權戰略,加強日美同盟,并將這種同盟從防御性質轉變為具有對外干預功能的同盟。
日美同盟功能的擴展,使中日關系的矛盾從歷史認識問題向戰略矛盾擴展。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日關系間麻煩不斷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日本的這種國家戰略取向。1995年的《防衛計劃大綱》明確提出了日本的軍事力量要在維護亞太地區穩定上發揮適當作用。1996年4月,日美就安全問題發表了題為“面向21世紀的同盟”的聯合聲明,將日美同盟從防衛日本擴大定義為“亞太地區繁榮穩定的基石”,并特別肯定了日本新《防衛計劃大綱》關于日本軍事力量作用的說法。翌年,日美兩國借當時的朝鮮半島危機簽署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提出了就周邊地區安全進行合作的概念。據此,1999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周邊事態法》,規定在日本周邊有事時,日本要給美軍以后勤支援。雖然該法案沒有對“周邊”的概念進行明確表述,但事實上將解釋權交給了政府,而日本政府不斷有人公開表示“周邊”所含范圍包括臺灣海峽。此后,日本在2004年出臺新《防衛計劃大綱》,明確將臺灣海峽列為日本周邊的不穩定因素,并公開表示對中國增強軍力特別是海軍活動的關切。日本這種以中國為目標,試圖介入臺海問題的防衛政策,加劇了中日之間的戰略猜疑。
3、日本政府公開干預中國內政沖擊中日政治關系
作為所謂“政治大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在外交上積極配合美國的全球民主化戰略,以所謂“人權”為理由,公開干預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1995年“藏獨”集團聯合日本一些反華議員鼓動成立了所謂“思考西藏問題議員聯盟”。該組織在日本多次集會和示威,并在國際上參與支持“藏獨”活動。達賴喇嘛更是接連訪問日本,一些日本政要則頻頻與其見面,明里暗里對其給予支持。近年來,隨著“疆獨”勢力的活躍,日本政客又開始積極介入。2012年4月,在“疆獨”勢力準備于日本舉辦“世界維吾爾人大會”之前一個月,日本部分右翼議員組織了“日本維吾爾國會議員聯盟”,公開有組織地支持“疆獨”活動。日本作為曾經侵略過中國的鄰國,其有系統有組織地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由上可見,正是由于日本右翼勢力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標的時候,不斷從各方面沖擊中日兩國建交時所確定的國家間關系準則,從而使中日兩國在經濟關系日益緊密的同時,政治關系日漸疏遠,戰略隔閡不斷加深。
二、安倍保守主義戰略使中日關系陷入困境
安倍是日本政壇戰后新生代中右翼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他不僅全面繼承傳統的保守理念,并以實現右翼保守勢力的政治理想為自己的執政目標。安倍保守主義戰略更突出之處在于要把日本打造成軍事政治強國的色彩,他的目標就是在國內完成修改憲法和自衛隊軍隊化的建設,在國際上扮演具有領導作用的“大國”角色。雖然,安倍主張用政經分離的方式處理中日關系,但是其極端的右翼主張正使中日關系陷入困境。
首先,安倍的保守政治主張損害中日政治互信的根基。安倍是日本保守勢力的活躍分子。2004年他曾與當時的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文彬組織“考慮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青年議員之會”,自己任事務局長,積極推進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出版的教科書在全國采用。他還是“大家一起來參拜靖國神社議員聯盟”的成員,二次競選時曾以當選后要參拜來標示自己的保守色彩。在否認歷史的問題上,他同樣引人注目。2007年3月,他在日本國會公開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日軍強征慰安婦”,并拒絕就此事道歉,當時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此次重返首相職位,他不僅表示要用“安倍談話”取代日本“反省歷史的三大談話”,甚至公開質疑東京審判結果。

2013年4月25日,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金奎顯(右一)召見日本駐韓大使別所浩郎(左一)抗議日本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關于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論。
安倍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實質上是為完成“修憲強兵”做鋪墊。2006 年首次執政時,安倍就推動通過了規定修憲程序的《國民投票法》,以及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的相關法案。第二次執政,安倍以在任內實現修憲為目標,一上任就開始著手推動修憲程序,有意先對規定修憲提案條件的《憲法》第96條進行修改,為下一步修憲鋪路。而在修憲的內容上,自民黨已在3月14日召開的眾議院憲法審查會上提出將天皇從國家象征改為“國家元首”,以及實行“集體自衛權”。
其次,安倍試圖以“聯美籠亞抑中”的外交戰略來確立日本大國地位。安倍為推動“政治大國”戰略而主要采取兩個策略,一是在美國主導的格局下表現出更多的主動性,二是充分利用中美之間存在的大國競爭。他在首次擔任首相之時就提出所謂“有主張的外交”,試圖把日美同盟由美國主導,改為日美聯合主導,打造一個日美共治的地區安全秩序。他配合美國民主戰略,提出了所謂“價值觀外交”。2006 年安倍政府提出建立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并將此設想定位為外交的“新基軸”。依據這個“新基軸”,安倍試圖建立所謂日美印澳的四國“價值聯盟”,在亞太地區構建針對中國的戰略布局。
安倍再次執政后,利用美國推行的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一則挾美自重,一則試圖通過打壓中國來抬高日本的地位,扮演亞洲領導者的角色。他重提日美印澳四國聯盟,將其命名為“亞洲民主安全菱形”,并針對中國展開亞洲外交。先是派副首相麻生太郎訪問緬甸,與中國展開影響力競爭。而后派外相岸田文雄跑到菲律賓、文萊和澳大利亞等國,拿南海問題說事,公然將“應對中國”說成是各國“共同課題”。最后,他親自出馬訪問越南、泰國、印尼等東盟國家,安全、經濟、價值觀三管齊下,明確表現出針對中國的意圖。這種圍堵外交幾乎推進到日本認為具有戰略價值的一切地方。2013年3月,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訪問日本,在討論兩國海上安全合作時,安倍再次把中國列入目標,他說,“中國的海上活動日益活躍,這是該地區共同的關切事項”。與此同時,他對斯里蘭卡讓日本軍艦利用其港口表示感謝。其試圖在印度洋限制中國海軍活動能力的意圖非常明顯。
第三,安倍利用釣魚島問題推進其政治戰略。安倍是在中日關系因釣魚島問題陷入緊張的背景下再次上臺的。但他選舉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主張在釣魚島問題上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安倍在釣魚島問題上有三大主張,一是中日之間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談判余地”,二是日本應派公務員駐扎釣魚島,三是針對釣魚島強化軍事力量和手段。這三項主張都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安倍上臺后,僅僅在派公務員駐島問題上說到要“暫緩”,并沒有表示出任何通過政治對話解決問題的意愿。他如此做的目的,無非是要將釣魚島問題作為推進其政治戰略的把手。安倍上臺后首先是利用釣魚島問題增加軍費,強化軍事力量。與此同時,他借用所謂美日協防,推動實行“集體自衛權”。而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圍堵中國,也采取的是將中日領土爭議等同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島嶼爭議,等同于海上安全問題的伎倆。
安倍保守主義戰略的最大危險性在于有使中日之間的矛盾向系統性矛盾發展的傾向。過去中日雙邊矛盾一般表現為個案性,通過個案的解決雙邊關系還能繼續正常發展。但如今,安倍把對華強硬作為實現其戰略目標的手段,在安全和政治外交領域針對中國全面地推進自己的戰略布局。這不僅使中日關系陷入僵局,而且有陷入對抗局面的危險。
三、日本“大國戰略”取向危險,也難以走通
安倍具有鮮明右翼傾向的“大國戰略”根基在于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目前,這種右傾化有可能向極端主義發展。2012年的日本眾議院選舉出現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右翼勢力開始在日本政壇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在眾議院480個席位中,自民黨占294席,以石原為首的新興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占54席,僅次于民主黨的57席。競選時,自民黨和維新會基本理念無大差異,二者之間只是比誰更右,誰對中國更強硬。安倍在組閣時選擇公明黨而非維新會,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擔心后者會搶了自民黨的風頭,二是和公明黨合作有利于爭取中間力量和化解反對力量。安倍上任以來,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強硬言詞和措施不斷出籠,支持率卻因此居高不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日本社會的極端情緒有所增長。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右翼實現修改和平憲法目標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對華政策的對抗性也有隨之增加的可能。
事實上,日本“大國戰略”的右傾化道路在國際上難以走通。安倍對華圍堵對抗政策得以實施需要具備一個重大環境因素,即美國的戰略中具有明顯的遏制中國的成分。美國亞太戰略的主要支柱就是日美同盟。為強化日美同盟,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問題上雖表明在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但明確支持日本的管轄權,并通過口頭表述、與日本進行應對釣魚島突發事態的聯合軍事演習等諸多方式,從軍事上對日本給予支持,甚至要制定共同作戰計劃。但即便如此,美國也顯然不愿意被日本牽著鼻子走進與中國對抗的局面。至于其他亞洲國家,雖然隨著中國的崛起,或多或少地對未來地區力量格局變化有些擔憂。但他們也難以接受日美要利用這種擔憂建立一種冷戰式的對華遏制格局。
總而言之,右翼主導下的日本國家戰略發展方向,對中日關系的傷害是全方位的,而且日本試圖利用地區內的一些消極因素來遏制中國,這使中日因釣魚島爭端而走向戰略對峙的風險增大。因此,中國對中日關系要有耐心。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和平發展環境的變化正隨著中國實力的迅速增長而變得愈加復雜。雖然存在著一些對我和平發展不利的消極因素,但積極因素更多。問題在于我們如何化解消極因素,為和平發展增加正能量。中國要想用“合作共贏”的機制取代“制衡穩定”格局,需要更善于運用軟實力。尤其在中日雙邊關系中,應充分了解日本政治文化的特性,注重外交的技巧和藝術,注重“法”、“理”、“利”的均衡運用,爭取化“敵”于無形。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