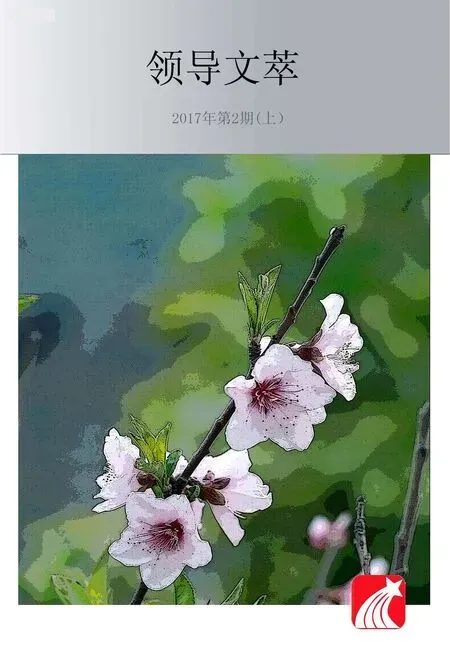看歐洲人喝酒
□邢世嘉

歐洲人對酒的講究如同中國人對美食的講究,絕不可大而化之。威士忌、白蘭地、伏特加、金酒、嬌酒,都各有各的喝法,從不馬虎。比如威士忌,由于釀造過程是將麥芽用火烘烤,繼而發(fā)酵而成,在口感上的特點是濃烈的煙熏味和強烈的酒精味,喝得多了容易上火。所以我們會看到歐洲人在飲用這種酒時,都要在酒杯里加冰塊,一邊晃動一邊喝。晃蕩是為了促使冰塊的溶解,晃蕩也是為了蕩出一種情趣:冰塊在悠悠晃動中撞擊杯壁會發(fā)出非常美妙的聲響,如果在同一個酒吧人人都享用威士忌的話,你就會感受到整個空間都回響著威士忌的交響樂。
歐洲人最精到的是喝白蘭地。其精到之一是選用酒杯,喝這種酒時他們通常選用的是大肚小口的高腳杯,選用這種杯子的緣由據(jù)說在于白蘭地的高貴,而之所以高貴卻又是源于它的醇香。杯口之所以要小就是為了讓酒的香味盡可能長時間地留在杯內(nèi),以便慢慢享受。“大肚”的功用是增加酒與空氣的接觸面,促進香味在杯內(nèi)充分回蕩,讓濃濃的醇香沿著小口向外散發(fā)。喝白蘭地的精到之二是酌酒技法,他們認為白蘭地是一種高檔酒,所以,要很文雅地享用,酌酒時每次只酌少許。
另外,你還會發(fā)現(xiàn),他們在飲用白蘭地的過程中從不會忘記讓手充分接觸杯肚,用手溫使杯內(nèi)的酒有稍許的加熱,使杯中散發(fā)的悠悠醇香在鼻腔縈繞,以便進入銷魂的境界。
說到喝白蘭地,我不禁想起自己在羅馬的一次尷尬經(jīng)歷。那次我和考察團的另一名官員在意籍華人楊小姐的陪同下,在羅馬的一家酒吧喝白蘭地。服務(wù)生款款端來3個高腳酒杯,2個大的,1個稍小的,他將那個稍小的酒杯首先放在楊小姐的面前,然后將兩個大杯分別放在我和我的同事面前。這位同事酷愛喝酒,置身于這種酒吧,酒癮就更加強烈,所以等酒一上桌他就按捺不住,像在中國喝白酒或啤酒一樣拿起瓶子咣咣咣一個人倒了一大杯。這驚人的一幕,我和楊小姐自然是見多不怪,倒是把那位服務(wù)生嚇得目瞪口呆。他哪里知道這是我們中國人豪爽、粗獷的特性在酒文化上的體現(xiàn)。
漫步歐洲街頭,我總是驚訝歐洲的酒館之多。到底有多少,我說不清,總之是比中國的飯館還多,酒館也常常是人滿為患,比中國飯館的生意好。
歐洲人對酒的依戀是超出我們想象的。歐洲人除了上班和睡眠以外,幾乎沒有什么時間可以不喝酒。一日三餐離不開餐前酒、餐中酒、餐后酒,從外面回家,要喝“進門酒”;睡覺要喝“睡前酒”。別看酒吧這么多,那只是歐洲人享受工休和夜生活的一個補充而已。
中國人對酒的依戀就沒有歐洲人那么強烈。對中國人來說,酒的功用更多地體現(xiàn)在人際關(guān)系上,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人際關(guān)系潤滑劑的作用。如果沒有人際關(guān)系的客觀需要,中國人其實是很少喝酒的。在中國的酒桌上之所以會有“牛飲”、“灌”、“吹”的壯觀場面,只是因為“感情深,一口悶”的需要,你千萬不要以為中國人就真的對酒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很多時候,中國人喝酒不是因為自己而是為了別人而喝,醉酒也不是因為自己貪杯而醉,而是為了別人高興而醉。
相比而言,歐洲的酒文化就顯得純潔得多,歐洲人喝酒的動機也顯得純粹得多。不論在什么時候,他們喝酒都是忘情的,自我的。他們喝酒從不去理會別人的情緒,只為自己的情緒而喝,也只為自己的情緒而醉。請人喝酒也不例外。
歐洲人請人進酒吧,一不為客人點酒,二不與客人碰杯,三不為客人埋單。要是在中國如此這般待客,恐怕不會有人受得了。當然,這樣的事在中國也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假如真的發(fā)生了,那這個請客的人一定落得一身“吝嗇”、“自私”、“無情無義”的臭罵。
有朋友問我對中國人和歐洲人喝酒有何感受,我想了想作了這樣的歸納:歐洲人喝酒注重過程,不在乎結(jié)果,只喝感覺,不喝感情;中國人喝酒只在乎結(jié)果(喝翻了沒有,客人滿意沒有),不注重過程,喝的是感情,而不是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