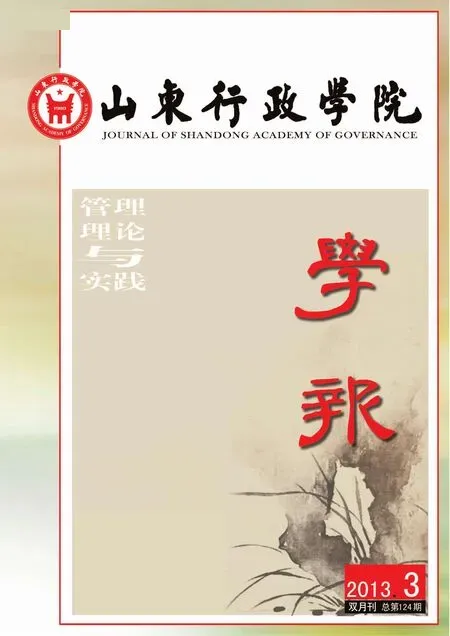女性主義對翻譯的影響
甄 娟
(山東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 經貿系,濟南 250014)
男人和女人,不管是出于有意識也好,無意識也罷,總是在遵守著社會為他們制定的標準。比如說,小男孩就必須要積極進取,要自信且霸氣,而對女孩的要求就必須是被動的,溫順的,謙虛的。人們要去使他們的行動符合這些由社會所決定的性別角色。Millet 指出,女人必須要反抗處于文化中心的權利,即男權制。女性想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建立屬于自己女性的社會習俗,建立女性話語權和女性主義批評。
一、語言形式
(一)父權制和語言
父權制,字面意思是父親的統治,描述了一種由男人掌握權力和婦女被壓迫的社會制度。父權文化在過去的幾千年里一直占主導地位。而且在世界各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形式。然而,它們之間又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是一種對自然和社會的等級秩序的控制,是陽剛之氣對陰柔之氣的控制。正像Lakoff 所描述的一樣,男權社會是male-dominated,male-centered,and male-identified[1]。父權制不僅說明我們的社會功能,還告訴我們它是如何控制女性的。父權制最好的定義是男性的控制,男人擁有權力所以他們可以控制女性。在男權社會中,女性被定位為男人的附屬品。因此,只有更好的了解父權制才能讓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女人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可以拼命打敗男人的力量。
女權主義者們認為,這些父權社會,只是一代一代的把他們認為的女性低于男性、女性不能與男性平等的這種錯誤觀念傳遞了下去。社會一直很武斷地把男性作為標準,顯然是很同意Aristotle 的觀點the female is female by virtue of a certain lack of qualities[2],或者支持St.Thomas Aquinas的看法all women are simply imperfect men.而有些人仍然相信Freud 是正確的,他認為,female sexuality is based on a lack of a penis,the male sexual organ[3]
雖然在一個層面上,我們可以支持或反駁“男尊女卑”的神話,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它在左右著我們的行為,給社會以限制,而這一點我們可能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的世界可以分為減去男性或加上男性,在這種潛規則之下,我們已經看到了父權秩序的構建。我們了解了男權秩序,然后我們給它提供物質,幫助它成為現實。然而我們中的一些人,決定停下來,我們不想再給男權秩序提供養料,成為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那就是給予他們男權的優勢。我們已經開始對世界進行重新分類,制定不同于以往的規則,這種規則不是建立在只承認男性人的屬性,而女性處于否定范疇這種假定基礎之上。
每一天,我們都在構建我們生活的世界。為了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有意義,我們對事件進行挑選,模仿和闡釋,很少有人去懷疑這些任意選擇的規則。我們對顯示進行構建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語言。語言是我們對世界進行分類和排序的手段,更是我們操縱現實的工具。在語言的結構和使用中,我們把世界變成現實;如果它本質上是不準確的,我們就被誤導了。如果在語言系統之下的規則,我們的象征秩序是無效的,那么,我們每天都被騙了。然而,規則的意義,是語言的一部分,不是自然形成的,他們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在等待著被人類發現。然而,與此相反,任何事情在發現之前,都可以被創造出來。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參考框架,沒有秩序,沒有進行系統的解釋和理解的可能。然而,這些規則一旦制定,不管制定它們時有任何誤解,都能夠自我確定和自我維持。雖然在一開始,很難確定在這些規則建設過程中,發生作用的力量是否是準確和有道理的,但是我們卻可以去分析我們當代語言的分類系統,并且猜測起源。而且還能夠分析這些規則在我們世界觀形成過程中發生至關重要作用的原因。
在語言的操作當中,有一個語義規則,那就是男性標準。雖然一開始,在對世界中的物體和事件進行分類時顯得不太重要,可是越仔細研究越能夠發現這是一個最普遍的規則。當在這條規則的操作之下,對世界進行分類時,我們就需要在這個前提下分類了,即男性的標準。當只有這一個標準時,那么那些不符合這個標準的,就出現了類別的偏差。因此,我們的基本分類方案不是把人類分成平等的兩部分,而是要么加上男性,要么減去男性。在最基本的意義的層面上,女性的地位來自于男性的地位。
(二)女性語言
Deborah Cameron 的可讀性比較高的關于女權主義者對語言的看法:
The radical feminist view,then,is of women who live and speak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man-made symbolic universe.They must cope with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the linguistically validated male world view and their own experience,which cannot be expressed in male language.Indeed,since language determines reality,women may be alienated not only from langue but also from the female experience it fails to encode[4].
由于社會對婦女的態度在最近幾年發生了變化,在許多語言中,語言也正在發生著變化,反映了女權主義運動和認識的不斷提高。婦女試圖尋找一種新的語言和新的文學形式,用來反映和回應他們的現實。他們開始批評和改變現有的語言。因此,它可能會呈現有用的信息,而不是壓迫婦女。例如,英語男性優先的后綴man 放到詞尾構成復合詞在最近已經受到相當多的批評,因其沒有參考對女性的尊重。在一個機構或會議上,當介紹女性主席時,把她介紹成了“chairman”,這會讓人覺得被冒犯了。這方面的關注,導致在英語中移除了帶有歷史歧視意義的英語形式,代之以不分性別的詞匯。同時,一些新的術語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術語。例如,他們使用“people”,“police safety officer”,“chair”,“sales representative”來代替“mankind”,“policeman”,“chairman”,“salesman”。
女權主義者提出了不同的方式,通過使用一些能夠避免消極態度和對女性的刻板印象的術語和短語,使他們的言語少受到歧視。無論這樣的建議是否被廣泛采用,它們對提高婦女地位,消除女性刻板印象,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這些建議肯定有象征性的價值。但是,改變重男輕女的隱含歧視女性的語言需要所有的語言使用者的努力。
二、社會刻板印象
在很長一段時間,翻譯一直比原作位置更低。根據“圣經”,上帝先創造了亞當,然后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在世界范圍內,男性比女性來得更早,就像原作和翻譯之間的關系一樣。翻譯是在原作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這就使得翻譯作品處于低級位置上。大家都知道,未經作者同意的情況下,出版翻譯作品是不合法的。在宣布翻譯誕生之前,必須保證先簽合同,使親子關系明確。這種法律過程的根本原因是,寫作一直被認為是原始的和有陽剛之氣的,而翻譯是衍生的和女性的。這是一個關于在家庭和社會中的權力配置的性別的表達的范例。
正如女權主義者對不同學科的研究表明,生產和再生產工作之間的對立構成了文化價值觀的工作方式。對于這么長的時間內,人們一直在使用性別隱喻來描述翻譯。婦女,翻譯人員和翻譯在各自的結構系統中都被放在歧視的和邊緣化的位置。甚至英語翻譯John Florio 總結說:所有的翻譯必須是有缺陷的,所以他們是女性的。
即使是在美國的版權法,例如,翻譯被認為是衍生性的工作,像是音樂表演,而作者是作曲家。當強調寫作和翻譯的重要性,性別偏見沒有消失。這種狀況換醒了的女權主義者的社會性別意識。Jacques Derrida 認為,翻譯既是原始的,又是次要的。寫作和翻譯是互相依存的。有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翻譯在塑造文本和定義文學和文化傳統方面擁有巨大的力量。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區分和批評那些貶低女性翻譯家和翻譯作品的觀點和成見,同時探討原因和副作用,以進一步攻擊內部的性別和翻譯歧視的系統。
三、政治語言與翻譯
在20 世紀60年代后期,社會運動和婦女組織正在進行中。在20 世紀70年代,成千上萬的婦女參加了全國婦女組織,更有數百萬人為了支持經濟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結束各種基于性別歧視的形式加入進來。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婦女被爭取平等機會的目標所吸引?答案之一是女性的性別意識上升。毫無疑問,激進主義改變國家的政治氣候,使婦女意識到他們的地位很低。毫無疑問,由激進派婦女在政治運動中所獲得的經驗為他們提供了組織戰略,這使得她們在吸引其他婦女參加到她們的事業中時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女權主義者的巨大努力,目前翻譯已成為在文學理論中的非常大的力量。婦女運動代表的不僅是把性別問題引入到文學中,還是一種政治趨勢。從外部來看,它對性別不平等這一社會事實起到很大的影響。通過政治改革和文學媒介,一定能夠實現這種文字和政治運動的目的。換句話說,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實現女權主義運動的目的,而翻譯也會對政治起到幫助。
翻譯家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而女性翻譯家生活在至少三種文化之間,這第三種就是指的父權制。從女權主義的角度看,性別歧視是一個沒有性別差異,但有性別層次的問題。這是一個男權至上,女性服從的問題。女權主義者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在存在差異方面是平等的,但是在權利方面卻是不平等的。婦女的政治條件與根本意義上的差異是沒有關系的。
女權主義者試圖通過語言和翻譯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他們看來,語言不僅是表達意思的工具,還是協調各種社會關系的手段,包括最簡單的個人關系和最復雜的政治關系。重男輕女的語言不僅限制了女性表達經驗,也損害了她們的尊嚴、活動和生產率。所以,女權主義者提出與女性地位有關的語言改革。例如女權主義者還開始轉向對圣經的翻譯。她們從女性的視角去解釋和翻譯,以使女性獲得在基督教的一個更高的位置。這對女性翻譯人員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
人們認為翻譯家們在他們的作品中不會保留政治的痕跡。但是,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的翻譯或語言都會或多或少的反應政治和社會事實。De Lotbiniere·Harwood 指出女性的翻譯是一種政治行為,是婦女團結的行為。女權主義翻譯者往往會把她們的意圖與她們女性的身份糾纏在一起。在女權主義者看來,她們不僅需要指出性別歧視的問題,還需要通過女權主義者的干預去解決這個問題。將性別視為生產文本的一個重要因素,使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的集中在政治意識上。
翻譯是一項政治活動。也就是說,翻譯一直是女性寫作的手段和培訓。它給女性提供了參加政治活動的方法,例如,攻擊奴隸制度。通過翻譯,婦女形成了一個交流的網絡,進一步為自己的政治議程服務。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翻譯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信念。
四、結語
翻譯和性別結合在一起并不是巧合。女性主義翻譯對翻譯理論存在很多靈感。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側重于個人的興趣和需要,特別是女性的興趣和需要。婦女運動不僅將性別意識帶入到翻譯研究中,而且對人們在社會刻板印象,語言形式,語言與政治翻譯,譯者的身份等方面的觀念轉變作出了貢獻。
[1]Lakoff,Robinson.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5.
[2]Aristotle,Translator Bywater Ingram.Aritotle on the art of poetry [M].University of Michigan:Clarendon Press,1920.
[3]Bressler,Charles E.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M].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ntice Hall,1999.
[4]Cameron,Deborah.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M].University of Michigan:Palgrave Macmillan press,1992.
[5]Millett,Kate.Sexual politcs[M].Americ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
[6]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