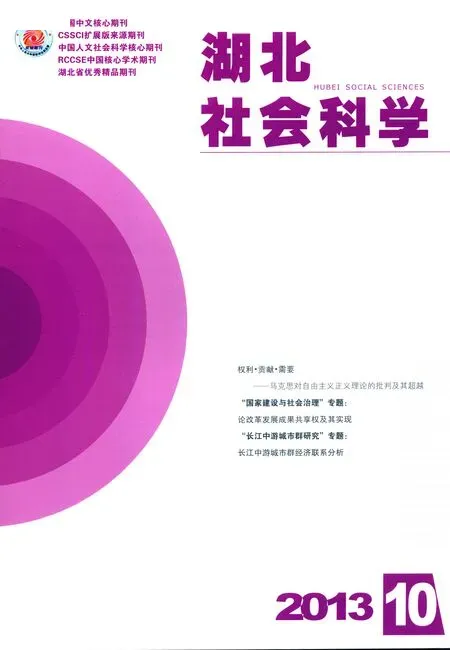權利·貢獻·需要——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批判及其超越
葛水林
(1.南通大學管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2.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 200235)
正義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早在古希臘,柏拉圖就把正義視作最重要和最必要的事情,認為理想的國家就是一個正義的國家。羅爾斯的《正義論》一書更是將正義視為人類社會的首要價值。①在《正義論》的首頁,羅爾斯明確宣稱“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參見[美]約翰·羅爾斯著《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然而,自古以來,人們對正義內涵及其本質的理解就見仁見智:有從分工的角度理解正義,認為正義就是每個人做符合自己本性的事,而不干涉他人;②如在柏拉圖看來,正義的城邦就在于“生產者、護國者、統治者”三者能夠“各司其職,互不僭越”。有從應得的角度主張正義就是“給其所應得”,查士丁尼在《法學總論》開篇就指出:“正義是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的這種堅定而恒久的愿望”。[1](p5)關于應得,比利時學者佩雷爾曼列舉了迄今最流行的六種正義標準:(1)對每個人同樣對待;(2)對每個人根據優點對待;(3)對每個人根據工作對待;(4)對每個人根據需要對待;(5)對每個人根據身份對待;(6)對每個人根據法定權利對待。[2](p580-582)佩雷爾曼區分形式和具體正義,認為第一種正義是形式正義,其余五種皆為具體正義。形式正義就是以同一方式對待人,即同等待人。在佩雷爾曼看來,由于抽象性和純形式,形式正義不可能出現爭論。人們對正義概念的分歧乃是關于具體正義的爭論。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批判無疑是對一種具體正義的批判。從抽象的人——每個人都享有生命、自由、財產三大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出發,自由主義正義理論主張所有人不分財富、等級、貴賤等,一律平等。如果說權利平等是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基礎和核心的話,那么,馬克思的正義理論則是建立在對平等權利原則進行批判的基礎上,人的貢獻與需要,構成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基礎與核心。
一、權利平等: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基礎和核心
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是以權利的平等為其基礎和核心的。正如有學者所言,“權利平等的原則在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論證中占有基礎性的地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所依據的原則可以被概括為權利原則”。[3](p63)與封建等級制不同,自由主義否認人的差別,認為人是生而平等的,這種平等就表現在所有人,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種法律面前的權利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以往一切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比以往一切社會形態更為文明、更為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識。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一開篇就明確指出,“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說自明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他們由其創造者賦予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為了取得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從被統治者的同意中產生出來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當它對于這些目的有損害時,人民便有權利將它改變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據的原則和用以組織其權力的方式,必須使人民認為這樣才最可能獲致他們的安全和幸福。”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也以美國《獨立宣言》為藍本,宣稱人們生來就是自由平等的,人人都擁有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的權利,而政府只能在國民授權的范圍內行使權力。因此,權利的平等乃是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基礎和核心。羅爾斯明確地將正義的第一原則界定為“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4](p61)而德沃金則通過對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平等尊重的權利不是社會契約的產物,而是進入原初狀態的前提。他說:“作為公平的正義是建筑在一個自然權利的假設之上的,這個權利就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享有平等的關心和尊重的權利,這個權利的享有不是由于出生,不是由于與眾不同,不是由于能力,不是由于他的杰出,而只是由于他是一個有能力做出計劃并且給予正義的人”。[5](p244)換言之,在德沃金看來,平等的關心和尊重的權利不僅是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也是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基礎。
二、欺騙與排斥:以平等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局限性
然而,在馬克思看來,以平等權利為基礎和核心的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盡管相較于以往的各種正義理論而言,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它廢除了封建特權壓迫,在人類歷史上首次確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理想,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種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表現卻并非完美。
首先,以平等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無視人的現實生活,它用抽象的公民身份遮掩、回避了人的現實差異。因而,它表面上是一種平等主張,實際上卻是在主張不平等,具有欺騙性。
馬克思認為,作為人類歷史活動的前提,個人總是現實的,而不是抽象的,他說:“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這些現實的個人,在馬克思看來,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6](p524)他們既非離群索居,也非固定不變,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6](p525)換言之,現實的個人是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個人,處于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受一定的社會關系制約,而非單純的人自身。基于“現實的、活生生的個人”這一前提,人的本質在馬克思眼里,就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從現實的個人出發,馬克思批判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認為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在把人當作“公民”,即“抽象的、人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的同時,并沒有廢除人的差別,而是將人的財產、出身、等級、文化、職業等一切差別拋入了市民社會,任其在市民社會中自由競爭。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一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盡管如此,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按其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作為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只有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6](p29-30)財產、等級、文化、職業等這些差別在市民社會中自由競爭的結果不是縮小而是進一步擴大人們之間的不平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是這樣去批判自由主義平等權利的虛偽性的,他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7](p199-200)同為公民的資本家和工人兩者的人生境遇之所以如此的不同:一個“昂首前行”,一個則“戰戰兢兢、讓人家來鞣”,關鍵就在于雙方在市民社會中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和擁有的財產等,有天壤之別。正是因為個人不是想象的,而是現實的,人們在年齡、性別、財產、能力、身體條件、勞動力分工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別,因此,自由主義的平等權利原則及其所表達和詮釋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就是虛偽的,具有欺騙性。它剝奪了現實的個人生活,把人視為“想象的主權中虛構的成員”,[6](p31)用政治領域中抽象的公民平等掩蓋、代替了實際生活領域中人的不平等,其結果只能是一種新的不平等。因而,誠如金里卡所言,“馬克思拒斥平等權利的理念,不是因為他反對平等待人的理念,而只是因為他認為,訴求權利不可能吻合那個理想。”[8](p308)
其次,從權利的生成及其本性來看,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乃是利己的人的權利,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分立性和排斥性。
與霍布斯、洛克等近代自由主義啟蒙學者把生命、自由、財產等權利視為“天賦人權”不同,馬克思從自己的唯物史觀出發,認為權利并非“天賦”,而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馬克思從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入手,把人類社會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第一階段,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為根基的第二階段,以及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階段。[9](p104)資本主義的政治革命在打破封建專制權力、建立資產階級政治國家的同時,也使市民社會從政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分解為獨立的個體。這些個體間的關系是通過法制表現出來的。權利因此并非天賦,而是歷史發展到“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的產物,是對獨立的個體關系的規范與調適。
自由、財產、平等這些權利不僅并非“天賦”,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它們是“利己的權利,是個人同其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離開的人的權利”。[6](p40)在馬克思眼里,自由這一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6](p41)是可以做和可以從事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情的權利。這一權利是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它好像兩塊田地之間的界限,將人彼此分隔開來,是人作為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單子的自由。而私有財產這一人權,馬克思認為,不過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種自由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6](p41)平等的權利就是每個人都同樣被看成那種獨立自在的單子。安全,馬克思認為這一市民社會的最高社會概念,也沒有超出自己的利己主義,它是利己主義的保障,整個社會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證維護每個成員自己的人身、權利和財產。在逐一分析了自由主義的各項天賦權利后,馬克思得出結論認為,“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于自身、封閉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在這些權利中,人絕對不是類存在物,相反,類生活本身,即社會,顯現為諸個體的外部框架,顯現為他們原有的獨立性的限制。把他們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利己的人身的保護。”[6](p42)
正是因為以平等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所具有的欺騙性和排斥性:一方面它否認人的現實差別,表面上是一種平等主張,實際上卻是在主張不平等;另一方面,它本質上乃是利己的人的權利,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分立性和排斥性,因此,馬克思本能地感覺并理性地認識到需要有一種新的理論去超越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使它在真正實現人類平等的同時,也能真正實現人的類本質。
三、貢獻與需要: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超越
1.原則和實踐的統一:貢獻原則對權利原則的超越。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私有財產的廢除,使得市民社會中因為財產等的不等對人們平等的影響消失殆盡。在社會主義社會,每個人和其他人一樣,都是生產者。人們之間的平等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也即人們對社會的貢獻來衡量。他說“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所給予社會的。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全部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各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的一份。他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10](p434)可見,私有制廢除后,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義原則,是以人們的勞動,也就是人們對社會的貢獻為基礎和核心的。
由于貢獻原則是以人們對社會的貢獻(勞動)為尺度進行衡量的,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的貢獻原則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踐上廢除了人的差別,從而使得正義的“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相互矛盾”。[10](p434)與權利原則表面上宣布廢除一切差別、所有人一律平等,實質上是將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等差別拋入市民社會,任其在市民社會中自由競爭,制造新的不平等不同,貢獻原則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把所有的人都只視為勞動者,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即勞動)來獲得報酬,實實在在地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等的差別,從而消除了權利原則下由于人的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等的不等對人的平等的影響。因此,與權利原則的虛偽性相比,貢獻原則使得正義的原則和實踐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內在的統一,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勞動)來獲得報酬的。
2.貢獻原則本質上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原則。
雖然貢獻原則使得正義的原則和實踐已不再相互矛盾,但在馬克思看來,貢獻原則仍然是有不足的。一方面,人的天賦是不一樣的。貢獻原則雖然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把每個人都視作勞動者,但是卻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如能力高者,能力低者,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另一方面,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有人偏好奢侈,有人崇尚節儉,有人喜歡高雅音樂,有人則愛好行善,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10](p435)因而,縱使大家工作能力一樣,貢獻一樣,需求的不同也會使得人與人的事實平等成為不可能。由此,馬克思得出結論認為,社會主義的貢獻原則,盡管實現了正義的原則和實踐的統一,但仍然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框框,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具有不平等的結果。
3.平等與關愛:需要原則對法權原則的超越。
由于貢獻原則本質上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原則,它像一切權利一樣具有不平等的效果,因此,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貢獻原則有必要為需要原則所替代。他說:“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一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6](p637-638)與貢獻原則以勞動為尺度、按能力計報酬不同,需要原則是以人的需要為尺度,按照人的需要進行分配的。因而,與貢獻原則不同,需要原則不再依附于個人能力的發展,它跳出了資產階級的框框,使得活動和勞動上的差別對人的平等的影響消失殆盡,真正體現了平等待人的理想。
需要原則不僅跳出了資產階級的框框,實現了對人的真正的平等關照,而且更重要的是,與權利、貢獻的法權原則相比,需要原則超越了法權原則的利己性,是積極地尊重、關懷、愛護人的一種重要表現。如果說權利原則是以人的分立性為基礎,本質上是利己的人的權利的話,那么,需要原則則是以人們相互之間的愛為基礎,本質上是對人的積極的關懷和愛護。正如布坎南所言,把人當作權利的承載者,就是“把自己當作人際沖突的潛在一方,在沖突中,就有必要明確自己的權利并為自己認為正當的要求而‘奮爭’”。[11](p76)相反,如果把人看作需要的承載者,則要求人們積極地去了解人,了解人的需求,進而去關懷、愛護他們,向他們提供幫助,使他們的需要得以實現。因此,與法權原則基于利益的計算、權利義務的考量不同,需要原則超越了法權的界限,是對人的關懷和愛護。當然,這種超越是有條件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0](p435-436)
需要之所以超越權利和貢獻,成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正義原則的基礎和核心,這和馬克思對人的關注和理解是分不開的。人在馬克思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地位,馬克思終其一生都在為人的解放而努力奮斗。《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告:“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2](p53)人,在馬克思眼里,是一種“類存在物”,“生命活動的性質包含著一個物種的全部特性、它的類的特性,而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13](p162)正因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關系回歸于人自身”,[6](p46)因而,正義,在馬克思看來,就不僅僅是資產階級宣布的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而是要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使人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正義就集中表現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6](p185)
四、余論:在法權的基礎上去積極地愛人
正是在批判以平等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從人自身出發,以人的貢獻和需要為基礎,構建了以人為目的的正義理論,從而超越了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但值得指出的是,這種超越并不是對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純粹否定,而是在“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基礎上的一種超越。與自由主義正義觀不同,如果說對權利的關注,會使人基于唯我論去理解自己,導致人與人的相隔、分立乃至排斥的話,那么,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對需要的關注,則要求突破法權的邊界,去積極地關懷和愛護人。兩者之間并非必然矛盾。正如金里卡等學者所言,“正義不僅相容于對他人的關心,正義本身還是關心他人的一種重要形式”、“正義所排斥的不是仁或愛,而是不正義”[8](p316)。反之,我們也可以說,愛是正義的升華,而非不正義。換言之,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不是要完全否定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而是要去提升它,升華它,使它不再是一種消極的補救的道德,而是一種積極的愛的道德。
在現階段,由于生產力的限制,我們的正義理論只能以次優的貢獻甚至權利原則為基礎,但我們不能一味地恪守法權原則,必須看到法權原則的不足,必須超越法權原則的虛偽性與分立性去關愛我們的鄰人,但這種超越不是完全拋棄法權,置貢獻、權利于不顧,而是要在承認、尊重法權的基礎上去關懷、愛護人,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和諧”,才能既“公平正義”,又“誠信友愛”。
[1][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法學階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2]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王新生.馬克思是怎樣討論正義問題的?[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0,(5).
[4][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5][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正義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加]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Allen E.Buchanan,Marx and Justice: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Roman and Littlefield,1982.
[1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