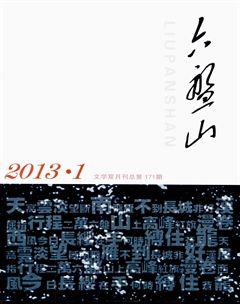喚醒身體 反抗壓抑
鄭鵬飛
一、感覺化敘述的文本分析與藝術淵源探索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莫言一直筆耕不輟,保持了旺盛的創作勢頭。其中,在他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創作的多部小說中,有大量的感覺化敘述。即在文本敘述中編織進大量新穎、奇特、大膽、怪誕的直覺體驗描寫,營造出色彩斑斕的感覺世界,以其濃烈的“感官刺激性”,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閱讀沖擊力。如:
“啪嗒一聲細響后,一道火光躥出槍口,黯淡了霞光,照白了他的紅臉。一聲尖利的響,撕破了村莊的寧靜,頓時霞光滿天,五彩繽紛,仿佛有仙女站在云端,讓鮮艷的花瓣紛紛揚揚。上官呂氏心情激動……只要是看到鐵與火,就血熱。熱血沸騰,沖刷血管子。肌肉暴凸,一根根,宛如出鞘的牛鞭,黑鐵砸紅鐵,花朵四射,汗透浹背,在奶溝里流成溪,鐵血腥味彌漫在天地之間。”(《豐乳肥臀》)。
這種感覺化敘述是從敘述者的內部視角出發,傾訴當事人的感官發現與微妙體驗,細致描摹個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的感受,及其瞬間的情緒印象、幻覺、錯覺、潛意識、下意識等非理性的內容。這種敘述方式強調了感官的功能,突出感覺的審美價值,實際上屬于現代主義表現藝術范疇。
作為現代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感覺化敘述的文學源頭可以上溯到“一戰”后的歐洲。當時,法國作家保羅·穆杭以感覺化方式表現現代人的現代體驗,被推為“新感覺主義的巨擘”(蘇雪林語)。保羅·穆杭對1920年代日本“新感覺派”作家如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人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80年代,莫言受到川端康成的影響,通過對其作品藝術特征的品味、領悟,逐步擺脫僵化的現實主義方法的束縛,開始以濃烈的主觀色彩和豐富、細膩的感覺觀照對象。
二、感覺化敘述的文化批判價值
感覺化敘述從文學“內部”看,具有豐沛的審美價值;而放在文學“外部”即傳統和“當代”雙重的文化語境中看,它有文化批判價值。
前文指出,感覺化敘述是采用內部視角,通過描述當事人的直覺體驗,創造了一個色彩斑斕的感覺世界。當讀者閱讀這樣的小說文本時,由“作者—作品—讀者”構成的文學“公共空間”形成了。在這個空間中,當莫言將瑰異、奇特的直覺體驗訴諸筆端時,讀者的感官體驗也復蘇、被調動了,他們的視覺、聽覺、嗅覺、以及味覺、觸覺會圍著莫言的指揮棒轉;讀者在作者營造的感覺世界中,會產生同樣的感官反應,體驗到同樣的情緒。此時,莫言的感覺化敘述就撫摸、喚醒了讀者的感官(身體),使它們從被傳統和“當代”的文化語境壓抑、遮蔽的狀態中解放出來。
從身體的文化政治學角度看,我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倫理道德實踐存在著重視道德理性、輕視身體的價值取向。孟子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程朱理學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點,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等論述中,“生”、“身”、“視”、“聽”代表身體及其感官活動,“仁”、“禮”代表某種道德理性,二者處于二元分立狀態,道德理性以某種終極真理、正義目的自居,身體則淪為工具、手段,處于次要甚至被罷黜地位,在這種觀念影響下,人們的身體長期處于被遮蔽狀態。
在20世紀50~70年代的“當代”文化語境中,人們的身體受到經濟制度的壓抑。這個時期,我國在社會財富匱乏、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為盡快實現工業化、趕超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了資本和資源密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決定了當時只能推行重積累、輕消費的國民經濟政策,在抑制消費的制度安排下,人們猶如“苦行者社會”中的清教徒,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身體的基本需求(吃穿用)很難得到滿足。與此同時,國家也形成了配套的“意義供給機制”,以“污名化”策略不斷貶低、丑化包括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在內的追求滿足身體需求的消費觀念,對身體形成了遮蔽、壓抑(劉心武《班主任》中謝惠敏認為女孩穿短袖、裙子就是“資產階級作風”即為例證)。
而莫言在童年、少年時代遭受的饑餓、貧困,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這種身體遭受嚴重壓抑的歷史記憶構成了莫言寫作中難以擺脫的情結,弗洛伊德認為,藝術、文學與科學,都是被壓抑的性能量升華后進行的轉移。“作家的創作,即藝術作品,正和夢一樣,是無意識的愿望,獲得一種假想的滿足。”莫言的創作與這種時代氛圍形成了一種反抗壓抑的隱喻關系,他的狂放不羈的感覺化敘事,就形成了對這種身體壓抑的反抗。
英國學者伊格爾頓認為,肉體是審美感性對理性話語霸權反叛的形式力量。正像理性話語向生活世界進軍要肉體來開道一樣,審美感性從理性話語中突圍也是從肉體開始的,肉體是審美話語反叛理性專制的亂臣逆子。在這種意義上,在文學的“公共空間”內,莫言通過感覺化敘事,實現了對傳統和“當代”文化語境中某些不合理的道德、理性、制度的批判,反抗了它們對身體的壓抑,使身體從被壓制、被漠視、被遮蔽狀態下解放出來,達到了感官解放、身體解放,開始向生命的自由狀態邁步。
【本欄目責任編校 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