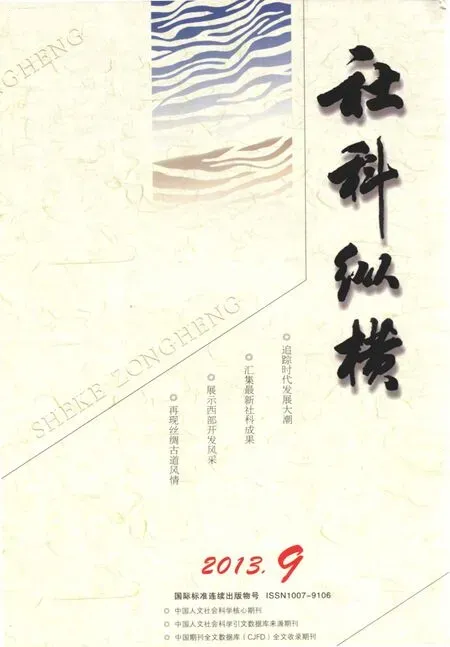高郵王氏訓釋《左傳》之方法及特點
張憲華
(上海大學文學院 上海 200444)
清乾嘉時期,學界治學崇尚質樸,懲元明學風空疏,棄虛務實,力矯時弊,這一時期,大家迭起,著作頗豐,其中成就最為卓著者當屬高郵王氏父子王念孫、王引之。王氏家學淵源深厚,又能篤志于學,勤奮讀書,打下了扎實的功底,經過終生不懈的努力,終于登上了學術研究的巔峰,梁啟超贊道:“王石臞、伯申父子,為清學第一流大師,人人共知。”[1]
高郵王氏善于用小學知識從事校勘、訓詁和整理古書,這一特點突出地表現在王氏父子二人合作的學術結晶《經義述聞》一書中。方東樹認為“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俯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2]此書主要解釋群經子史中的疑義,廣征群書,匯通古今,其糾正前人誤解之文句,為后世所宗,代表了清代漢學派治學的最高水平。在《左傳》學方面,《左傳述聞》是《經義述聞》一部分,共三卷,216條,其中王念孫說者為81條,王引之論者135條。內容基本為校勘文字和考釋經義,每一條都解決一個具體問題,沈玉成、劉寧將之視為“清代考據學派關于《左傳》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3]。
乾嘉為清代學術全盛時期,其成就遠邁前代,而學術之發達往往要講求方法的科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分析道:“然則諸公易能有此成績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而已。試細讀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現此等精神。”[4](P172)他以王氏父子為例,具體研察其研究方法有六: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虛己,第三曰立說,第四曰搜證,第五曰斷案,第六曰推論,并認為,“此清學所以異于前代,而永足為我輩程式者也”[4](P173)。王氏父子治學,無論其成就,還是其方法,都贏得后人的高度贊譽。王氏父子精于訓詁之道,善于運用傳統的訓詁手段又有所創新和發展。通觀《左傳述聞》,王氏父子訓釋《左傳》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明字詞之古今義
易:古有疾、速義。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此處杜預注、劉炫、孔穎達之解皆失之。王氏評注疏家對‘易’字之注曰:“易,速也,疾也。古謂疾速為易也,后人不知易有疾速之義,或以為改易,或以為簡易,望文生訓而古義遂失其傳矣!”
怨:古有刺義。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怨,刺之。王氏評曰:“《正義》以為君怨,為怨怒之怨,失之矣。”
欲:王氏曰:“古義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者欲皆謂省好也。言欲惡皆謂好惡也。”《左傳·成公二年》:“余錐欲放鞏伯,其敢廢舊典以泰叔文。”
第二,析《左傳》中的專有名詞
政:專指正卿。《爾雅》:“正,長也。”王氏曰:“正卿為百官之長,故謂之正。”如:
《左傳·桓公十八年》:“并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左傳·哀公十五年》“: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偪:專指有礙于權。如:
《左傳·襄公三年》:“楚公子申為大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宰。”
《左傳·僖公五年》“: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
第三,破假借,求本字
王引之《經義述聞序》:“訓詁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為之解,則詰鞠為病矣。”[5]
劉又辛總結王氏父子考訂假借字的方法,主要有:
(一)“得經意”——即從經文上下文和全篇文意判斷假借字。
(二)利用前人傳注,但不迷信傳注,以是否能得經意為取舍標準。不合經意的要敢于以“己意逆經意”。
(三)“參以他經”,即同其他經文中的語言材料相參證。這就是用歸納法歸納同類語言材料。做歸納對比研究。
(四)“諸說并列,求其是”。用比較法辨明是非。
(五)“字有假借,則改其讀”。即把假借字改讀為本字。
(六)有時用同源詞材料相參證以求得本字。
(七)利用古音知識及方言材料以證古語本字。[7]
如“又可以為京觀乎”“、不可以終”條: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一。”《釋文》“:何,或作可,誤也。”陳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為‘何’字之省,未應遽斥為誤。”宣十二年《傳》“: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宋十行本,明閩本、監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經》,宋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誤。余謂“可”即“何”字也。此言古之為京觀,所以懲有罪也。今晉實無罪,則將何以為京觀乎?既曰“何以和眾”,“何以豐財”,“何以示子孫”,又曰“何以為京觀”,四“何以”文同一例。(《爾雅·釋邱》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經》作“可”者“,何”之借字耳,非有兩義也。又襄三十一年《傳》:“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案:“不可以終”,本作“可以終世”,“可”,即“何”字也。上既言“不能終矣”,此又言“何以終世”,作問詞以申明之,正與上文相應也。僖十一年《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正與此同。下文言“令聞長世”,又與“終世”相應也。《唐石經》及各本皆作“不可以終”者,傳寫脫去“世”字,僅存“可以終”三字,后人又誤讀為“可否”之“可”,遂于“可”上加“不”字耳。《漢書·五行志》引此正作“何以終世”。(宋景佑本如是。今本作“不可以終”,乃后人以《左傳》改之。)《志》文本于劉歆,蓋歆所見《傳》文本作“可以終世”,而“可”即“何”之借字,故引《傳》直作“何”也。[7]
第四,同義詞互訓
王氏認為:“凡同義之詞皆可互訓,而注疏都未之及。”王氏還指出同義詞之間,另一字之別義亦可以為訓。如“有”與“友”古字通,故友可訓為親、愛、有亦可訓為親、愛。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雖及胡省,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有,愛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友也。
第五,內證和旁證
王氏遇到難解之處,有時還通過內政和旁證來推究竟某些詞義,如:
《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使謂原繁曰:‘且寡人出,伯父無裹言。’王氏考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對曰: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從而定“裹言”即“不通外之言,即所謂無密言。”
《左傳·文公十八年》:“天下之民謂之饕餮”,“饕餮”二字上下同義,“解者謂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不知饕餮本貪食之名,因謂貪得無厭者為饕餮。饕與餮無異也”。《左傳·襄公八年》“馮陵我城郭”,“馮陵”二字上下同義,“解者訓馮為迫,不知馮亦陵也”[8]。
限于文章的篇幅,我們每種方法都只能擇取一二例加以簡要說明,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高郵王氏校釋《左傳》的某些特點:
第一,音韻學
王氏父子精通音韻學,反映王氏古音見解和研究成果的資料,主要有以下幾種:
韻譜:《高郵王氏遺書》載有《毛詩群經楚辭古韻譜》兩卷;
書信:《與李方伯書》、《與江晉三書》、《與陳碩甫書》、《與段玉裁書》等等;
序跋:《書錢氏〈答問〉地字音后》、《六書音韻表書后》、《重修古今韻略凡例》等等;
學術專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廣雅疏證》、《讀書雜志》中涉及古音的文字材料;
王引之《與夏遂園書》,較之乃父又有所精進。
王氏父子之所以能在小學、經學方面取得的成就,離不開他們精深的音韻學造詣,“有音韻學家而不治考據者,未有考據家而不通音韻”[9]。他們強調訓詁必須將文字與聲音結合起來,既要知文字,更要知聲音訓詁。正如王念孫在《廣雅疏證自序》中談到訓詁的方法時說:“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于所不知,蓋闕如也。”[10]
第二,文法的萌芽
中國之文法,傳自西洋,其內容包括甚廣,在馬建忠《馬氏文通》之前,中國沒有系統的語法觀念,一些學者,如漢代鄭玄、唐代孔穎達已經有一些模糊的語法意識,發展到清代王引之之時,已經能夠用語法解釋經典、串通文意。在訓釋古書時,王氏父子主要是從文意、文勢、文例、文章結構、篇章劃分、行文特點、用詞特點、句型特點、音韻特點等方面著眼辨誤糾謬。如:桓公三年:“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立違,謂立奸回之臣”。晉代杜預做注解時,把“違”解釋成“違命”,這里“違”被看作是動詞,王引之解釋成形容詞,“違”是“奸邪”之義,楊樹達評論認為似乎更為恰當。
文法學的意識,王氏雖不能明言,而心知之,亦有發明。《左傳述聞》一書中在文法方面的收獲略述如下:
(一)倒言:即目前語法所謂詞序提前。如《左傳·昭公十九年》“:私族于謀而立長親。”王氏認為應為倒言。另外,王氏又引《左傳·昭公十一年》:“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左傳·昭公十九年》:“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
(二)使動:《左傳·襄公十一年》:則武震以攝威之。“攝”同“懾”,懾也。王氏指出: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
(三)指出古漢語虛詞的特殊用法。如選用兩個虛詞表示一個意義:《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將庸何歸”,即“將何歸。”
在《經義述聞》多條論述里,王引之還注意用修辭方法來解釋儒家經典,盡管當時修辭學還沒有成為一門系統而富地位獨立的學科。如《左傳》“:廣哉熙熙乎”。予謂熙熙,即廣也。此處所謂“重言”,即是一種修辭方法,即“疊字”。其他還有互文、省略、對文等等。“《經義述聞·通說》所收各篇論文中,其中批評前人望文生訓和增字解經的弊病以及論經文假借各條,尤為明白剴切,為研究訓詁學和注釋學者所不可不反復細讀的重要文獻”[11]。
第三,廣征博引
王氏父子在校勘《左傳》脫字、衍文、錯簡時,善于依據《左傳》文例,證之其他典籍,加以訓詁與考證。如“與子上盟”條,《左傳·襄公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王引之判定“盟”字為衍文。這一判定是基于考證“盟”與“誓”的差別而得出的。“用兩珪質于河”,是“誓”而非“盟”。他引《曲禮》:“約信曰誓,蒞牲曰盟。”《周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司盟》:“凡盟詛,以其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連續列舉《左傳》的九個例證和《穀梁傳》的一個例證,考證《左傳》凡言諸侯盟,“無不殺牲歃血者”。如果倉卒無牲,則以人血代之,而不用珪。再考《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子犯以璧授公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以及《晉語》但言公子沈璧以質而不言盟,韋昭《注》曰:“信也,沈璧以自誓為信。”證明用珪,為約信而并非盟。因此,“蒞牲者,乃謂之盟,投璧不可謂之盟也”。[12]
高郵王氏在校釋《左傳》時還善于批判吸收當代學者的成果,對顧炎武、臧琳、惠棟、盧文弨、錢大昕、陳樹華、段玉裁、阮元、臧庸等眾多當代學者之說,往往能夠批判繼承。如《左傳·僖公九年》:“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顧炎武曰:“藐,小也。”惠棟曰:“案呂諶《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訓藐為小,亦未當。”王引之據《爾雅》、《廣雅》,并證之《周語》韋昭注、《文選·寡婦賦》李善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經》等,以顧氏訓“藐”為小為是,釋“諸”即“者”字。王氏無征不信,實事求是,表現出科學求證的態度。
第四,以小學校經
皮錫瑞總結清代經師的學術貢獻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曰輯佚書;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學。通小學表現在音韻、文字、訓詁之學成就斐然。清人多重考據,反對空談義理,像王氏父子這等大師,對于語言與思想的關系,小學與經學的關系有著正確的認識:“訓話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段注說文》王念孫序)有的人之所以沿襲舊誤,“皆由于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經義述聞》阮元序)皮錫瑞說:“經師多通訓詁假借,亦即在音韻文字之中;而經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最精。”[13]
王氏父子重視小學,并在小學研究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直接推動了訓詁學的發展,也推進了乾嘉考據學的繁盛。高郵王氏四種,堪稱以小學明經學的典范,不僅是清代考據學派小學研究的代表作,也是經學研究的重要成果。精于小學,長于校讎,是他們有別于其他眾多學者的治學優勢。對《左傳》的校釋,只是用小學校經的成果之一。
王氏父子在清代學術史上有著崇高的聲譽,阮元譽為“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黃侃稱王氏是“繼往開來,成小學中不祧之祖”。王氏父子超越別人之處就是對科學方法的掌握和自覺運用,這些方法給后世研究訓詁的人開辟了一條寬闊的途徑。
[1]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227.
[2]方東樹.《漢學商兌》,《續修四庫全書》本[M].第0951冊:593.
[3]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299.
[4]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王引之.經義述聞[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2.
[6]劉又辛.通假概說[M].成都:巴蜀書社,1988:69.
[7]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九)[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449—450.
[8]王引之.《通說下》,《經義述聞》卷三十二[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773—774.
[9]楊向奎.《王念孫王引之〈高郵學案〉》,《清儒學案新編》五[M].濟南:齊魯書社,1994:325.
[10]王念孫.廣雅疏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
[11]郭在貽.訓詁學[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05.
[12]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八)[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444.
[13]皮錫瑞.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4: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