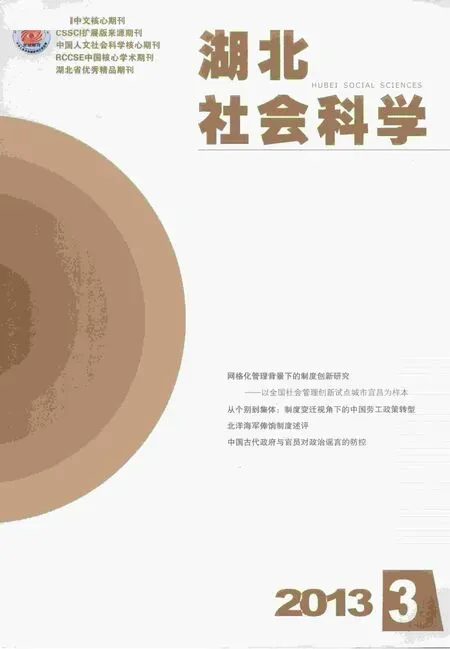寫作運思的特性論列
王澤龍
(河南教育學院 中文系,河南 鄭州 450046)
寫作運思是寫作主體在心理上的謀劃、設計和推敲,是一種極其復雜、精微的高級思維活動,是整個寫作過程中最為緊張、最為勞神,也最為關鍵的階段。沒有運思,不僅對感知對象的進一步加工是不可能的,也就無法通向表述的空間;運思不佳,寫作也會步履蹣跚,即使勉強到達終點,也了無生氣和光輝。對于寫作運思必然存在的種種特性,我們應當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加以全面透徹的認識和把握,這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駕馭整個寫作的行為過程。
一、動機導向性
寫作運思都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都有它賴以產生的或顯明或潛隱的起因。一片賞心悅目令人陶醉的自然風景,一樁驚天動地令人震撼的社會事件,一縷牽腸掛肚綿綿不絕的情思,一個心向神往念念不忘的夢想,抑或是一種說不清根由話不明情狀的信息或感受,都可能使寫作主體產生運思的動機。而且,運思之舟的遠行,又總會有運思動機的定向導航。動機不僅是起因,也是目的。作為高級思維活動的寫作主體的運思,無不有著自覺的目的,即完整地認識寫作客體,并實現系統的表達和交流。這使得它和直覺性思維活動以及實踐性思維活動有所區別。直覺性思維活動是不自覺的、非邏輯的;實踐性思維活動不追求表達與交流。而在寫作運思中,不管是對信息的選擇與輸送,還是對載體的敲定與運用,始終都瞄準最優化的認識與最優化的表達這一明確目的去求質、求度、求序,最終組成文本的形象系列或思想系列。前者是由記憶中的表象奇妙組接創造出的新形象的圖畫,后者是通過概念、判斷和推理得出的結論。除此以外,也有的是二者得兼,珠聯璧合,相輔相成,達到認識的飛躍和表達的合宜。誠然,運思動機或目的導向的這種彼岸的前景有清晰的也有朦朧的,最終有可以到達的也有不能到達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這種彼岸的前景都會頑強地或隱或顯地吸引著運思主體,促使他盡其所能不厭其煩地去認識它,捕捉它,描繪它。例如元人馬致遠的《天凈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這首小令幾乎全用名詞組成,粗看東鱗西爪,似乎是互不相干的物象堆砌,細讀才領悟到每一物象的展現都服從于一個總的目標:表現游子天涯漂泊的悲慘境遇和凄苦心情。每一個名詞帶出的天涯景物都讓人覺得那么凄愴,景物中正蘊藉著天涯游子寂寞悲涼的心態。眾多的心態畫面(意象)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合成了寫作主體心靈的立體形象 (意境)——對天涯游子的境遇與心情的認識與感受。它由自然(枯藤老樹昏鴉)到人間(小橋流水人家),然后到自己(古道西風瘦馬),由形到神 (瘦馬夕陽——其形可睹;斷腸人在天涯——其心可知)。層層渲染,步步加深,向讀者放射出定向的信息集束流,換言之,這正是運思目的導向的效應。甚至,有時雖然表面上看來有所偏誤,其實卻是迂回前進,曲徑通幽。相傳清朝才子紀曉嵐應邀給一位富家老媼做詩祝壽,開口便是:“這個婆娘不是人。”舉座嘩然。但第二句即出:“九天仙女下凡塵。”眾人解頤。第三句又說:“生的兒子都是賊。”眾人面面相覷。末句揭底:“偷來蟠桃獻至親。”滿堂喝彩。至于長篇巨著的運思,在動機或目的的導向之下,更不能照直思維、一馬平川了。當然,除了寫作主體有意的安排之外,運思中還有不少時候是難以自主地遭遇了曲折,但是只要有心力,他就要排除曲折;也有不少時候是難以自料地偏離了目標,但是只要發現了,他就要調整航向,以求到達彼岸的前景。
運思遵循動機或目的導向而行進,這一程序的最高指揮層次就是對生活與對世界的整體信念,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或者說是思想品位。正如魯迅所說:“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1](p302)其次,生活經驗、學識水平、語言習得、審美修養以及心理素質等,也都是運思導向的根本性、決定性因素。
二、變數無定性
運思雖然有一定的動機或目的的導向,然而,作為一種復雜的運動過程,又往往會充滿不可預定的變數。這是一種氣象萬千、風云變幻的世界。福樓拜寫到包法利夫人死了時,倒在地上哭得打滾,別人詫異,他說他沒有想到包法利夫人竟然死了。許廣平回憶魯迅夜晚寫作,有時寫興正濃,放不下筆,直到東方天亮是常有的事。《傷逝》這篇小說,就是一夜寫成的。家人勸他休息,他總是說:“寫小說是不能夠休息的,過了一夜,那個創造的人脾氣也許會兩樣,寫出來就不像豫料的一樣,甚至會相反的了。”[2](p83)巴金也說:“我開始寫《秋》的時候,我并沒有想到淑貞會自殺,我倒想讓她在十五歲就嫁出去,這倒是更可能辦到的事。但我越往下寫,淑貞的路越窄。寫到第三十九章淑貞向花園跑去,我才想到了那口井,才想到淑貞要投井自殺,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3](p424)那么,這是為什么呢?
原來,盡管在操筆前的醞釀階段即運思的前期,寫作主體往往預先設定了寫作運動的方向、步驟和結果,但進入運思的后期即付諸表述階段,由于文字符號要素的直接操作,在其生成轉換的創造功能作用下,往往使得運思內容要素的相互運動在層次上發生偏離和嬗變,不同程度地改變其預定的方向和步驟,不斷地調整其運動發展的軌跡,采取新的運思視角,發現新的運思目標,從而形成新的運思結果。這對于主體操筆下的運思預定而言,就是自身運動的一定程度的變數無定性了。這種現象,突出地表現在文學寫作進行的運思過程中。許多作家在談到創作體會時都認為,作品中的人物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你只要開始描寫他們了,他們就會按照自己的性格、稟賦,或某種生命邏輯,自動地去干他該干的事,說他自己該說的話,他們有一條自己的軌跡,并不受作家先前的運思目標的操縱,反而常常讓作家因始料不及而大吃一驚。其實,不管作家們是否明白,所謂作品人物的性格邏輯或生命邏輯,還是寫作主體在運思過程中所必然要遵循的思維邏輯。換言之,運思中變數無定的偶然也蘊含著某種必然。另外,實用文體的運思也同樣存在變數無定的特性。比如闡述一個論題,在思考的過程中,各種信息材料會在大腦屏幕上紛至沓來,相繼出現,甚至旋轉變幻著,交叉扭結著,供你識別和選用。運思中改變觀點,調換例證,變換論證方法,重組結構框架的事并不鮮見。
變數無定性典型地表現為運思中“說不清”的模糊。因為,運思受著主體知識經驗、信息材料、主觀心理、語言符號等的制約,而知識經驗和信息材料在頭腦中的儲存都是既有屬于顯意識層的,也有屬于潛意識層的;主觀心理活動也是既有屬于邏輯的,也有非邏輯的;語言符號也常常是模糊性集合狀態。這樣,就必然會使運思經過一個“生活←→心靈”物我化一的相互銜接、過渡、轉化的“亦此亦彼”的中介區,即變化的模糊的狀態。在此期間,寫作主體往往會有走投無路的迷茫或舉步維艱的困頓。福樓拜在談到創作《包法利夫人》的艱難時這樣感嘆:“藝術!你究竟是什么惡魔,要嚼我們的心呢!為著什么呢!”[4](p179)正是這種迷茫和困頓,常常使得那些意志薄弱的寫作者半途而廢,無功而回。
我們這樣講運思的變數無定性,也并不認為它是那樣絕對的變幻莫測,不可把握。只要我們肯下功夫,深思多慮,就能從萬變中抓住不變,從模糊導向清晰,從無定引向確定,最終孕育成精神產品的胚胎,以至讓它充滿健康生機地呱呱墜地。
三、內向自為性
所謂內向自為性,就是人腦這個自控系統在運思過程中相對外界的暫時封閉,“關起門來”自我醞釀和構想,而不需要再從外界獲取信息。正像牛羊等反芻類動物采食草料時先是不經細嚼就吞咽下肚,但爾后還要讓草料由胃里返回口腔慢慢咀嚼,又俗稱為“倒嚼”,倒嚼時就無需再去采食。采食是“外向求索”的,倒嚼是“內向自為”的。寫作運動中的感知有似采食,運思則有似倒嚼。
內向自為的含義可以從相對于客觀和相對于主觀兩方面來考察。前者要求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盡可能少受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擾。如果你剛坐下來半小時,就接了五次電話,恐怕任你是何等的天才,也無法順利進行運思了。甚至有人在運思時對房間里輕快悠揚的音樂和別人趣味橫生的談話,也會覺得煩躁不堪。北宋陳后山(師道)做詩時,連小貓、小狗都攆到門外;據說英國詩人拜倫因為氣憤寫作中有人“打岔”,竟把金表摔進火爐,還對家人鳴槍示警!另一方面,更要求運思主體自己能夠全神貫注,頑強求索,心無二用,持之以恒,而不是三心二意,浮念叢生,或如蜻蜓點水,淺嘗輒止,運思才會有佳釀美醪汩汩而出。在實際的運思活動中,可能會看到寫作者有時坐在案前苦思冥想,有時卻隨便擺弄著什么東西,有時又背著手踱來踱去,似乎是那樣悠閑自得,其實他“內向自為”的運思是十分活躍和緊張的。這種活動,有時會達到“會神”、“入迷”的境界。巴爾扎克說:“在這些苦思苦想、廢寢忘食的時刻里,任何人間的牽掛,任何出自金錢的考慮,都不在他們心上了,他們忘掉了一切。”[5](p52)
運思內向自為的特性,古人就不僅早有真切的感性認識,并且也有理論的表述。劉勰指出:“陶鈞文思,貴在虛靜。”[6](p84)蘇軾也在《送參廖師》一文中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而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靜。”要達到“虛靜”的運思境界,就要從客觀上排除和避免外界物質環境的干擾;更重要的,寫作主體還要“疏瀹五藏,澡雪精神”,[6](p84)即拋棄名利雜念,超脫無聊瑣事,給運思提供一個主體心胸寬闊、心境優化的內在空間。
當然,當運思阻滯不前,千回百轉搜腸刮肚,百思不得要領時,讓緊張的精神之弦放松一下,接納一些看似與正事無關的其它信息也是有益的調節。所謂“用筆不靈看燕舞,行文無序賞花開”,就是從對“燕舞”和“花開”的觀賞中受到啟發,打通了受阻的思路。這種封閉系統的開放,是運思內向自為性的特殊表現。不過這種開放,要求與運思的方向對路、合拍,對信息的接收有著與運思內容高度一致的選擇性。這時雖然運思主體沒有感覺到,但實際上他的腦神經細胞還在積極地做著內向性思考的工作。沒有運思主體內向自為的反復思慮,就很難有那種神奇的妙手偶得。并且,也并非所有的放松和調節都能收到“無意插柳柳成蔭”的喜悅,刻意的“放松”和“調節”,又會生出另一種“有心栽花花不活”的苦悶。深山老林里的天然靈芝,既大多可遇不可求,又肯定得進山入林才能遇。
四、外化可行性
寫作運思固然具有突出的內向自為性,然而另一方面也有顯著的外化可行性。或者說,寫作運思與一般的思維活動相比,除了必然經過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之外,還必須成熟到可以外化落實為有形的語言文字的地步。《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孔子說:“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由“物”生了“意”,而“意”還必須可以轉化為“文”。因為,寫作運思不但具有認識的功能,更要達到交流的目的。認識是一個“使自己明白”的內在過程,它通過感性到理性的飛躍來實現;交流是一個“使別人明白”的外在過程,它通過表述與傳播來實現。所以,寫作運思不能只是為認識而關起門來進行的內在思維,還必須具有將這種認識表達顯現出來的外化可行性。
“外化可行”以“內向自為”為基礎,但內向與外化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陸機說:“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6](p66)可見由“物”到“意”不容易,由“意”到“文”也不容易。蘇軾也在《答謝民師書》中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可見,“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已屬不易,而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即讓運思成熟到可以說出來寫出來的地步,更是難上加難了。
運思要求的外化可行性正因其難能,故而也就可貴。它能使寫作主體的認識最終達到精確化、系統化和定型化。這就是運思的效應。從寫作運思和文本的關系來看,后者就是前者的預求結果,也是形式和內容的辯證統一體。就其內容而言,它就是寫作主體通過具體材料表現出來的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改造客觀世界的思想;就其形式而言,是寫作主體用來承載這種運思結晶的由字、詞、句、段所組成,并具有一定體式規范的篇章。文章書面語言的規范性要求逼出了寫作運思的精確化,篇章結構的整體性標準逼出了寫作運思的系統化,文字符號的穩定性特征促成了寫作運思的定型化。以寫出文章為目的的運思,最終也收到了穿越時空的交流效益。即使殷商時代人們的運思結晶,至今還清晰地儲存在龜甲和獸骨承載著的短小篇章里,向現代人發射著幾千年前生成的信息。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寫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極大挑戰,然而它的地位始終不可動搖。廣播電視發出的大多還是寫作運思的結晶,電腦網絡傳輸的大多也是寫作運思外化而成的文章。
五、群體類似性
盡管迄今為止人們的認識尚未達到一致,但寫作總是有規律的;運思作為寫作過程的關鍵階段,就總體而言也是有規律的,任何人的寫作運思也都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約,這就是寫作運思的群體類似性。首先,存在決定意識,意識來自存在。運思中意旨的發想和開掘都不是無根無秧的,而是要坐胎于寫作客體進入寫作主體感知的視野,“由物生意”是運思活動肇始的必由之路。運思雖然如同鄭板橋所說,“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但是“胸中之竹”還畢竟是“竹”,而不是“玉米”和“棉花”。看到松樹,人們常常聯想到志士,而不會覺得它像庸人;看到芭蕉,人們常常聯想起美人,而不會覺得它像丑婦。這說明,運思的基礎——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感知就常常具有類似性,因而不同寫作主體的運思也就可以相聯通乃至相類似了。其次,雖然人們對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認識,產生不同的意旨,但是在運思當中,他總要以自己的這種意旨去駕馭材料。這里包括根據意旨的需要,把各種材料分別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和其它材料構成一定的和諧關系,以施放出最大的張力;也包括對于本來完全相同的材料,寫作主體也會根據意旨的不同需要,使之或者保持科學的原貌,或者發生藝術的變形。雖然其結果各不相同,但是“以意馭材”始終是一條鐵定的規律。即使是靈感突現,也還是“意”在其中,是“以意馭材”的迅即實現。第三,內容決定形式,必須 “因材綴文”。一個科學研究項目的操作過程和取得的成果,誰也不能寫成一篇荒誕離奇的意識流小說;某種事物特征、功用的介紹,誰都往往選用說明文的形式,等等。誠然有時相同的材料也可以寫成不同的文體,但是,“材”和“文”之間總還要有一定范圍的適應性、互洽性聯系,這也是人們在運思時都同樣不可漠視的。如果要“量體裁衣”,那么“材”就是“體”,“文”就是“衣”。正是從這些方面來看,運思作為一種由“物”到“意”,再由“意”到“文”的精神勞動過程,不同的寫作主體之間也總存在著一定的群體類似性。當然,這種類似性應從宏觀上概覽,不宜在微觀上細究;它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六、個體特異性
運思的個體特異性并不難理解。即使面對同一客體,不同的主體也會有不同的感知,進而必然有不同的運思以及表述。同樣是一根手杖,巴爾扎克雕上的銘言是“我粉碎了一切困難”,而弗洛伊德雕的卻是“一切困難粉碎了我”。朱自清和俞平伯在同一個時間、同一條畫舫上泛游,爾后又同以《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為題所寫的散文(兩篇),也能讓人透過他們以相同客體為表述對象的文字符號,看到他們迥然有別的運思特色。試看二人在拒絕了歌妓賣唱之后的不同心理活動,朱自清寫道: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里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于她們,一面對于我自己。她們于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作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
俞平伯則這樣想:
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賣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曾滲過一層濃烈的悲哀,佩弦(按即朱自清)或者作如是想罷?至于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為可笑的浮詞,它的收韁勒馬的威風,散作隔界的煙云了。
顯然,朱自清作為一位正直學者,樸實、拘謹,語言里壓不住難平的心潮,讀來動人情懷;俞平伯作為一位智慧哲人,冷靜、超脫,文字中蘊藏著睿智的思辨,掩卷啟人心扉。
個體特異性主要是由于運思這種特殊勞動的個體化和主觀性決定的。如果說人們從事的物質生產可以進行集體勞動,許多時候就要求基本相同因而也可以相互替代的話,而精神生產中的運思則必須是個體勞動,一個人的“想”決不能用另一個人的“想”來代替。每一個寫作主體又總有著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生活體驗、思想品位、知識積累、語言習得、審美修養和心理素質等等,也有著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能力結構,即有著特殊的思維個性,其接受信息并且進行加工改造以組合成新信息的模式、路徑和結果也就必然千般百種、千差萬別。人腦,這種地球上最靈異的花朵,它所釋放出的色彩和芬芳,其實是最為斑斕和豐富的啊!
運思的個體特異性也來自讀者受體求新求異心理的呼喚。東漢王充在《論衡·自紀》中說:“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其實,正是由于“不同面”、“不共聲”,才有各自存在的獨特價值。讀者求新求異的接受心理,其實也正是對客觀世界運動性和豐富性的天然契合,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主體與客體的相對和諧,推動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斷進步。作為寫作主體,為了實現傳播的效益,其運思的啟動、深化和外化,也都必須尊重受體的這種求新求異的心理,使自己在各個方面具有獨特的魅力。也只有這樣,才算是出色的運思。
個體特異性還表現為運思過程和結果的不可重復性,它既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因為,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思維也總處于流動的狀態,寫作主體的每一次運思,必然會受到此時此地種種內外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表現出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運思的特性。就像流動的河水,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正因為如此,人類才有著不斷創造的巨大潛能。當代著名學者楊義這樣評論魯迅的小說:“魯迅小說格局最顯著的特點是別開生面,具有高度的不重復性。他尊重生活的多樣性和人們藝術趣味的多樣性,在藝術格局上不重復他人,也不重復自己,他的天才就表現在不落俗套和層出不窮的創造上……正由于他的小說格局篇與篇之間存在大幅度的差異感和多種類的創造性,他為數不多的小說展開了一個有若滄海一般開闊、深沉、氣象萬千的藝術世界。”[7](p187-188)魯迅先生顯然是有意追求和發揮運思個體特異性即創造性的光輝典范。
我們的任務就在于,有意識地培養和訓練自己占優勢的個性心理特征,充分發揮個體特異性中的主觀著色和不可重復的作用,使自己的每一次寫作運思都帶有既區別于他人、也區別于以往的自己的鮮明特色。
還要說的是,運思對于寫作主體來說,既是一杯佳釀,也是一碗苦酒。當一個人運思入迷的時候,就會如夢如癡,忘乎所以,甚至走火入魔,不可自持。換言之,當寫作主體由“感”導向“思”的時候,“思”的精靈便會立刻占領腦的整個空間,揮之不去,驅之不散,演繹出不勝描述的萬千氣象。寫作運思,需要我們傾注良多的辛勞和智慧。
[1]魯迅.魯迅雜文全集[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許廣平.欣慰的紀念[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
[3]李存光.巴金研究資料(上卷)[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
[4]周昌忠.創造心理學[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5]李學勤,等.中國文學寫作大全[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
[6]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