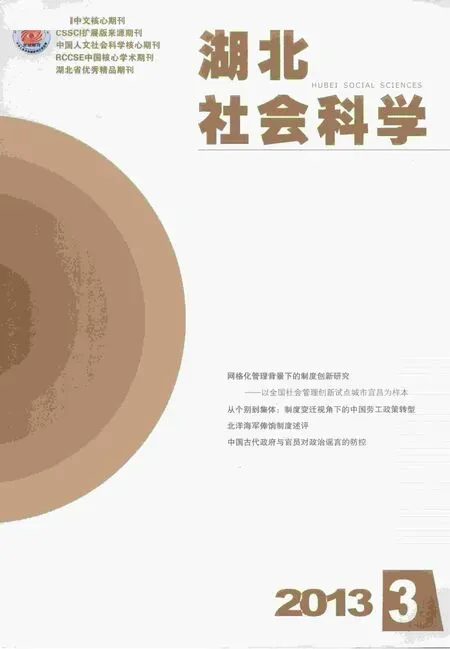《給李風叔叔幫忙》的社會心理學分析
肖格格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社會交換論是一種行為主義社會學理論。社會交換論的創始人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喬治·霍曼斯。其主要論點是:社會學中所研究的制度、組織以及社會都可以分析成“人”的行動,利己主義、趨利避害是人類行為的基本原則。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到某種或明或暗的、能夠帶來獎勵或報酬的交換活動的支配。因此,人類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可歸結是一種交換過程,這種交換包括情感、報酬、資源、公正性等等。人們在社會交往中結成的一定的社會關系可視為一種交換關系。本文以曉蘇的小說《給李風叔叔幫忙》為例,探討社會學家喬治·霍曼斯提出的作為社會行為基本形式的人的心理和行為的五項基本命題在中國現代社會交換中是如何體現其意義的。[1](p83)
曉蘇的短篇小說《給李風叔叔幫忙》的故事情節簡單明了,一位退休的鄉鎮林業站站長“李風叔叔”,為了滿足想跳槽的老婆周蜜的要求再三求“老埡鎮長秘書我”幫忙,結果卻總是出人意料的令幫忙者啼笑皆非,讀者的情感在曉蘇舒緩溫潤的敘述中也悄悄地被啃噬著。年輕貌美的周蜜才十九歲,不顧父親的反對,嫁給了年長她二十歲的下派干部縣林業局其貌不揚的李風科長。李風享受美色的代價是從縣城降級調到了鄉鎮的林業站當了名普通的 “木材檢查員”。在中國,男人的事業在社會生活中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對男人的評價也是以事業有成來衡量的,“攝職從政”是男人高于一切的追求目標,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的男權主義造成的心理認同“男主外,女主內”外部社會事務的爭權奪利等行為通常發生在男人之間,男人失去權力就意味著失去了大部分社會資源的占有,也就是說可用于交換的資源會急劇流失。一個無職無權的男人會被人視為平庸的象征。曉蘇給主人公降級的做法恰恰體現了的這種事業犧牲之巨的蒼涼,由于起點變低,再有水平和能力也只能以一個林站站長的基層職位退休,這為后面不再占有資源的退休老人李風的被棄留下了一個合理的落腳點。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交換是古往今來一切民族、一切社會普遍具有的現象,人們之所以樂于進行相互交換是希望從中得到獎勵或報酬。在以婚姻為交換背景的行為中周蜜付出了美貌“周蜜也值得李風叔叔愛,她個子高高的,胸脯鼓鼓的,屁股翹翹的,又能歌善舞,……雖說人到中年了,但風韻猶存,美色不減,看上去比年輕時更有女人味”后獲得的社會資源是 “從一個代課老師轉成了國家正式教師”、“從油菜坡小學調到了老埡鎮中心小學”、“通過關系給周蜜弄到了一個專科畢業證,上面還壓了鋼印呢”。人類已從經濟交換發展為社會交換,已從單純的物質交換發展為物質與非物質的綜合性交換。“周蜜撒嬌的時候,就是李風叔叔最幸福的時刻。”此時交換的所得是“(李風叔叔)更關心她,更體貼她,更心疼她,馬上就去給她做好吃的,給她買漂亮的衣服,給她洗襪子和三角褲頭”,并且做這些的時候“從不讓周蜜插手”,周密享受到的則是關愛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勞而獲的物質、社會地位等現成的種種輕松生活。她不需要像其他婚姻中的婦女一樣作“女主內”的煩瑣的家務及由此帶來的過早衰老的風險;也不需要與配偶一起承擔什么家庭經濟和社會的責任。“李風叔叔樂意這樣侍候周蜜,象一頭老黃牛,任勞任怨,毫無怨言”,可以看出李風叔叔是很享受這個付出與獲得的過程的,此時彼此是“周瑜打黃蓋”式的各取所需對等自愿的一種互惠互利的享受,形式不同但享受的本質是一樣的,不存在誰剝削誰的問題。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霍曼斯認為社會交換具有公平性傾向。公平性本身就是人們需要的交換價值之一。在李風叔叔退休之前的時間里,他們彼此的付出與預期是基本相符的。根據霍曼斯“攻擊——贊同命題”,如果人們的行為得到預期獎勵,甚至得到大于他們所預期的獎勵,或者沒有遭到預期的懲罰,人們就有可能采取贊同性行為,這種行為的結果也可能對他們更有價值。[2](p56)
李風叔叔“平穩著陸”——退休年齡到了,正常退休。說明他弄虛作假為家庭成員謀取私利的做法并沒受到法律或社會道德的什么阻撓。困難是來自他失去權力之后,“人都退休了,站長自然當不成了”與周蜜的交換內容勢必要發生結構性的變化,要維護原有的平衡就不得不通過其他途徑來補充這種缺失。在客觀事實面前只好以另外曾經儲備過的資源來爭取獲得更多可以用作交換的資源。求人幫忙可能是他目前最易想到和做到的行為了。在位與不在位體現的就是有權力還是無權力的區別。求人與被人求體現著同一原則。俗話說“人不求人一般高”,其實與人沒有關系,只是與人所擁有的權力有關,求人也即是希望被求的人所擁有的權力能為我所用,幫我達成某種心愿。“幫忙”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一種交換現象。這就使故事順理成章的得以延續,自然無痕。李風叔叔的眼光轉向了“攝職從政”的主人公“我在老埡鎮當秘書,李風叔叔以為我很有權力”。凡事皆有因緣,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我”與李風叔叔并非物質上的往來,“畢竟在我家住過,冬天還讓我跟他睡一床。他當時經常買水果糖給我吃,還給我講了好多童話故事呢。”“我”顯然對李風叔叔“存以甘棠”,李風叔叔付出的是無意間對“我”兒時積累的一些美好的情感體驗,“我”回報給他的是由付出時間、精力和金錢為載體的有目的的行為所帶來的一種具體結果“幫忙”。芝加哥學派的威廉·懷特認為:人類并不總是追求最高的物質利益。人們的文化賦予的意義,對于人而言,事物不僅具有內在價值,而且具有象征意義。鴿子不會出于禮儀的目的而期待獎勵或感覺到獎勵,而人卻會為了國旗或十字架而自愿獻身。[2](p55)對于兒時的純真美好的感情延展出來的心理體驗此時還是積極的。“頭一回找我幫忙,我的熱情還挺高”,在具體辦理普通話合格證的過程中主人公“我”表現出來的行為雖然有力不從心的困難,但還是在努力付出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其動機就是“萬一上當受騙,也只有我知道,不會有人笑話我;如果辦成了,我在李風叔叔面前也有面子”。此時的“不會有人笑話我”“有面子”皆是“我”期待獎勵或感覺到獎勵的外顯的表現形式。也體現出“我”想真心辦好事情并且付出實際行動的良好真誠的品德。
被幫忙者“周蜜”本人從其為人行事來看,雖參與了社會生活,身份是鎮中心小學的公辦教師,但并不具備做教師的基本素養,普通話是教師必備的工作語言,合格證只是一個書面證件。她此前沒有通過一點自己的努力學習獲得這些必備的知識技能,卻能在此崗位上一做就是多年,這就意味著她因此而帶來的麻煩都是背后由李風叔叔利用自己的資源擺平的。如此不學無術之人放到如此重要的崗位誤人子弟能幾十年沒長進還不受清理,可想而知她背后的“李風叔叔”多年來付出的努力和心血與人交換的代價之巨大。從她與“我”一起去辦事時候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應該不了解各種辦事的規則,同時也不理解辦成這件事情所應付出的代價。換言之,她歷來只是個享受結果的人,對他人為自己提供的享受條件的代價是不明白的,也就是個癡長了幾歲完全不明事理的人,就象一個兒童隨手拋棄不喜歡的玩具一樣毫不在意,這可能是她能輕而易舉的浪費別人的心血和勞動而不自責的根本原因。主人公“我”雖然是在給“周蜜”幫忙,但與之構成交換關系的卻是“李風叔叔”,所以周蜜不必要為“我”付出什么,因為是“我”答應了“給李風叔叔幫忙”。她能安然享受“我”給李風叔叔幫忙這件事情的結果就行了,同時也就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應該為此付出的各種成本(金錢、人事關系、體力、智力甚至由此可能承擔的風險),可見她是沒有與李風叔叔有難同當的分擔意識的。由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弄虛作假的非正當的行為,雖然是為了促成事情成功卻陷入了“事非宜,勿輕諾,茍輕諾,進退錯”。最后,“我”在李風叔叔面前不僅無功而返同時還被人當做騙子,錢財與尊嚴都受到了損失,關鍵的期待“人情”也沒有落下,事與愿違具有了必然性。根據霍曼斯的價值命題:行為的結果對人們越有價值,人們就越有可能實行該項行為。對人們來說,行為獲得獎勵意味著行為具有正價值;如遭到懲罰,則意味著具有負價值。正價值越高,人們就越有可能實行該項行為,負價值越高,人們就越有可能中止該項行為。[2](p56)這里主人公遭到了絕對的負價值,所以產生“合格證的事之后,我本來不想再給李風叔叔幫忙的”的心理是必然的了。
我們來分析第二次幫忙活動中的付出與獲得,李風叔叔因為周蜜以不與之同房相威脅逼他去推銷香菇,“不然我這日子真是沒法過了。”在找不出第二個可以幫忙的人的情況下“我就硬著頭皮來找你了”,主人公因為“小時候你給我講了那么多好聽的故事呢”勉強接受了這個心理并不認同的“幫忙”。求人的過程中被看成“小地方的人”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可還是選擇了“舍命陪君子”地服從“兩顆淚突然從我眼里掉了下來。”布勞把獎勵分為四種類型:金錢、社會贊賞、尊重和服從。其中以服從價值最高,金錢價值最低。布勞認為擁有使人服從的權力是一種最令人向往的獎勵。主人公選擇服從正是滿足了工會韓主席行使“使人服從的權力”獲得的心理獎勵感。作為交換結果得到了“我每斤香菇給你三十五塊”的承諾,看似高出“我”每斤香菇三十元的預期,但主人公并非唯利是圖的生意人,對價格并不敏感,換言之,“我”求人不是為了金錢;所以不太關注錢之多少給我帶來的心理獎勵,而是給李風叔叔幫忙這件事情的成功與否。主人公以犧牲金錢(請客吃飯的花費)、尊嚴(被人當成小地方的人瞧不起)與健康(酒量有限被強行灌酒對身體的傷害)為代價完成了推銷任務。“不管多么屈辱,我總算給李風叔叔把忙幫成了”,其心理也是期待獎勵或感覺到獎勵的。這里既有希望得到李風叔叔尊重,也有因此類幫忙而可能得到的社會贊賞。同時,體現出“我”“篤初誠美,慎終宜令”的良好真誠的品德。可是周蜜破壞了這一切,她早期的追求者財大氣粗的黃克萬使李風叔叔需要萬般求人的問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此時“我”忍辱負重,“好像受誰欺負了”,為李風叔叔所作的努力都在一瞬間變成了負值。負價值越高,人們就越有可能中止該項行為。主人公“從今往后,你再也不要找我給你幫忙了”的心理也在情理之中。
李風叔叔多次找“我”幫忙雖然使“我”損失慘重,并且“我”也告訴他再不必找“我”同時也下定了決心再不給他幫忙。可最后他還是選擇了來找“我”幫忙調動周蜜的工作。也是基于,“我”雖然損失重大但并沒有在李風叔叔面前承情使他過份難堪,同時前兩次“我”都盡心盡力給他辦了,雖然結果出人意料,但對李風叔叔來說卻得到獎勵了,所以他為難時會再三想到“我”。喬治·霍曼斯的刺激命題認為:如果人們在過去因對某種刺激作出某項行為而得到獎勵,那么,一旦今后出現的刺激或情況和過去越相似,他們就越有可能作出同樣或類似行為。“我還是不打算給李風叔叔幫忙”因為前面積累的負值太高,實在很難看出“我”有幫忙的動機和行為了。社會心理學的基本預設:趨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李風叔叔強人所難的行為也是符合這一原則的,當他一生不惜代價維護的婚姻受到沖擊時,一心指望“我”幫忙時,讀者真的能體會到一個“六十開外的人了”的男人失去權力后被剝奪時的絕望與蒼涼。“我”最后選擇再次給李風叔叔幫忙時可以理解為是社會因素對心理因素的主導作用和人的生活目的的象征意義的作用,才使“我”有了去幫忙的動機。李風叔叔此次給出需要幫忙的理由是幾乎要失去他為之奮斗了一生的女人“周蜜”。
第三次幫忙時不僅重復了前一次的請客之事還送了禮(行賄活動冒違法風險),竟然還使少兒時就有溫暖記憶“仿佛我們是青梅竹馬”的朋友小棗受侮。小棗與李風叔叔與“我”的情感體驗是同一層面的,犧牲小棗的情感對“我”而言比不幫李風叔叔而帶來的內疚感更痛苦,由此體驗到的心理挫敗感會更大。因為“我”此前已經給李風叔叔幫過忙了,作為補償性的內疚程度要輕得多;而對小棗情感的喪失會嚴重傷害到“我”的情感底線,甚至會導致終生內疚。李風叔叔的事情終辦成,“周蜜”的調令下了,但“我”卻不會從中體會到任何成功的喜悅。社會交換論者提出如下公式:reward(報酬)—cost(代價)=outcome(后果)。上式中報酬包括物質財富、心理財富(精神獎勵、鼓勵等)、社會財富(身份地位、聲望);成本包括體力、時間、放棄享受、忍受懲罰、精神壓力等。上式中交往方如果覺得后果相等,則體現的是公平,大家心理上是平衡的,結果就會繼續交往。[3](p128)如果交往方覺得后果是小于期待的,則體現的是會抱怨、消極投入、憤怒結果是中止交往。如果交往方覺得后果是大于期待的,會體驗到內疚,會有補償行為。因此,無論此次幫忙的結果如何大家都能知道“我”的負價值性“我一連許多天都萎靡不振”。
喬治·霍曼斯的剝奪——滿足(或厭膩)命題認為:人們在近期內獲得獎勵的數量過多就感到這種獎勵的價值正在變小而產生滿足感。造成“幫忙”行為的始作俑者周蜜正是這一命題的典型體現。十九歲如花似玉的周密與厚嘴黑皮膚已經謝了頂的年近四十的李風叔叔年齡外貌皆不般配,“她不顧一切的嫁給了李風叔叔”,從此她就獲得了同齡人艱辛奮斗一輩子也難有一樣的好處。機會極少俗稱鐵飯碗的“民轉公”指標、從鄉村小學調入鎮小學、當教師必備的文憑。這些都是李風叔叔享受周蜜提供美色的而給予她社會資源方面的回報。在日常生活中,李風叔叔也是任勞任怨侍候周蜜毫無怨言。可以說從社會生活到家庭生活她都處于李風叔叔給予的獎勵之中,這種持續的數量多到數不清的獎勵使她感到價值正在變小而產生滿足感。助長了她不明事理和貪得無厭的滿足感。即使在李風叔叔退休(失去權勢)后社會資源嚴重匱乏的情況下,她依然只考慮到自己的需求“突然想跳槽”,讓他去四處求人。幫忙者“我”在艱辛的一次次幫李風叔叔滿足她的需求(近期內獲得獎勵的數量過多)時,其表現出來的態度就是極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結果,就如剛飽餐過一頓的人再給來一頓美味,已經沒有吸引力一樣的滿足感。用霍曼斯的成功命題也可解釋這一行為:人們雖然有種種行為,但某項行為獲得報酬或槳勵的次效越多,人們就越有可能去從復該項行為。人們行為的次數取決于得到獎勵的次數,同時人們會由于得到獎勵的份額固定不變而逐步減少行為次數。
當她發現與李風叔叔之外的其他男人交往中這種競爭性的產生使刺激具有了不確定性,由此更易引起心理興奮感,如賭徒一樣收獲的多少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身處其中的過程本身就能帶來無盡的快樂感。霍曼斯認為,人們所以積極從事釣魚、打獵,甚至沉湎于賭博,即使收獲很少,也樂此不疲。正是由于這類行為的特點是得到獎勵的份額沒有一定規律,已經財大氣粗的早年的追求者、好色的經理等等男人對她的追求引起的刺激感相對于“六十開外的人了”的男人失去權力后的李風叔叔而言是不言而喻的。[2](p55)盡管李風叔叔“尖起腳來做長子”,但他與周蜜的交換活動不取決于他的意愿。正如社會心理學家布勞承認的那樣:不公平交換也是社會交換的主要形式。李風叔叔選擇為了愛情放棄事業發展,但社會交換只是一種有限的活動。“社會交換能否繼續進行取決于對方的反應,如果人們沒有得到預期的獎勵反應,交換就會中止”。[2](p57)顯然退休后的李風叔叔無論多么努力,已經無法使周蜜得到預期的獎勵反應,她最終選擇了中止交換活動“她和我離婚了”。
這也是老夫少妻這種生活方式普遍呈現出的實際情況,他們在選擇的時候交換規則就注定了最后的結局。就失去權力后的男人的困境這一點而言,是他本該一開始選擇時就意識到的風險。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離姻成本過低,使得結婚離婚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構成的傳統婚姻模式的超穩定性已經受到了極大沖擊,“夫唱婦隨”、“夫婦順”等結構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在的社會狀況已經是一對夫婦要成功地度過一生,雙方都要付出極大地努力與感覺上是對等的代價。李風叔叔與周蜜的婚姻生活中,當他們的付出與期待是平衡的時候,他們是恩愛的;一旦失衡則分手在所難免。
喬治·霍曼斯的社會交換理論,與中國以傳統血親情理為根本理念構成的人際關系中“人情”、“幫忙”等特有的現象看似毫無關聯,西學東漸這么多年的結果使得中國的普通市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都受到了重要的影響。社會交換理論的五個命題的提出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在當今的中國社會生活事件中也可以得到檢驗,其可檢驗性也說明中國當今社會更趨向于西方化,民眾對外來的西方文明的接受承度也越來越深入和廣泛了。代價必定是本國的傳統文化會以驚人的速度流失,甚至可能會徹底地消失,這是中國文化人必需面對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1]曉蘇.給李風叔叔幫忙[J].小說月報,2010,(12).
[2]談谷錚.霍曼斯和布勞的社會交換論[J].社會科學,1986,(10).
[3]杜·舒爾茲,西德尼·埃倫·舒爾茲.現代心理學史(第八版)[M].葉浩生,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