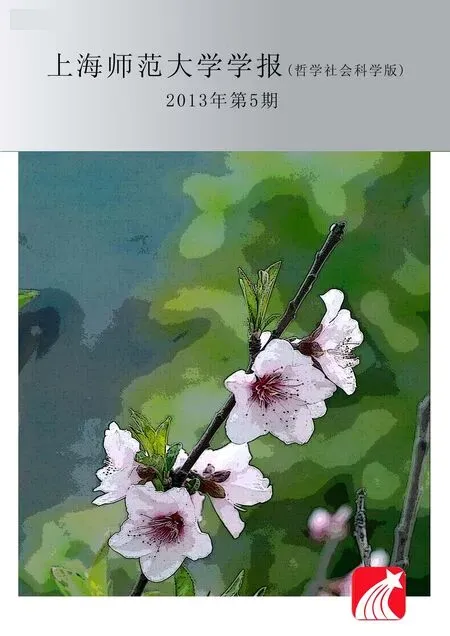論漢語文白演變雅俗相融的價值取向
徐時儀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234)
語言永遠處于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要全面、深入、系統地了解語言,就必須探索語言發展中決定變與不變的主要因素和規律。研究語言變化的最佳切入點則是語言變異,因為語言的歷時演變總是能在語言的共時變異中得到體現,語言的發展是在變與不變的對立統一中進行的。如果說20世紀前語言學的研究主要是對語料的搜集和整理,借以研究語言的規則與特點的話,那么今天研究語言的共性和決定語言變與不變的機理則是當代語言學研究發展的趨勢。①
漢語詞匯在由古至今的發展中有變,有不變;有變化大的,有變化小的。至于為什么變,怎樣變,為什么這樣變而不那樣變,則既有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又有人們具體取舍的價值取向,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交融。詞匯的演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既是鏡,也是燈,不僅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語言演變,而且也折射出各個時代不同階層人們的意識、情感和心靈狀態。語言在反映客觀外界的同時,也體現了使用者內在的主觀思想。語言的演變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使用者自我意識的發展水平,尤其是漢語文白的演變可以說更真實更細膩地記錄了人們的思想傾向和意識情感。漢語詞匯的古今發展和文白演變不僅體現了“言語意義←→語言意義”和“口語←→書面語”整合融合的動態演變,而且也體現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階層的人們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必然發展趨向,即典雅的精英文化與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相融合的價值取向。
一、言語意義←→語言意義互動交融
“言語”和“語言”是一組相對的概念。語言是社會成員經過約定俗成的靜態符號系統,具有交際工具的客觀性、概括性、規約性、社會性和相對穩定性;而言語則是人們運用語言這種工具進行交際的過程和結果,具有靈活性、具體性和臨時性。語言是說話人能做什么,是靜態的;而言語是說話人實際做了什么,是動態的。語言是從言語中抽象概括出來的,來自于言語;而言語活動雖在語言約定的規則內進行,但還具有個人特色,且每個人每一次說話都是不同的。語言系統的各個結構成分(語音成分、詞的數量和構詞規則等)是有限的;但在具體的言語活動中,作為一個行為過程,人們所說出的話是無限的,每個人都可以說出無限多的話語。大致而言,語言是言語活動中同一社會群體共同掌握的、有規律可循而又成系統的交際工具;言語則是個人對語言的具體使用和使用的結果。
語言的詞義含有言語意義和語言意義。詞義處于獨立或靜止的條件下不受語境的制約,這時的意義是語言意義。語言意義進入交際過程即言語活動中,受到語境的影響和制約發生一定的變化,形成言語意義。②言語意義是交際活動中語句所包含的和傳達出來的全部內容。言語意義的核心部分是語言意義,語言意義指語言體系中所固有的意義。語言意義是常體,即言語意義的綜合和概括,有相對凝固、穩定和多義的特點;言語意義是變體,具有靈活、多變、具指和單一的特點,其內涵要比語言意義豐富得多。言語意義除了語言意義之外還有附著在核心成分之上的語境義。語境義指的是交際時的一些具體情境,如時代背景、上下文、個人修養、習慣、經驗、知識等因素起作用而產生的臨時意義。語言意義和語境義融合在一起,構成具體的言語意義。言語意義為一定的現實交際目的服務,而交際又都是在特定語言環境中進行的,語境對言語意義有制約作用,單義詞在語境制約下實現了具指化,多義詞在語境制約下實現了單義化與具指化。言語意義可以說是說話者與接受者在交際過程中互動的產物,在交際過程中說話者往往需要根據接受者的反應調整話語,接受者也需要根據對說話者所說話語的理解作出相應的反應。言語意義的變化又影響語言意義的變化,語言意義吸納言語意義的變化從而形成了語言中詞義的古今演變。
語言的發展從縱向的觀點看是一種歷時的演變。不論是詞的分合、疊置或遷移、轉換,都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積,而是經過不同歷史層次的變異而形成。從橫向的觀點看是一種共時的演變,不同歷史時期傳承下來的成分并存整合成一個新的系統。語言表達功能決定語言形式,歷時的變異與共時的整合是語言存在和發展的兩種基本形式。這兩種形式交替進行,相互作用,使言語意義←→語言意義既能承傳不斷,也能與時俱進,表現了語言系統不息的生命力。
不同的交際場合和語境對語言的使用有不盡相同的要求,從而形成不同的語體。語體是一系列言語特點的體現。如既有《史記·儒林傳》所說“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的“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的某些詔書律令,代表傳承的語言意義;又有白居易所作老嫗能解的詩,反映鮮活的言語意義。無論是帝王的詔令還是文人的詩詞,從中皆可見雅俗間言語意義←→語言意義的互動交融。又如《朱子語類》所載朱熹講學內容多為師生即時的問答,出于講學的需要和特點,創意地利用了多種表達手段,有時用當時語言的表達方式,有時又用典籍所載語言的表達方式,師生間在問答時選擇何種語體取決于說話者表義的動因,往往表述事件發展的具體進程多用俗白體,表述思想或進行評價多用雅語體,文白相間,雅俗共融。尤其是朱熹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講學內容用詞不盡相同,來自不同地區不同的門生所記又有同有異,其中包含有各種性質和各種層次的言語成分,既有承古的文言和成語,也有當時的白話和習語,反映了“言語意義←→語言意義”的動態演變,體現了漢語詞匯發展演變淵源有自的傳承性和吸納口語的開拓性。朱熹講學時門人弟子往往邊聽邊記或課后互相傳記,大多不暇加工而直錄原話,可以說活生生地反映了師生這一階層間的語言交際實況,且后世傳刻刊印的各本也多有異文,從這些無聲的詞語改動中也可“聽”到編刻者所說的一些有“聲”語言與宋代所說語言的不同,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前后相近的幾個時間點上語言變或未變的珍貴線索,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③從朱熹門人弟子的記載也可見雅俗間言語意義←→語言意義的互動交融。④
二、口語←→書面語共存交融
語言作為社會交際的工具,一般都有口語和書面語兩種表達形式。口語是訴諸聽覺的“說”的語言,書面語是訴諸視覺的“看”的語言。呂叔湘曾說:“世界上沒有,也不可能有,完全沒有口語做根底的筆語;文言不會完全是人為的東西。可是文言也不大像曾經是某一時代的口語的如實的記錄,如現代的劇作家和小說家的若干篇章之為現代口語的如實的記錄。”⑤從語言本身的發展而言,語言不僅通過一代一代的口耳相傳,而且文字產生以后也通過書面的記錄得以傳承。今天的口語實際上是前人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融合體。漢語的書面語有文言和白話兩個系統,文言是以先秦兩漢的書面語為模式的一種書面語,白話則是與文言相對而并存的一個反映了東漢至今歷代口語成分的漢語書面語系統。兩者同源殊途,既有不同,又互有聯系。白話雖與口語關系密切,但又不等同于口語。研究語言演變主要依據口語或口語的記錄,口語或口語記錄的語言研究價值取向在于這些語料能夠全面真實地反映當時語言的實際面貌。語言在演變發展中,一方面是口語成分被吸納到書面語中,另一方面書面語成分有時也會被口語采用,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雅俗間的互相吸納,互相滲透。語言的發展不僅存在“言語意義←→語言意義”的動態演變,而且也是“口語語辭←→書面語文辭”的不斷轉化過程,書面語和口語之間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兩者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表現形式,基礎是共同的而區別則是局部的。⑥如“眼里沒人”是口語體,“目中無人”是書面語體。又如“改改這句話”是口語俗白體,“此句欠妥,宜酌情刪改”是書面典雅體,而“這個句子必須修改”則為正式規范體,介于口語俗白體和書面典雅體之間,口語和書面語都用。⑦再如我們面對一些具體的詩文時,往往難以斷定其性質究竟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呂叔湘在《文言和白話》一文論及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話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定下明確的界說。⑧朱光潛《文學與語文》一文也論及多數文言文作者口里盡管只說先秦兩漢,實際上都是用“一爐而冶之”的辦法“雜會過去各時代的語文”。⑨張中行《文言和白話》在談到文白界限時曾例舉了六種文白混用的情形,涉及樂府詩、佛經譯文、曲子詞、話本、章回小說、文人筆記等多種文體。⑩由文白界限的模糊亦可見雅俗間“口語語辭←→書面語文辭”彼此影響滲透的互動交融。一般來說,官方政府的文書多為正式規范體,學術研究的論著多為書面典雅體,文學藝術的創作則或鐘情典雅或青睞俗白或兼有兩者,而人們在家說自己的方俗口語,在外使用通語,在正式公共場合則使用雅語,由此形成莊雅與俗白之別。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由于口語旋生旋滅,古人無法利用錄音設備錄下自己說的話,時至今日,我們只能依據古人記錄下來的書面文獻來探索這些當時有聲的語言反映的漢語古今演變。這些書面文獻雖已是經過加工的口語記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因種種因緣往往直錄或書面加工不多而記錄了當時所說原話,從中可還原出當時的語境,“聽”到紙上所載的有“聲”語言。
從詞匯的角度來看,有大量的詞匯成分既適用于口語,也適用于書面語,而從口語語辭到書面語文辭的擴展,體現了雅俗相融互補的自然過程,形成了口語和書面語并存不斷完善的語言發展模式。這種雅俗相融并存的不斷完善,不僅是語言發展的模式,也是文學、思想、藝術和宗教等發展的模式。如敦煌文獻中形式豐富多樣的講唱文學,既有宣揚佛教教義的講經文,又有韻散相間敷演佛經故事的講唱文,適應文人精英到一般大眾等不同階層的需要,兼顧了不同層次受眾接受信息的能力,具有通俗化和生活化的特點。講經文和講唱文互相影響,兩者在傳承文賦傳統基礎上融合而衍變為變文,進而又產生《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話本。這些話本具有口耳相傳的口語和書面加工的文本的雙重屬性,其中說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講史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后又為文人加工,敷演撰成長篇章回小說《西游記》和《水滸傳》。又如,朱熹講學時用當時的口語解說儒家經典,門人弟子筆錄下來整理成《語錄》刊行,后又在各家所記筆記的基礎上匯編為《朱子語類大全》,而朱熹所撰《詩經集傳》、《周易本義》、《四書章句集注》和《四書或問》等著作及宋張洪編《朱子讀書法》、清李清馥撰《閩中理學淵源考》等,則把朱子講學的口語加工為書面語,體現了古語和時語的雅俗相融,而儒家的學說經二程和朱熹等諸家的闡釋形成為理學。再如兩漢之交,佛教傳入中土后,華嚴宗和唯識(法相)宗吸引上層高僧大德們剖判入微地研習精理奧義,凈土宗吸引一般僧俗民眾整日念“阿彌陀佛”來到達極樂世界,禪宗則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而盛行于官方與民間。釋迦牟尼的教理經隋代智顗、吉藏和唐代玄奘、窺基、弘忍、神秀、慧能、神會、法藏、宗密等高僧在不同層次上的鉆研加工,從玄奘創立的慈恩宗由盛而衰到慧能的禪宗繼之而興,幾經演變而形成中國的各宗派,進而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成為上至帝王學士,下至市人村民,雅俗相融的一種宗教信仰。因而就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演變軌跡而言,在先秦口語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文言文可以說是由俗到雅,在秦漢以后口語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古白話則可以說是口語和書面語交融碰撞互為影響,在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雅俗合流基礎上有所甄選乃至舍棄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話語生態。
三、本土文化←→外來文化碰撞交融
語言接觸是語言相互影響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起因,語言接觸可以深入到語言系統的各個層面,語言接觸導致的語言變異可以涉及到語音、詞匯和語法,而社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則決定了語言接觸的深度,即決定了一種語言受另一種語言影響(干擾和借貸)的方向。中國歷史上永嘉、安史、靖康之亂造成的南北分裂,對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可以說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語言也隨之而有較大的變化。如東晉在江東建國,身處吳語氛圍,同時南渡移民又帶來了“中原正音”,兩者相融合形成了當時的官方語言“江淮話”。如果說南遷的名士們鄉音難改,說吳語只是入鄉隨俗,他們的子孫輩說的話則與南方吳語水乳相融。又如清代滿族進京,其時京師“言龐語雜,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話、土話、官話,久習者一聞而辨之”。今天的北京話是東北旗人話和北京老話以官話為中心合起來的,成為普通話的基礎。
任何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都不會是簡單的復制和移植,而是相當于化學變化的互化整合,作用于受眾并最終為接受者接受。本土文化←→外來文化的交流往往產生碰撞和交融,在整合過程中往往產生新物質或新概念,導致主體文化一定程度上的變異。如西漢末東漢初佛教的東傳、漢魏至唐五代大規模的佛經漢譯,導致了漢語與梵語等語言的接觸,形成了漢譯佛典不同于文言的特有句式。又如遼金元時期契丹和女真及蒙古族入據中原,各民族間的交融加強了語言的交流,不僅南北語言不斷融合,而且本土和域外語言也有雅俗的交融,形成北方一帶地區通用的“漢兒言語”。尤其是元代統治者為了維持其統治,不得不學習漢語。他們學的漢語自然不可能是高深典雅的文言,而必然是當時通行的口語白話。元代皇帝要了解漢文典籍,由漢人大臣用當時的口語來詮釋講解,寫下來成為白話講章。元代的詔書敕令等都是先用蒙古語寫成,然后譯成漢語白話,形成能讓一般平民大眾也能看懂聽懂的白話公牘和白話告示,通行于全國,以其時口語為規范基礎的書面語與蒙古語同時成為元代的官方語言。這促使雅俗相融的北方通語進一步擴展至南方,形成在北方原有雅俗相融格局基礎上的南北交融,達到新的雅俗融合,上層的雅言介入日常生活口語,下層的便俗語介入書面語,漢語書面語也由文言向白話定位,白話成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溝通的應用語體,客觀上也推動了文白此消彼長由量變向質變的轉化,初步形成文白轉型的雛形。
由于南朝的政治相對來說比較穩定,上層精英和底層平民的語言有雅俗之別;而北方戰亂頻仍,士族紛紛南遷,氐、羌、鮮卑、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遷入與漢族雜居,這些少數民族與漢族交際所說語言自然是當時的口語,也就是底層一般平民的語言。同時,雖然漢族高度的文明逐漸同化了這些民族,但在同化的過程中由于這些少數民族人數眾多,必然會帶來其自身的語言特點,如同成年人學外語難免帶有自己母語的一些成分,而為了交際的需要,即使北方處于社會上層精英地位的漢族士人也必然會在語言的有些方面作些遷就和讓步,如同我們與說不同語言的人交談時在語言上彼此都會包涵和容忍一些,因而上層精英和底層平民的語言趨于更多地相融,相互間的差異減少,形成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下所說“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的局面。北方金元統治者與平民百姓的雅俗相融導致了中原原有的語言系統的調整,從而在原有語言系統基礎上形成了反映當時口語的通語,為今天北方大方言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明清至民國的西學東漸又形成一種新的話語生態,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沖擊導致了漢語與歐美語言的大規模接觸,產生了大量新詞語,不僅促使漢語文白轉型順應時代變革由量變到質變,在古白話基礎上承文言的雋永凝煉,同時汲納歐化語言成分,形成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新白話,而且從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兩個層面豐富了漢語的概念系統和觀念系統,擴展了人們的思想空間和科學思維能力,形成了構筑新時代突破傳統范式體現中西會通的新思想體系。
四、社會底層←→社會上層流動交融
社會成員流動性和不同社會階層間的交往交際交織在一起,成為語言變化的重要因素。如魏晉南北朝、唐末五代和宋金元之際戰亂等造成的社會大動蕩、人口大遷徙,形成社會底層和上層以及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流動交往。一批由布衣素族進入上層皇室的新貴有別于門閥世族,所說自然夾以底層平民的語言,形成社會底層和上層的流動和語言的雅俗交融。又如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重要的選官制度,科舉制使有才識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各級政府任職,士人的主要出路是科舉,一些平民子弟躋身仕途,一些官宦子孫則淪為平民,科舉也造成了社會底層和上層的流動以及語言的雅俗交融。
唐代仕途開放,“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大批出身低微的士人進入權力中心。宋代太祖趙匡胤鑒于“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改革科舉制度,由皇帝親掌取士權,嚴密科舉條制,實行“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原則,取士不講門第,凡是粗具文墨的士人,不問貧富和出身,皆可應舉,廣泛吸引知識分子走科舉入仕之路,寄之以重任,委之以大命。這既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權的鞏固,又推動了社會經濟、文化、思想和科學技術的繁榮與進步。雖然有幸進入政權的士人并非全是人才,但在“居今之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的社會氛圍下,可以肯定地說,這些進士中幾乎囊括了全部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代表當時的精英。特別是從宋真宗朝后期起,隨著科舉制度進入黃金時期,大量人才亦隨之陸續涌現出來。以宋仁宗一朝為例,出類拔萃、彪炳史冊的不下數十人,為歷朝歷代所罕見。其中著名的有余靖、晏殊、范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包拯、張方平、司馬光、王安石、曾鞏、劉攽、劉恕、蔡襄、蘇軾、蘇轍、蘇頌、沈括等,既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學家、文學家、史學家和犯顏直諫、風節凜然的諫臣。
唐宋由科舉進入官場的士子多數出身于平民之家,入仕前生活在社會底層,說的是平民的俗語,入仕后在官場說雅語,在家或與親友自然還是說家鄉話,形成類似《紅樓夢》中賈政所說的話與劉姥姥所說的話的共存互補。這些平民出身的士子金榜題名進入社會上層,所說語言在趨雅的同時,也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教化、自下而上的諷諫這種雙向關系的雅俗交融。
五、趨雅←→趨俗互補融合
語言是人類思維的載體和交際的工具,人們用彼此約定俗成的符號表達意義,約定俗成是特定時空中特定人群無需言明的“集體無意識”默契,而交際既發生在同一階層間也發生在不同階層間,語言交際是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進行的。什么符號表達什么意義,不能任意改變,否則就會造成交流中的不理解。然而就客觀而言,社會在發展,時代變了,新的事物出現了,就不得不增加新的詞語和句式來表達。就主觀而言,交際的語境具有認知動態性,即說者和聽者的話語理解不是預先確定的,而是彼此在言語交際中對語境假設的不斷選擇、調整與順應。說話人與聽話人在認知語境上越是趨同,交際就越易成功。交際過程實際上是雙方認知語境信息或假設的趨同過程,而語言表達總是在既遵循常規又不斷超越常規的狀態下進行的。人們在交流中可能會無意識地略微偏離約定俗成的表達,也可能會有意地標新立異,兩者都是用原來沒有甚至不容許的說法來表意。這類偏離的表達大多由于不為約定俗成的說法所接受而消失,但也總會有一些出于交際時可以包涵和容忍的遷就和讓步而生存下來,逐漸為大家接受,習而成俗,成為新的約定俗成的表達。如“很陽光”、“很中國”,“很”作為副詞本不能修飾名詞,現已為人們認同。又如“被幸福”、“被小康”,“被”用作被動式帶名詞的表述也已為人們接受。因此語言在人們交際使用中會不斷地變化,而交際既發生在同一階層間,也發生在不同階層間,語言交際是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際者的社會關系、交際目的、態度等。如表達相同概念,上下輩社會關系不同,用語則有簡體和敬體的不同。從交際過程中的編碼和解碼來看,說寫者和聽讀者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質對詞語、句式等的選擇都有影響和制約作用。語言既是精英文化的載體,也是平民文化的載體,既是本土文化的載體,也是外來文化的載體,不同階層不同文化各自使用的不同詞語在交際中自然會互相影響。不同文化群體使用的詞語雖有文白雅俗的不同,但交際使用中如果沒有形成對方語言的認知語境,就會出現交際障礙,交際中彼此間都有自我調節過程中的互相作用。正如說不同語言的人們為了交際的需要,在交談時在語言上彼此都會包涵和容忍一些,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遷就靠攏對方,出現雙向的“語言調節”現象,不同階層的人們為了交際的需要,在交談時也必然會在語言的有些方面作些遷就和讓步,進行語言調節,日積月累,這就促成了語言的交融和演變。如《紅樓夢》中劉姥姥和賈母、王夫人、鳳姐的交談,互相間在用詞上都自然而然地迎合對方以便于對方的理解。
一般而言,社會中的每個成員所說語言都既有通語又有方言,每個成員在社會交際時都會根據語境和交際對象等交際需要的不同來選擇通語或方言的詞匯成分。每一個成員言語能力中存在的通語和方言成分可能相互影響而進入會話交際,使得一些語言成分產生變化,一旦某個變化的語言成分在某一特定階層中擴散傳播,就意味著變化的開始,由某一特定階層內的擴散傳播擴展到此特定階層與其他階層間的擴散傳播。如果這一變化在不同階層的擴散傳播中漸為人們認同,這就導致了對這一變化的約定俗成。
如先秦漢語中的“日”和“月”,后又可稱為太陽和太陰。“太”形容極大,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最初稱“日”和“月”為“太陽”和“太陰”可能是在某一特定階層內,后在不同的階層中擴散傳播,“太陽”一詞漸為人們認同,今口語仍沿用以稱“日”。“太陰”未為人們認同而某一特定階層又以“月亮”一詞稱“月”。“月亮”本為主謂詞組,意謂月光明亮。唐李益《奉酬崔員外副使攜琴宿使院見示》:“庭木已衰空月亮,城砧自急對霜繁。”清李光庭《鄉言解頤·月》:“月者,太陰之精。然舉世鄉言無謂太陰者,通謂之月亮。唐李益詩……以‘繁’對‘亮’,言其光也。相習不察,遂若成月之名矣。或曰月兒。”據李光庭所說,“舉世鄉言無謂太陰者,通謂之月亮”,“月亮”本是鄉言這一特定階層所稱,而歷代文人吟詩作文又稱“月”為“玉兔、夜光、素娥、冰輪、金輪、玉輪、玉蟾、桂魄、蟾蜍、銀兔、玉兔、金蟾、銀蟾、蟾宮、顧兔、嬋娟、玉弓、玉桂、桂月、桂輪、桂魄、玉盤、銀盤、玉鉤、玉鏡、金鏡、冰鏡、嫦娥、姮娥、素娥、廣寒、清虛、望舒”等。“太陰”和文人吟詩作文所用“月”的雅語在某一特定階層內擴散傳播,而鄉言所稱的“月亮”在不同階層的擴散傳播中漸為人們認同,今口語仍沿用以稱“月”。
又如“郎”,最初是宮廷侍衛人員所在地,引申而稱宮廷侍衛人員,后用作官職名或作為獎勵性的封贈。由一種殊譽而為世人趨從,詞義漸泛化為男子的美稱和通稱。再如“博士”,最初也是古代學官名。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后用來稱呼具有某種技藝或專門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如《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警世通言·萬秀娘仇報山亭兒》:“家里一個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鐵僧。”這些稱謂詞最初地位尊貴,后漸由雅趨俗,從眾泛化而雅俗合流。
語言有雅俗之別,典雅和通俗是相融互補的,每一個民族都有俗文化和雅文化。俗可指相沿習久而形成的風尚習俗,如風俗、禮俗、習俗、民俗;可指平常、普通,如通俗、世俗、常俗、凡俗、俚俗;也可指鄙陋,如低俗、淺俗、粗俗、鄙俗、庸俗。雅可指正規、合乎規范,如雅正、典雅;也可指高貴優美,如高雅、博雅、莊雅、風雅、文雅、古雅、儒雅、雅致、秀雅。典雅和通俗又是相對而言的,社會的變化和歷史的發展使雅與俗相應而變。雅與俗不在于文之古今。《詩經》、《楚辭》出自民間,在當時大體也是白話,具有先秦時期野丫頭活語言的生氣,經文人加工后,去除粗俗的成分,而成為比較典雅的詩文。后世出自民間或采用口語的作品同樣具有當時野丫頭活語言的生氣,經文人加工去除粗俗成分后也可以說是比較典雅的創作。如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卷下之下《惑溺》:“賈公閭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踴,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房玄齡編《晉書》卷四十《賈充傳》改為:“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例中改“踴”為“笑”,改“嗚(親吻)”為“拊(輕拍)”,改“愛”為“私”義,把直白的口語加工為比較典雅的書面語。大致而言,無論多么時髦的流行用語,隔代不用則可變俗為雅;無論多么優雅的古典用語,濫用無度也會俗不可耐。俗都以民間隨意的下層性為依歸,雅則以歷史傳承的上層性為依歸,雅俗相互影響,雅與俗之間可相互轉化。
約定俗成可以是趨雅也可以是趨俗。交際場由說寫者、聽讀者、話語和語境構成,說話對象、場合和內容不同,用詞也隨之而異。古往今來,人們生活的社會和交際的語境大致可分為物理世界、心理世界、語言世界和文化世界。一個完整的交際場是由語言世界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組合而成的,表達者和接受者在編碼與解碼時都要受到“四個世界”的影響和制約。語言世界不是直接對應于物理世界,而是有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作為中介。人們通過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來運用語言世界,同時又通過語言世界來認識物理世界和創造文化世界、反映文化和傳播文化,而文化世界是制約表達者和接受者編碼與解碼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說社會上層的精英多用雅語,社會下層的平民多用俗語,那么趨雅是雅為俗所崇尚而向雅趨同,認同雅的優勢,模仿雅進而包容一些雅語成分;而趨俗則是雅為俗所觸動而向俗趨同,認同俗的鮮活,吸納俗進而融入一些俗語成分。尤其是在正式場合即使是平民說話時也盡可能趨雅用典雅的詞語,而在非正式場合即使是士人或官員也一定趨俗用俗白的口語。如一位校長對辦公室秘書可以說“下周的作息時間要進行一些調整”,而不會在家里對妻子這樣說。又如某位老師在教室里對學生可以說“中午用餐時不宜大聲喧嘩 ”,而不會在家里對自己的孩子這樣說。社會上層和下層的交際是趨雅←→趨俗雙向的融合,既有雅,也有俗,且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如通俗文學中的白話小說和經文人整理加工的民間說唱文學往往按照雅文化的標準作雅化,提升了俗文化的品位,具有雅與俗的雙重性格。例如明代的世情小說《金瓶梅》描寫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比較完好地保留了明代中后期都市群眾口語、客廳用語、說書人套語和隱語黑話、行業語,以及文言公文用語等多元語言的自然面貌。萬歷丁巳(1617)年間東吳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詞話》本是說話人的口講述錄,呈俗文化形態;而崇禎年間的《金瓶梅》則經過文人的加工,呈文人文化形態,往往把常俗之語改鑄為文人之言。兩個版本系統大致反映了其時口語與書面語的異同和雅俗融合的價值取向。又如日常生活用語和新詞新義為雅俗所共用,不僅出現在各階層人們的口中,而且也出現在文人的筆下。例如《紅樓夢》第十回:“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又如《三刻拍案驚奇》第十九回:“既是央他換,怎的分量曉不得?”例中“了不得”、“曉不得”都是當時口語詞。
如果說文人間交談時多用雅語,平民間交談時多用俗語,那么文人與平民間交談時就會是雅俗并用。文人吸納俗語且日常生活中也說俗語,在寫作時或作加工或直接寫進書面語,化俗入雅,俗語漸為書面語吸納又成為雅語。如由根據三國正史及民間傳聞說唱的“說三分”寫成的《三國志平話》到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原有的口語往往被改寫成書面語。又如北宋詩人陳師道吸取當時的諺語,把“巧媳婦做不得沒面食不饦”、“遠井不救近渴”和“瓦罐終須井上破”等改寫成“巧手莫為無面餅,誰能留渴須遠井”、“瓶懸瓽間終一碎”等七言詩。與此相同,文人的雅語有時也會被平民口語采用,融雅入俗,雅俗合流。如姜子牙“直鉤垂釣”的故事本為文人學士筆下津津樂道的典故,經元人編《武王伐紂平話》和明人改編《封神演義》的加工而進入平民口語,形成“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這一婦孺皆知的歇后語。
六、結語
語言演變發展的動因在于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的發展要求語言的同步發展。詞匯是語言中最活躍的要素,反映社會變化最敏感,經常發生變化,詞匯系統也相應地處于動態的變化中。由于社會的變化、新事物的產生和新概念的出現,詞匯系統同樣也是一個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開放的系統。新質要素的產生必然帶來舊質要素的消亡,新陳代謝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詞匯的發展過程,概括說來,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也就是詞匯新質要素的不斷產生和舊質要素不斷衰亡的過程。詞匯的發展變化不僅涉及到詞量、詞音、詞形、詞義、詞的用法和類屬,而且也涉及到詞和詞之間的各種關系等諸多方面。這些變化對于整個漢語詞匯來說是量變或局部質變,而積累到一定的階段則可能是質變。語言的發展又具有漸變性和參差性。就語言發展的漸變性而言,漢語文白轉型是在文言和白話此消彼長的基礎上形成的。就參差性而言,文白的轉型有各種因素的影響。漢語的文白演變是同一語言內口語形式和書面語形式的語體轉型,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既是表達功能的需要,也是雅俗相融的價值取向,隱含著價值觀念的更新,涉及到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等多方面,其中也涉及到語言的接觸和方便更多人運用語言的平民意識。
白話最終取代文言成為當代中國人文化交流和文學創作的基本工具,大致上可以說是言語意義←→語言意義、口語←→書面語、本土文化←→外來文化,以及社會各階層間趨雅←→趨俗互動共存與整合融和的合璧,而現代文化的形成也是典雅的精英文化與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相融合的產物。漢語詞匯的古今發展的總傾向是向通語靠攏,既有從歷時的角度看是當時新出現的白話口語成分,又有從共時的角度看是傳承歷代的文言書面語成分,既有“陽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既有本土文化成分,又有外來文化成分,從而形成隨著口語的變化而發展的現代漢語。漢語的文白轉型在某種程度上正體現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階層的人們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必然發展趨向,即精英文化與平民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雅俗相融互補的價值取向。
注釋:
①參拙文《略論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傳承和發展》,《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②詞義最初形成時總是處于原始的渾沌狀態,內蘊著人們對客觀事物各種特點各自的不同認識,在交際使用中漸漸由渾沌而明晰,約定俗成為大家認可的詞義。參拙著《近代漢語詞匯學》第四章第一節《詞義構成與類型》,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③參拙文《詞匯擴散與文獻傳本異文》,《中國語言學報》第13期,商務印書館2008年。
④參拙文《〈朱子語類〉知曉概念詞語類聚考探》,《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⑤呂叔湘:《文言和白話》,《國文雜志》1944年第3卷第1期。
⑥約瑟夫·房德里耶斯《語言》曾說:“人們永遠不會像說話那樣寫作。人們寫(或力求寫)得像別人一樣。哪怕最沒有教養的人一旦拿起筆來就會感覺到他們所用的語言與口語并不一樣,它有它的規則和它的用法。”岑麒祥、葉蜚聲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364頁。
⑦口語體適應俚俗的語境,如順口溜和二人轉等;書面語體則適應高雅的語境,如外交辭令和政論文等。
⑧《呂叔湘語文論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⑨朱光潛:《談美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220-222頁。
⑩張中行:《張中行作品集》第一卷《文言和白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93-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