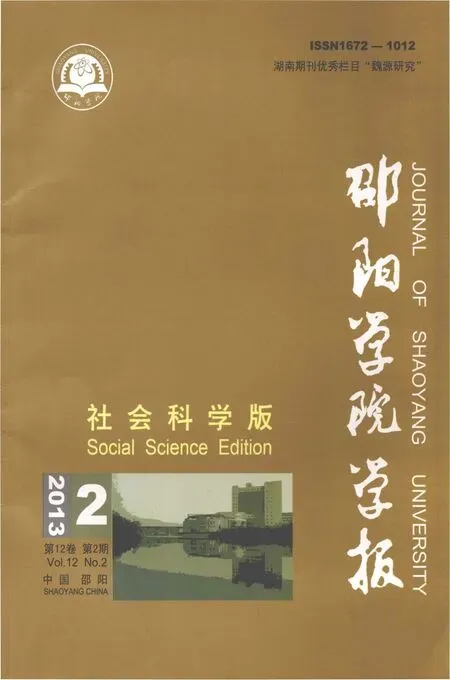兩種創作情結的相互扭纏——丁玲向左轉時期的創作心態分析
陳紅玲
(邵陽學院 中文系,湖南 邵陽 422000)
丁玲一生的創作曾有過幾次明顯的轉型。閱讀丁玲在1929 年冬至1930 年底的創作文本,我們發現:丁玲的創作明顯地從早期的“莎菲”天地里走出來,放棄了自我傾訴式、自我剖析式的敘述方式,運用“革命加戀愛”的敘事模式,表現革命與愛情的沖突,實現了創作的向“左”轉。針對這一轉折,馮雪峰給予高度評價:“丁玲所走過來的這條進步的路,就是,從離社會,向‘向社會’,從個人主義的虛無,向工農大眾的革命的路”。[1]丁玲在此期間的創作,盡管她主觀意識上趨同當時最流行、最先鋒的革命文學思潮,在作品中注入“革命意識”這一創作新因素,創作了長篇小說《韋護》、中篇《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及數個短篇。然而,“革命意識”這一主導性的創作新因素,并沒有完全擠占掉丁玲原有的個性創作因素,潛意識中仍保留著“五四”個性化創作立場。“我最后一本《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作風的書,是《韋護》,出版于1930 年。這本書的作風是夠寫實的,但內容可是浪漫的。”[2]丁玲的這段自述充分說明,此時,她創作風格雖已改變,已經傾向于革命文學,但作品內在仍保留一貫的浪漫內容,“與其說是寫革命與愛情的沖突,不如說是寫革命為虛,寫愛情幸福纏綿、相思苦惱為實。”[3]。作品中兩種創作思想情結的扭纏不清,也表明處在創作轉型期的丁玲創作心態具有矛盾性。
一、在顯意識層面,創作轉向革命文學
上世紀20 年代末到30 年代初,最流行、最先鋒的文學思潮是“戀愛+革命”的左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丁玲的創作緊隨此潮流。1930 年1 月5 日發表于《小說月刊》第2 卷1 至5 號上的《韋護》,是丁玲創作趨從“革命+戀愛”寫作模式的標志。將《韋護》列入普羅小說,丁玲開始似有不服,但還是承認“陷入戀愛與革命沖突的光赤的陷阱里去了”[4]。《韋護》這篇小說是取材于瞿秋白與王劍虹的戀愛故事。但作者在創作上有了重要的突破。“這突破主要表現在它正面地、突出地寫了革命,寫了共產黨人,寫了革命的理想戰勝了小資產階級溫情的愛情觀;并著力寫了具有濃厚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女知識青年麗嘉的思想轉變。這實際上突破了真人真事的限制,也突破了當時最流行的‘革命+戀愛’的創作局限。”[5]宋建元的此段評論是對丁玲創作轉向的肯定,特別是對作品中革命戰勝愛情描寫的肯定,也道出了丁玲此類小說與當時風行的“革命+戀愛”小說的相異之處。事實上,丁玲作品中戀愛和革命相沖突的主題,不同于蔣光慈之流早期小說戀愛和革命簡單相加的寫作模式。[6]丁玲晚年對自己的這一轉折有過論斷,她稱之為“突破”。她認為《韋護》的題材范圍有所突破,而在《田家沖》和《水》中,則是“自己有意識地要到群眾中去描寫群眾,要寫革命者,要寫工農”[7]。這屬于思想意識的突破。的確,1931 年隨著小說《水》的發表,丁玲告別了“革命+戀愛”的寫作模式,標志著“新小說的誕生”。
究其原因,丁玲的向左轉與當時的左聯作家們的左轉還是有所不同的。“魯迅等人的向左轉,是以窮盡啟蒙主義作為其思想前提的。而在丁玲這里則可以說是以遭遇并窮盡個人主義話語的困境作為其思想前提。”[8]丁玲的向左轉并不是突然的轉變。二十年代末期,政治上的挫敗迫使激進知識界對文學產生了新的期待:文學不但要承擔反抗舊文化舊道德的使命,它還應該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前途與命運作出切實具體的回答。其間,魯迅、茅盾、葉紹鈞、郁達夫等“五四”作家受到了強烈的否定性的攻擊,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新文藝思想引發了“五四”文學“向左轉”的急劇變化。隨著當時社會形勢的變化,丁玲在思想上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再加之,丁玲當時對自己的創作情況也很不滿意,創作上也需求改變。她不愿只能夠寫出一些只有感傷主義者所最易于了解的感慨。但她也不喜歡胡也頻轉變后的小說,如《到莫斯科去》。她認為他的這種創作犯的是“左傾幼稚病”。她當時的想法是:“要末找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末寫文章”。[9]雖然此時丁玲還未能把革命與文學聯系起來看待,但在后來的客觀創作實踐上,她還是把革命與文學結合起來了。《韋護》、《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就是這種結合的有力佐證。“1930年丁玲創作發生了轉變,這轉變可以說由女性作家危機與意識形態特點合力促成。”[10]
在“革命+戀愛”小說中,作家表現的是知識分子拋棄個人主義,投奔大眾集體革命的思想觀念,丁玲的作品也不例外。韋護(《韋護》)為了革命而拋棄愛情;美琳(《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離開個人主義者子彬,走向革命大眾;個人主義者瑪麗(《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因為不革命而成為男性世界的包袱兒遭到拋棄。丁玲的這些作品又復原了她曾經顛覆和置換了的傳統兩性關系。在丁玲的“莎菲”時代,女性是絕對的主角,但在她的轉型代表作《韋護》、《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中,男性成為了小說的主角。韋護、若泉、望微都是革命者,他們意志堅定,投身社會革命。為了革命事業,甘愿拋棄愛情,拋棄個人幸福。而其中的女性角色則降至次要地位。她們一味耽于愛情,政治上冷漠,生活上慵懶,只為愛情活著。在此,女性成了男性形象的反襯。早年男女對立的二元沖突模式消失,男性成為女性的引導者,女性如果不想被拋棄就必須站在男性同盟軍的位置,來取得男性社會的認同,作品中的女性自我向革命理性作了妥協。至此,革命終于戰勝了愛情,也標志著丁玲的創作由過去的“性別寫作”轉向了“革命寫作”。
二、革命話語之下,潛意識地保留著“五四”個性化創作立場
丁玲是“五四”最后一個女作家,也是左翼文學的第一個女作家。1924 年,丁玲為了追求進步思想從上海來到北京,結識胡也頗,并與胡同居,又開始寫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等轟動一時的小說。在此期間,丁玲都以“莎菲女士”的姿態面世,沒有表現出她的政治傾向。直到1931 年胡也頗遇難后,丁玲創作才明顯轉向。如《水》反映的就是社會革命斗爭。然而,與同期男作家此類題材的作品相比,丁玲“革命+戀愛”小說對“革命話語”的表現程度與情感態度,顯然都不如男作家。丁玲自稱,“寫《韋護》的時候,她的創作動機與寫《在黑暗中》時一樣,并不意在寫英雄、寫革命。”[11]可以說,此時丁玲的創作已經開始向左轉,但她并沒有完全放棄從‘五四’精神中繼承過來的張揚自我價值的個性主義創作,而且這種精神或隱或顯伴隨了丁玲的一生。
丁玲的創作,從自我走向群體過程中,知識女性的自我意識和批判意識,使她“左聯”時期的轉型之作(《韋護》等),時常不自覺地從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游離出來。按照丁玲創作的主觀意圖,她設想:莎菲式小資產階級女性被革命者引導或批判,有的被改造成革命者,有的最終脫離革命大眾,被革命拋棄,以此來完成對“革命話語”的表達;然而,作者潛意識中的反叛精神與性別意識,在寫作過程中,使她越寫越遠離自己主觀意圖,導致她的作品客觀上承傳著“五四”個性主義的創作精神,依然保留著女性的主體意識。以革命黨人瞿秋白為原型的小說《韋護》中,她在寫作策略上有意做出‘革命戰勝了愛情’的安排。但是,她仍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對男權中心主義的批評立場。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丁玲的向左轉,并不是與過去徹底決裂,而是在有所保留的基礎上向前邁進。在革命話語之下,任然潛意識地保留著“五四”個性化創作立場。
考察丁玲的“革命+戀愛”模式小說發現,它更傾向對兩性愛情觀的探索與揭示,作者對女主人公愛的合理性表示了同情,反而淡化了“革命文學”的革命性。探其原因就是,作者對愛情的崇尚。丁玲曾有這樣的論斷:“我個人是主張寫愛情的。愛情對于人生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都需要愛情,從古到今,愛情一直與生活,與文學不可分開。我們中國有很美的愛情故事,有《紅樓夢》、《西廂記》、《白蛇傳》等。寫愛情的作品,只有寫美好的、高尚的感情,才得以流傳下來。”[2]基于此種創作觀,丁玲在向左轉的代表作中都盡情地抒寫愛情。因而,在小說《韋護》中,韋護贏得麗嘉的愛情并非因為其革命者的身份,而是韋護的人格魅力。但,事實又是怎樣的呢?韋護與麗嘉的分手,表面看來,韋護離去是由于聽從“另一種人生觀念的鐵律”,因為愛情妨礙了他的革命工作;事實上,“麗嘉并沒有一次妨害他工作的動機。”“她不會要求他留在家里的。”因此,“他的沖突并不在麗嘉或工作,只是在他自己。”[12]在于他人性的惰力和弱點。美琳離開子彬也是如此,從作品中我們看不出美琳的離開是出于外在革命的感召,更多出于對愛情的失望。瑪麗離開望微同樣如此,是付出的愛情沒有回報,是強烈的愛情渴望沒有得到應答導致的。因此,“丁玲的這些作品與其說是‘革命+戀愛’的‘革命小說’,不如說是探索女性精神追求與命運出路的‘性別寫作’”。[13]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從30 年代向左轉開始,丁玲逐漸改變了自己的創作立場與傾向,開始由追求個性主義創作轉向人民大眾文學。但丁玲過渡期的轉型不徹底。“這個轉折,對丁玲太重要了,也太艱難了。”[14]《韋護》、《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三篇小說準確地勾勒出丁玲在“轉變”過程中思想的矛盾性。盡管作者主觀上有用“革命話語”努力把握時代,有著表現時代的強烈欲望,但由于作者潛在性別意識與性別立場的不時滲透、流露,使得創作往往呈現出紛繁復雜的矛盾現象。事實上,“此期丁玲的‘轉折’,應該是從‘個性思想’的‘一項單立’到‘革命意識’與‘個性思想’共時的‘二項并立’”[15]。只是這種“并立”在作品中的表現迥異,前者是作者刻意要抒寫的,表現在顯性層面上,而后者是作者創作中潛意識流露出來的。這些都使得丁玲此時期作品呈現出矛盾復雜的思想內容,從中也可以窺見丁玲當時創作心態的復雜性。
[1]秦林芳.“轉折”中的持守左聯時期丁玲創作中的個性思想[J].文學評論,2008,(6) :120.
[2]宋建元.丁玲評傳[M].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144-155.
[3]常彬.虛寫革命,實寫愛情——左聯初期丁玲對“革命加戀愛”模式的不自覺背離[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1) :178.
[4]丁玲.我的創作生活[A].丁玲全集( 第7 卷) [C].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327-328.
[5]宋建元. 丁玲評傳[M].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146-147.
[6]熊鷹.都市、電影和女性[J].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多彩畫卷——丁玲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355.
[7]丁玲. 答〈開卷〉記者問答[A]. 丁玲全集( 第8 卷)[C].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
[8]賀桂梅. 知識分子、革命與自我改造— —丁玲“向左轉”問題的再思考[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2):195.
[9]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A]. 丁玲全集(第9 卷)[C].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8.
[10]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的地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20.
[11]閻浩崗.丁玲:革命年代的個性話語[A].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多彩畫卷——丁玲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240.
[12]丁玲.丁玲自傳[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77.
[13]陳嬌華.潛隱在“革命話語”中的不諧音—論丁玲“革命+戀愛”小說中隱含的矛盾現象[J]. 南華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8,(5) :88.
[14]周良沛. 丁玲傳[M]. 北京: 十 月 文 藝 出版社,1993:253.
[15]秦林芳.“轉折”中的持守左聯時期丁玲創作中的個性思想[J].文學評論,2008,(6)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