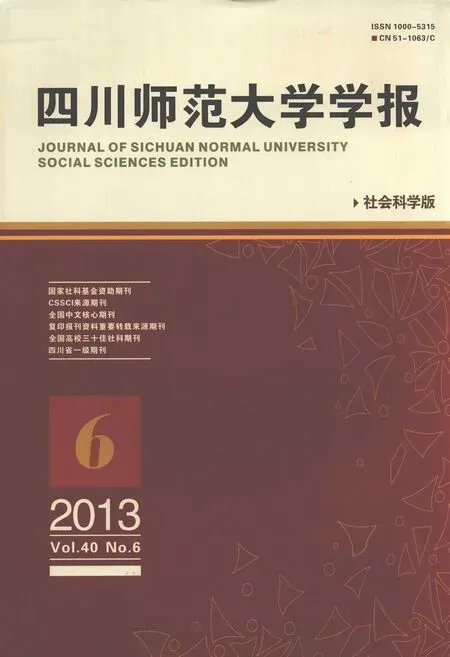“五四”后學生自治與校園學潮
婁 岙 菲
(華東師范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五四”后學生自治與校園學潮
婁 岙 菲
(華東師范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五四”之后,學生自治得到極大鼓吹,各地學校普遍設立學生自治會,但因從基本涵義到實際運作規則、方式等根本性問題,均難以達成一致,在實際運作中反而成為挑起學潮的重要誘因之一。學生自治施行不久便有“失敗”的說法傳出,部分學生因權利的濫用而將校園內矛盾激化,釀成學潮,甚至不乏以激進的方式來解決矛盾的案例出現。學生表達不滿方式的變化,既折射出了“五四”后學生群體在師生關系層面的反傳統傾向,同時也是其整體走向激進化的重要表現。
“五四”后;學生自治;校園學潮
“學生自治”的提法早在清末就已在新式學堂出現,其具體組織形式類似當今的學生社團,與“自治”觀念關聯并不大①。民國成立后到“五四”之前,學生自治問題雖偶有討論,但并未形成規模。各校的學生社團大多以同鄉會、懇親會為主,一般只組織規模較小的學生課余活動,以“觀摩德藝,鍛煉身體”為宗旨,多由校長及教職員主其事[1]80,1920年代之后逐漸隨實驗主義思潮的傳播而風行全國。作為舶來品,學生自治的基本內涵、適用范圍、自治權限等問題,也經過了一系列由外來而至本土的調適過程。“五四”后,各地大中小學競相組織成立學生自治會,并被視為實施訓育的一種有效方式,得到了各方認可。從理論上講,基于自治觀念而設立的學生自治會可以充當校方與學生之間的中介,起到傳遞信息、溝通想法、共謀進步的作用。從教師一方面來看,學生自治之所以在“五四”之后得到極大的鼓吹,最初目的是希望借此起到壓制學潮的作用。但吊詭的是,學生自治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反而成為挑起學潮的重要誘因之一。
在“五四”運動中,學生們的自我意識被激發起來,但初嘗權力滋味的學生們,“為勝利而陶醉”,變得欲望難平[2]125-126。 他們不再安于校園內平靜的讀書生活,而是愿意處處顯示自己與眾不同的影響力。對校園內外的校務政局稍有不滿即付諸行動,罷課、游行、請愿也成為學潮最為常用的方式。以往討論“五四”運動的影響,一般都較為重視學生自我意識覺醒積極一面的討論,而對其走向極端之后帶來的負面影響仍有待深入討論②。鑒于此,本文將在辨析各方學生自治觀念分歧的基礎上,分析“五四”后受到自治觀念鼓動的“新學生”在心態層面產生了哪些影響,這些心態上的變化使得學生對其自身的自我認知及其社會角色的認知又發生了什么影響,與1920年代校園學潮③的頻繁發生又有怎樣的關系。
另外,還需特別說明的是,與其他以當下現實問題為研究對象的教育學科相比,教育史學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已經發生過的事,這既是教育史的“劣勢”(相對而言)——難以“致用”,同時也正是其優勢所在,即可以憑借著后見之明洞悉事物的發展趨勢。因此,教育史學研究能夠為學界做出更大貢獻之處,與其說是立足于“當下”的經驗總結,毋寧說是立足于“歷史”的更有說服力的解釋。也就是說,教育史學要建構的重點是,通過對歷史現象及其變化過程的考察,逐漸建立起當前教育問題從何而來,又呈現了怎樣的變化的連續性分析。這也是本文展開論述的基本前提。
一 “五四”后學生自治的設想與實施的落差
學生自治成為風靡各校的時髦舉動要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期。受到“五四”精神的鼓舞,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大學和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等校,學生的自我意識空前高漲,相繼成立了學生自治會。此時杜威(John Dewey)來華演講也對學生自治觀念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學生自治會開始在各地學校普遍設立。各學校學生自治會組織方式雖各有不同,但大體上多分委員會和議事會兩部分。委員會是執行機構,分門辦事,各委員由班級選舉。每班委員中再推選出一人組織議事會,作為決策機關。此外,也有部分學校還成立了“學生會”。關于學生自治會與學生會的異同,早已有人做過細致的分析,學生自治會是“謀學生之自律、自學、自強”的教育組織,主要于校內活動;而學生會則是一種政治表現,主要從事的是民眾運動[3]。1920年代后期,由于政黨力量逐漸滲入校園以及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劇,學生自治會與學生會之間在實際職能上的區別也漸趨模糊,但在“五四”前后,各校仍以設立學生自治會為主④。
早在學生自治實施之初,學生自治的定義、權限與范圍即是眾人最熱衷討論的話題。從總體上看,師生對學生自治內涵的理解基本可以達成一致,即認為學生自治是自己管理自己,是學生團體共同的責任。所以,學生自治“非自由行動,而為共同治理;非打消規則,乃為共同立法;非可放任,仍須守法;非向學校宣布獨立,乃為練習自治,仍須受學校之輔導者也”[4]。也就是說,學生自治是一種“有限的自由”,并非完全的自由放任,仍需要學校與教職員充任指導者的角色。如果翻閱1920年代初的相關討論,可以發現在學生自治的最初階段,持這種看法者相對較為普遍,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認為自治是有效的自我管理方式和“求學的一種方法”,能夠幫助學生為將來的社會生活做好準備[5]。因此,即便在當時對學生自治的認知還只是停留于書面的討論,而少有切實的經驗,但學生自治倡導者的言論仍是占據各類媒體的主流,學生自治不久便風靡各校,對學生自治的施行有著相當樂觀的預期。
不過,某些師長一輩的人物在學生自治施行之初就表示了擔心。蔣夢麟曾在北京高師自治會成立之日以“學生自治”為題發表了演說。他說,他理想中的學生自治是有助于培養公共意志或公共精神的,同時學生參與其中也需擔負各種相應的責任;他提醒到,學生自治“并不是一種‘時髦’的運動,并不是反對教員的運動,也不是一種機械性的組織。學生自治,是愛國的運動,是‘移風易俗’的運動,是養成活潑潑地一個精神的運動”,若學生沒有這樣的大決心,學生自治便只是“空的”,“是慕虛名的”;他很擔心學生自治團體有可能處理不好與學校中其他團體的關系,并預計將來的問題恐怕都會從這里生出來,因為“活潑有精神的自治會,必歡喜多干事,范圍必漸漸兒擴大。那時因這個范圍問題,就會和教職員的團體生沖突”[6]。
陶行知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系統地討論了學生自治的概念、基本特點、實施中可能遇到的弊端等問題。他認為學生自治是做共和國公民最需要的操練,可以幫助學生練習修身,積累經驗,輔助風紀之進步,但是如果辦理不善,有可能把自治“誤作治人”,相互之間鬧意氣,甚至把學生自治“當作爭權的器具”。但這并非學生自治“本體上的過處”,主要還是因為“辦理不妥當”。所以,他特別強調學校和學生都“須采取一種試驗態度”,“章程不必詳盡,組織不必細密”,最重要的還是要“一面試行,一面改良”[7]。
所謂“試驗”,實際上帶有冒險的性質,即便是有著完美的過程設計,但結果如何往往還是難以預料。隨著學生自治在各地普遍施行,師長們的上述擔心不幸言中。胡適在沒過多久就已經發現,學生界對學生自治的認識存在兩大誤解。其一,以為自治就是不要治,“自治”就是“無治”。其二,誤以為學生自治是由學生來管理學堂;他表示,之所以要提倡學生自治,是因為“有許多地方受外力加入之管理,不如學生管理自己的力量大”,自治并非只注重“自”的方面,更應注重在“治”的方面,“假如自治而不能治,那可就喪失自己的人格了”;他認為學生自治之所以誤入歧途,正是對上述“自治原理”發生誤解[8]。
時任浙江省立第一師范校長的姜琦也觀察到許多人對學生自治存在不少的誤解,以為自治背后是政治起作用,是一種法律上的事業;學生一經自治,便可與學校脫離關系而宣告獨立,也不必再接受校長和教職員的管束,如果實行自治之后還要事事經過校長核準或認可,就會被認為是“欽定憲法”、“官督民辦”的自治,“不合于‘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姜琦認為,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是把教育上學生自治和法律上地方自治混為一談了,所以,他提出學生自治是一種教育事業,“教育者使被教育者在學校里面,練習自己管理自己的道理,鍛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將來在社會上獨立自營協同合作的準備”,作為學校管理的一種,學生自治便不能完全離開教職員的指導[9]。
從個人發展的角度來看,“學生自治”是指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既鍛煉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領悟和實踐“自覺”和“自動”的精神。但越是概括的表述,理解起來也就越難免出現歧義。施行“學生自治”并不只是學生自己的事情,實際上也牽涉到學校管理中權責的重新劃分問題。對校方來說,倡導學生的自治,相應地就要將某些權力下放給學生,學生掌握了權力便開始關注于自身的權益,參與校務的管理和決策⑤。這樣一來,校方與學生究竟該如何將各自的權責做出恰當的限制,又該怎樣進行監督,這些問題恐怕在著手實施學生自治之初都是未曾考慮清楚的。
學生自治之所以能夠得到追捧,與其說是對新式西洋理論的好奇,不如說是著眼于施行的實際作用,特別是對有可能帶來的學校管理及師生關系改變的期待。但是,設想是一回事,施行又是另一回事。第一師范學校的學生徐紹烈就回憶自己學校實施的是“口舌的自治”:“五四”學潮之后校長就宣布了自治草章,組織自治籌備委員會訂正草章,但各級選出的學生代表們只知道引經據典、高談法理,“足足有二星期,還沒有定那幾條會章”。好不容易定好會章,又有人跳出來說“這次選舉是非法的”,于是又起爭執,“一學期的學生自治幾乎全在三寸不爛之舌上用功夫,沒有一些實事做出來”[10]。還有人就回憶自己就讀的浦東中學的學生會,除了每月開幾次評議會之外,并無多少活動,而且評議出來的東西,“大概都是空空洞洞的,把議案向揭示牌上一貼,就可以完事的”,即便是這樣,評議會有時候還會因為不足法定人數而開不成[11]。“五四”后,雖然學生自治成為一個“新流行的極時髦的名詞”,但大多仍對自治會章程、如何組織等問題茫然無知[12]。學生自治會往往流于形式,熱情參與者固然有之,但大部分學生則采取觀望和漠不關心的態度。徐紹烈就將實行自治以后的學生分成了四派,即失望派、服從派、旁觀派、墮落派。所謂“失望派”是指那些本是熱心倡導學生自治的,但在外界“惡勢力”的“逼迫”和“壓抑”下不能施展,只好退回書齋;“服從派”和“旁觀派”對于自治的漠然是相通的,區別在于前者只知隨波逐流,后者則是對任何主張都“大肆其熱諷冷嘲的謾罵”,最終使提議不了了之;所謂“墮落派”則是指那些本來就冥頑不靈的學生,以為“自治”之后便可以不再受規則的束縛,隨心所欲,這一派最愛“鬧飯堂,起風潮”,可說是“學生自治的害敵”[10]。
無論對于學生還是教職員,最初因為對自治實行的前景過于樂觀,再加上對新事物好奇心的驅使,還大致能保持著相對積極的態度,但時間不長,種種弊端就開始顯現。學生自治實施沒有多久,輿論上就已經開始出現有關學生自治失敗的聲音。有人就曾觀察到實行學生自治后,學生與教職員兩方面的“誤會”:學生們以為前受高壓,今去障礙,恍如撥云霧而見青天;一朝當權,唯我獨尊,正可不顧一切,為所欲為,好像猛虎出兕檻一般。辦學的人們,以為學生自治,是應時產物;為洞識時務順應時勢起見,不得不將這份權限,拱手而讓諸學生。從此表現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派,以為訓練權限,全盤讓出,是好是歹,與己無干……;一派以為大權旁落,心實不甘,無已,而陰事窺刺,暗中掣肘,總使學生自治進行上,發生障礙[13]。
作為體現學生自治意識的組織,學生自治會最關心的還是牽涉到學生個人或集體實際利益的層面,或者說是與學生休戚相關的校務問題。因為此前對學生自治認識和討論不足,雖然教育界都較為看重自治的作用,但對于施行方法和步驟上理解的分歧越來越暴露出來。比如胡適更看重的是學生自治對于養成公民的作用,他曾批評學界青年對于“自治的方法”知之甚少,學生需要學習的是如何提議、如何表決、如何修正以及遵守會場秩序、會場規則等,學生自治也需要遵守“共和的原理”,要學會容納少數人的意見,不能以多數壓迫少數[8]。胡適的理想一直是希望建立起一套民治社會下公民行使權利的規則和方法,學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校政,是學生自治體現其團體的一方面,而其目標在于為今后社會養成自治的公民。
在實際運作中,熟記規則和步驟還是稍嫌紙上談兵,針對施行中的問題如何做到有的放矢恐怕更難。有人批評學生自治是“靜而不動”、“散而不群”,在此種條件下,學生自治只是少數人的行為,是散漫而非群體的,所以提出要通過“活動”的“動”字和“合群”的“群”字來改進[14]。學生自治本就是一種群體的行為,這是學生自治得以成立的前提,但自治實施中反而需要強調群體行動和切實執行,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惲代英則提供了另一種解決的方法。他表示可以依靠“小團體引起互治的精神”,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只有在此基礎上再去實行校務公開,才能“使學生多參與真的事物”,不至造成有名無實[15]。惲代英的方法顯然是更偏向學生自治個人的示范作用。還有人認為學生自治只知道“從形式入手”,是導致失敗最大的原因,而“真正的自治,不必先有形式上的組織;應自事實上著手”,先創立出“自動”的事業才是最重要的[16]。
這幾種方法本無所謂高下之分,但觀念上的不同顯示出的卻是對于學生身份的不同認知。學生在群體性的活動中,究竟該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是以發動團體分工努力,還是以個人帶動團體,亦或是只求最后結果無須過分關注何為主次,都是在學生自治實行過程中逐漸凸顯出來的問題。處于學生運動之中的少數負責人和多數參與者,也許并不一定能引起沖突和對立,但潛藏于兩者之間的對學生身份的不同認知,則與“五四”后學潮迭起有著重要的關聯。
此外,也有人將學生自治的淪落原因與政黨派系的暗中利用聯系起來。周予同就觀察到,學生會成立之初,“組織雖然疏略,但大家出于熱誠,還非常純潔”,但是,沒過多久,就有了腐化現象,其中間或也有派系的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政客覺得學生的勢力可以利用,于是暗地組織私黨,而少數學生們為自己將來卒業后地位起見,亦不惜欺騙同學以遂其私”[17]79-80。
對此,舒新城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表示,“五四”之時,學生相率加入政治運動,書本實驗室的研究差不多成為“備位之具”;等到“五四”運動成功,“教育者舊日的威信全失”,青年因無適當的指導,以為“五四”的成功完全是學生的力量,再加上社會上一般人隨聲附和,也以為學生勢力最大,這就造成了“黠者利用之以為政爭之具,怯者則諸事惟學生之意是從”[18]302。舒新城的分析基本是站在教師的角度立論,他所指出的這種不正當的放任,如果轉換在學生的角度來觀察,則與羅家倫所言的“學生萬能的觀念”[19]是一致的。
總體而言,1920年代的學生自治從設想到實施經歷的是一個由樂觀而至失望、由失望而至失序的過程。本意作為公民訓練的學生自治,非但未能借此建立起正常的校園秩序和良好的師生關系,學生自治的嘗試被認定為是“失敗”的。經由學生自治的推行而分得學校部分管理權力的學生,雖然仍有認真執行自治精神的成例,但也有不少學生將自治看作攻擊校政、發泄不滿的工具。1920年代頻繁爆發的校園學潮與學生自治的失敗關系密切。
二 自治失敗與校園學潮
舒新城曾以“歷史眼光”來觀察清末以來學生自治的變化。他表示,清末因模仿德國而提倡軍國民教育,以為訓育只是要求學生做到對教員校長絕對恭順,對校章絕對服從,“學生則完全被視為機械而被動地位”;民國初建時,雖注重人格感化,但實際效力很少;“五四”后,各界又錯誤地理解了杜威“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的學說,以為學校就是實在的社會,學校行政人員就是國家官吏,學生則為國民,于是歐美為學生處理日常飲食起居的學生自治會搬到中國之后,便成了“議會式的學生自治會”,這就造成了“學生對于校中行政,不但參與而已,并有干涉之權”;他還引用曾有辦理學生自治經驗的中學校長的話,表示學生如果未經相當團體生活的訓練,便組織大規模的自治會,結果只能是“根基未植枝葉先茂的學生自治”,這種自治會“不但是缺乏自動的精神,而且是具文的、虛聲的,不幸或將造成與團體生活的反習慣——即少數人操縱,多數人不負責任——也未可知”[18]300-302,304。
這種不理解“根基”只知道套用和照搬的做法,被舒新城批評為“遺棄其精華,保留其形式”[18]300。實際上,這不僅是踐行學生自治中遇到的問題,也頗能反映“五四”后學生界的普遍現象,即雖對理念問題不求甚解,卻不忘追求形式上的一致。近代以來中國的學校制度是在模仿日本及西方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校長、教員與學生成為構成新式學校最主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國傳統的師道觀念里,師長是長輩,學校的大事小情均由“家長”作主,享有的是絕對的權威,作為“后輩”的學生只能被動接受結果。清末新式學堂建立之初,學生自我意識開始萌發,有不少學潮即明確表示反抗的就是所謂校方的專制。“五四”運動以前,學生偶有自動的結合,但大多也只是少部分人的舉動,校內外環境稍有變化,即行消滅。“五四”之后普遍成立的學生會和學生自治會,宣稱自己代表的是全體學生的利益,要與校方分庭抗禮。由此傳統師生之間的社會關系被逐漸打破,嘗試過權力滋味的學生也在尋找其他的方式延續他們的欲望。以學生自治精神為基礎的學生會和學生自治會,不僅在中等以上學校中很快占據了學生團體的領導地位,就連一些初小或高小也都成立了學生自治會,加入自治的隊伍。自治會是先進、時髦的代名詞,凡有學校之處,便視同必需,否則不足以顯示其有謀求發展的追求。但是正如前文所引述,學生自治實施的效果并不樂觀。比如,清華的學生覺得學生自治的聲調在清華已經算是很高調,但唱過了二三年,“把學生秩序反唱到了亂七八糟,難堪救藥的田地”[20]。 “自治”成了“無治”,嫖賭煙酒、洋臘迷窟、私自出校、任意逃課都“乘隙而生”,學生借自治,恣意享受自由,學校也借自治逃避責任,不聞不問[21],即便是清華也難逃自治失敗的命運。
隨著學生會和學生自治會的成立,“學生自治”這幾個字卻已經成為學生干預校務、決定教職員選任的“武器”和“擋箭牌”。如果教師稍加干涉,便會被視為保守落后的“專制魔鬼”,遭到群起反抗,并最終釀成學校風潮[22]。1924年初,《教育雜志》上刊出署名“涵冰”的文章《師道》。作者注意到,“五四”之后,學生們對于學校中任何事情或人員,“一有不滿意的地方,就立刻起來,借助學生自治會的力量,毫不顧忌,趕校長、趕教員,不惜犧牲自己的金錢、精力、時光,甚至對于對方的人格盡情詆毀、攻擊、謾罵,以泄其憤,舉平日教授自己的教師,陶冶自己的校長、職員,視若路人之不如。這種現象,非常普遍;凡近幾年來國內的學校風潮,幾無一不有這種情形”[23]。《教育雜志》自1923年第一號開始,陸續登載常道直總結的各地各級學校風潮表,同時又在第四號上刊載了他的分析文章《民國十一年度學校風潮之具體的研究》。常道直詳細分析了前一年報章所載的106起學校風潮的分類、原因、經過情形、處理結果以及亟待解決的問題,以此希望能“于消弭風起云涌之學潮上有所裨補”[24]。對當年的學潮印象深刻的還有嚴既澄。在他的眼中,1922年的教育界已變得很是不平靜,稍一翻閱報章雜志便見學潮二字,“觸目累累,真有書不勝書之慨”,他把鬧學潮的起因分為兩種:一是經費問題,多因經費積欠由教職員發動;二是校長或教員問題,多由學生發動,“對于不良的校長和教員,一覺悟其不純稱職,便群起而攻之,忍一時的痛苦,謀久遠的福利”[25]。
呂芳上先生依據1919年到1928年間可檢索到的248次學潮及學生運動,按照發生的主因將其歸納為:(1)反對新舊校長(占39.91%);(2)學生不滿學校設施(占14.91%);(3)反對政府及教育當局(占12.09%);(4)經費及收費問題(占 8.06%);(5)反對教職員(6.85%);(6)反對列強(占6.85%);(7)學生沖突(占 4.83%);(8)檢查仇貨事件(占 2.41%);(9)教職員沖突(占 2.01%);(10)不明(占2.01%)[26]23。從中不難發現,只有第(3)(6)(8)種是與社會及政治等校園外因素直接關聯,因校園內部因素釀成學潮的比例接近70%。相對于帶有政治意圖的學生運動及學潮(如“五四”運動、“五卅”運動等),雖然校園內學潮的社會影響力要小得多,但校園內學潮無疑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對于學生們來說,國家安危、政局走向、軍事形勢當然是關心的焦點,但那些宏大的國家主題顯然并不構成他們日常生活的全部。圍繞著學校這個中心才是他們生活、學習的施展空間,因此這一空間中人物、事件以及相互之間的沖突更易引起他們的共鳴,遇到與他們所求不一致時也更易釀成學潮。對于學生自治來說,前文諸多引述,特別是對學生自治失敗的觀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學生自治在施行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表現出從有序變為無序甚至失序的狀態。原本是為建立秩序而實行的學生自治,因部分學生的放縱改變了性質和方向,學生自治反倒成了釀成學潮的催化劑。
據統計,在歷次學潮中,“罷課”是學生最常用的武器,其次為游行和請愿⑥。有人曾總結學生抗議中慣常采用的手法:一般來說,“先由學生方面,驟起暴動,封鎖門戶,斷絕交通,毆辱校長(或教職員);繼以罷課、打電報、發宣言、請愿官廳、求援外界;后由校長呈報官廳,藉助軍警之力開除學生,或解散學校”[27]。上述列舉各項,無論以何時何地的標準來判斷,恐怕都屬于相當激進的舉動。以罷課、退學的形式表達不滿,可追溯到清末新式學堂,但仍以“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最大。雖然“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但是民眾因愛國而做出的罷課、罷工、罷市等抗議行為不可能被軍閥政府所允許,因此沖突不斷,于是愛國運動漸漸地變成反抗政府的運動。而“五四”后,學生與校方或教職員的關系,也常被用來與“五四”運動抗議示威中民眾與軍閥政府的關系進行類比。面對學生提出的更換校長、教職員,廢止考試等等各種要求,學校當局也常常以學風校規等等來進行壓制,這又會引發學生對于校方的不滿和對校規的蔑視,激起學生的反抗心理,甚至連同舊制度、舊禮教等等都要反抗起來。但與“五四”運動所具有的愛國性質不同,各校風潮與愛國的主題較少發生關系,由此學校風潮本身的合法性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任鴻雋、陳衡哲即曾公開撰文表示:“哄校長,趕教員,許多學校的風潮,是與愛國絕對無干的”,對于學生來說,“研究學問去培植自己的實力,才是真正的愛國行為”[28]。
然而,就“五四”教育界的現實來看,需要回答教育界風潮的合法性問題的不應該只有學生。因為教育經費的短缺,政府發不出教職員薪水而有教職員要求發薪的“薪潮”、不肯教課上班的“教潮”,由教職員而引發的學校風潮也在此時頻繁上演[26]188。校長、教職員一般選擇的抗爭方法以公開提出辭職、罷教最為普遍,此外,也有像北京國立八校因索薪而釀成的“六三慘案”這種相對極端的沖突[29]41-43[30]。隨著軍閥統治日益嚴苛,教職員的“教潮”、“薪潮”和學生的“學潮”之間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使得教育界的風潮始終難以歸于平靜。郭秉文在回顧1922年高等教育問題時曾談到學校內部“不靜之現象”,他表示之前的學潮“以救國相號召”,但現在的情況則是“對一人、因一事,有觸而即發”,其中又以“社會心理之影響為最大”,學校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青年受到“無秩序、無紀律”社會的刺激與暗示,“胥以暴力為歸”,并非一紙整頓學風的訓令所能補救[31]。
楊天宏教授以“學生亞文化”來指稱“五四”后學生表現出來的激進且帶有強烈精英意識的校園文化,同時他還將校園文化另一重要載體教師也納入到討論范圍之中,這一觀察十分值得重視[32]。中國傳統的師道觀中,教師常被要求成為道德上和行為上的模范,起到身體力行的示范作用,但教職員被迫付諸于罷教、抗議的行為,則給同在校園中的學生帶來了相對負面的影響。有的教員為了自身生計,只得在各校兼課,疲于應付繁重的教學任務,也就談不能處處做到對學生的悉心教導。對此,邵力子就曾批評所謂教育家,“遇著學生鬧風潮,便總說學生不好”,這和資本家遇著工人罷工就說工人不好有著“同樣的心理”,他希望教育家都能反躬自責,與學生相見以誠,盡管責備學生,但先須責備自己[33]789。上海工專侯紹裘也曾站在學生的角度指責學校當局也有“許多令人齒冷的地方”,他曾經質問教職員說:“鬧風潮的學生所宣布的幾大罪狀,未必全是虛構的。就使退一步講,這些是學生誣蔑的,但是我要問你們到底在教育什么,竟令全體的學生一齊起來誣蔑你們?或者你們要說:那是少數壞學生鼓勵的,其中不乏明白的人,只是被脅迫罷了。但是我又要問,你們的教育怎樣會使多數好學生被少數壞學生脅迫而不敢主張正義呢?”[34]
學生指責教職員不夠認真負責,教職員則視學生為“不祥之物”[35]。“五四”后,教育界的生存環境雖有漸趨惡化的意思,但師生關系驟然轉變至如此惡劣,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學生在此時的普遍心態已經發生不小變化。浙江六師的學生陳宗芳所言則頗能代表當時學生們的想法。他說:“我個人底觀察,學校的阻礙進步,學生便有鬧風潮的必要。這種風潮越鬧,學校愈會進步,大家齊來,有可鬧處、使我們不滿意處,我們正不妨鬧個天翻地覆,從黑暗中鬧出光明來,不怕斥革,何怕政界干涉,在校里做一個鬧風潮的分子,就是于社會上留一粒革命種子,將來學校的進步,社會的改造,不靠我們,還靠那一個呢!”[36]在學生們的思維邏輯中,作為未來社會中的一份子,學校能否進步是與社會今后改造能否成功聯系在一起的。學生們既然已經經歷過“五四”運動,參與并影響到了國家大事的決策,那么,一所小小學校內部的行政管理、教師任命,實在是一舉手一投足就可以解決的小事情。學校事務如有辦理不善之處,學生有責任也有義務挺身而出。就學理上分析,能夠發現學校內的各種問題,并且能積極主動找到解決方法,這本是自治精神之所在,但學生究竟應該用何種方式表達他們對于校務的意見,也同樣可以詮釋自治精神。從實際情況來看,面對校務問題,學生們最初尚能保持一定的協商方式,但隨著事態陷于僵持,他們往往更易于選擇罷課、請愿等相對激烈的斗爭方式。常道直曾從學生的角度總結了學校風潮的經過:大概凡一風潮之起,多先由學生提出某種要求——積極的或消極的;進行要求時,有時并發布宣言,表明其要求之正當,若要求不遂,則每出于罷課;罷課期中,每用種種宣傳方法,宣布校長或其他教職員之“罪狀”,或者逕向行政官廳請愿,甚至有向督軍、巡閱使請愿者;有時一校學生間往往因鄉誼觀念、個人私誼或個人利害關系而分成兩派,互相攻訐,釀成分裂現象。至于毀壞器物、侵犯人身于風潮經過中亦間或見之;又通常學生于拒絕新校長或舊校長去職后,每自提出繼任校長之資格,或逕自行校長之“假選舉”,此亦為一年來反對或拒絕校長風潮中之一常見事例[24]。
從教育行政管理角度分析,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放開學校事務的管理權限,更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學校風氣,只不過學生對校務的參與需要劃定適當的范圍,而不是完全取代校長和教職員的絕對自治。但“五四”后,學生顯然不滿足于只是列席參與校務那么簡單,而是多少有想掌控學校發展的意味。
在蔣夢麟的印象中,因為“不滿的情緒已經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長得根深蒂固”,所以在學校里的學生也受到這種情緒的感染,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學生所求稍有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他們只知道“向學校予取予求,但卻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五四”后就“為成功之酒陶醉了”的學生們“沉醉于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2]131-132。蔣夢麟之所以對學生有如此負面的評價,與他親歷的北大“講義費風潮”有著很大關系。1922年10月中,北大部分學生因不滿講義收費而發生圍攻校長辦公室,并由此引發了從校長蔡元培到總務長蔣夢麟及其他行政負責人沈士遠、李大釗、李辛白等隨同辭職,全體職員也宣布暫停辦公,校務陷于停頓。這次風潮由小事件而釀成大風潮,不僅成為此后蔡元培辭離北大的誘因,也顯示了學生逐漸走向與校方或教職員對立一面的象征事件[37]。
三 走向歧路的學生自治
1920年1月出版的第一期《學生雜志》,以署名“種因”的文章《學生底新紀元》作為開篇,顯然是希望以此預示一個嶄新的開始。作者肯定了學生在“五四”運動中所顯示出的巨大能量,但也不無擔心地表示,學生們“好名過于崇實,仿佛在社會上居一種特殊的階級,幾于無事不能,無事不問,于是學生底弱點暴露,社會的同情亦冷淡。這是學生底大失敗”;作者認為,學生的生活本應該是“最純潔最高尚的生活”,此后的學生應當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能夠改造自己的,才能改造社會國家。能夠自覺的,才能夠覺人覺世”,并視此為“學生思想改變的大關鍵”,是“學生的新紀元,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新紀元”[38]。以“學生的新紀元”來概括即將到來的1920年代學生們的種種變化,可以說有著相當敏銳的前瞻性眼光,同時也帶有迎接新時代的普遍樂觀。
1920年代是極速變化的時代。對于學生而言,他們改變自身的愿望的確更為迫切。隨著各校風潮的爆發,一向以文弱書生形象示人的學生,希望逐漸擺脫掉被壓制被束縛的弱者地位,進而掌握在校園內外的主動權,并開始為謀求自身的權利而斗爭。但由于其并未改變學生這一社會身份的整體屬性,而只是在個體一方的心態和自我的身份認同上做出了調整,這就使得學生仍無法從本質上改變其弱者的地位。正是因為這種弱勢的地位,處于各類風潮之中的學生為了保證抗爭取得勝利,更易以弱者的身份取得社會各方力量的支持,因此普遍地采取相對激進化甚至是武力的斗爭方式。
著名作家老舍在創作于1926年的小說《趙子曰》中,全方位描繪了大學生的生活。他寫到:“在新社會里有兩大勢力:軍閥與學生。軍閥是除了不打外國人,見著誰也值三皮帶。學生是除了不打軍閥,見著誰也值一手杖。于是這兩大勢力并進齊驅,叫老百姓見識一些‘新武化主義’。”[39]251老舍的小說創作帶有強烈的寫實主義色彩,老舍將“學生”與“軍閥”并舉,并不只是出于文學創作上的需要,而是可以看作當時社會現實的一種記錄。易家鉞就曾以《中國的丘九問題》為題,記錄了他對湖南、安徽兩地學生界的觀察。所謂“丘九”是社會上給予學生的綽號,有比“丘八”(即“兵”)還要厲害的意思。學生與軍閥兩種本來敵對的力量,卻被發現有著共通之處,這不得不說是學生界的悲哀。周作人就曾表示:“有一個時候,學生是天之驕子,無論做什么事都是對的,旁人沒有批評的自由。到了近來,湘皖地方發現了‘丘九’的徽號,于是名譽有點壞起來了,但是只要和校長教員為難,人家總還是不敢說他們不對的。”[40]552
其實,早在“五四”運動后不久,就已經有人對“五四”隱含著的武化問題做過討論⑦。梁漱溟針對“五四”后學生被捕事件,并沒有如同眾人那般要求釋放學生,反而提出要將學生付諸于法庭辦理,而鼓勵參與其事的學生主動自首。在他看來,“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即便“曹、章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成立時,他們仍有自由”,縱然學生是愛國的行為,但也不能不管不顧地橫行,侵犯加暴行于他人;梁漱溟所憂慮之處在于,學生有可能借著國民意思四個大字不接受法律的制裁,踐踏在法律之上所帶來的損失將會更大[41]。梁漱溟此言一出,立刻引來眾多反對之聲。他們從法律、國家、外交等多方面對學生打人的行為做出無罪的辯護⑧。在“五四”后群情激奮的輿論環境之中,梁漱溟對于學生動武的質疑雖然有著理性主義色彩,卻是不合時宜的。
兩年后,還是學生的孫伏園在《晨報》“五四”紀念專刊上撰文轉述老輩議論,“五月四日是打人的日子,有什么可以紀念呢?”他也承認出手打人是“下策”,但是又說“倘損傷了少數人,能使大多數人得到利益”,這些“小小缺點”也就算不得什么。不過,他還是因“打人”二字,聯想到中國的國民性問題:“為什么中國人不留心光明正大的宣傳運動,卻崇拜這出奇制勝的打人運動?”他覺得,“五四”以前雖不能說是十分美滿的宣傳,但總算有幾種出版品,“很有點像文化運動”,國人卻未有直覺,“直到青年不得已拔出拳頭來了,遂大家頂禮膜拜,說這是文化運動,其實這已是武化運動了”[42]。與此相對,張維周則更加正面地肯定了“武化”的作用。他認為“五四”運動之所以可貴,“正在學生肯起來打人這一點上”。“五四”是學生干政運動的開始,特別是像在中國這樣政治亂且社會沉悶的情況下,這種熱烈的干政運動是萬不可少的。學生認真拔出拳頭,實行與外力及民賊宣戰,不再像“五四”之前只是在理論上進行鼓吹,對于實際的政治問題卻未見影響。所以,他表示“五四運動的真價值,就在不用‘筆頭’,而用‘拳頭’;不是‘文化’,而是‘武化’”[43]。
“尚武”是近代教育中頗為重要的思潮之一。清末學部厘定的教育宗旨即將“尚武”納入,民初蔡元培在此基礎上又提出將“軍國民教育”作為新教育方針,雖然有人評論說軍國民教育實際推行狀況并不能令人滿意,“以全國皆兵”和強健身體的目的“在事實上”均未曾達到[44]97-98,但有些時候不能僅以是否達成實際效用作為衡量標準,有不少作用于觀念層面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五四”后學生“武化”趨向正可看作這種潛在的影響。學生處在學潮之中,思維、行動往往更易走向極端,特別是各方沖突僵持不下的時候,動用武力反而成為最直接又最有效率的解決辦法。1925年發生的女師大風潮,之所以在延宕半年多時間后形勢突然明朗,主要還是因為武力的介入;一直以來,楊蔭榆、章士釗被詬病的正是他們動用警力驅逐學生、解散學校,但實際上,學生自治會也在這一過程中主動而非被動地運用了武力予以對抗,甚至其激烈程度遠超楊、章之上[45]。
1920年代初,美國教育哲學家孟祿曾受邀到中國訪問,他在演講中曾有一絕妙的比喻頗為傳神,他說:“以前的中國,如坐在椅上,絕無顛蹶之虞;現在的中國則如乘在自由車上,偶一不慎,危險立至。蓋椅是靜的,隨便可保持其均衡,自由車是動的,非有發動的精神,必不足以保持其均衡。故現在教育上之問題,即在如何造就此等活潑的人才,以駕馭現在之動的前進的中國,而保持其均衡也。”[46]辦教育更需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但時代在變,人亦在動,如何在此過程中尋找到新的平衡也并非易事。曾積極參與“五四”運動的羅家倫后來發表感言,表示“五四”運動“實在成功太速,徒然把學生的地位抬得很高,而各界希望于學生的也愈大”,但卻是“虛名過于實際,實在是最危險的事”,“因為社會把學生的地位抬得愈高,所以對于學生的責難也由此愈甚;因為對于學生的希望愈大,所以弄到后來失望也就愈多”[19]。不幸的是,“五四”之后,社會輿論對于學生界的看法確實也經歷了這個由“希望”到“失望”的過程。
與其他社會階層相比,“學生階級”的優勢自“五四”運動起逐漸顯示出來,除了對新知識的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學生”是一個處于隨時變動中的社會階層,他們求知是為未來生活做準備,一旦完成了一定要求的知識和技能的學習,他們便會以“畢業”的方式結束他們的校園經歷,學生身份便也宣告結束,而另一種社會角色則宣告開始。郁達夫就曾注意到學生這種特殊的身份,他表示:“學生為自身學業計,為將來出路計,不得不結合得特別的牢,不得不反抗得分外的烈”,所以,他對學生賦予厚望,認為“上抗強權,下領民眾”是學生階級的任務[47]53-54。不過,過于強調學生的特殊身份也有可能造成學生的自以為是。瞿世英(菊農)即對此提出過警告。他表示,因為有了“五四”運動聯合各界的經驗,學生便以為“各界人士”是可以號召的;同時,又因為成功太易,便以為凡事成功都很容易,于是,“大家都趾高氣揚,以為我學生本‘萬能之上帝’,何事不可為,何事不能為,養成了嬌惰的氣習,凡事孤行,安得不失敗”;而若等到失敗之后再去求得各界的援助,各界本來就難以與學生共同進退,再加上失了社會的同情心,自然不能不失敗,這樣久而久之,學生信用便也逐漸喪失,能力也會減弱[48]。
面對1920年代教潮、政潮迭起的現實,學生們所選擇的抗爭方式,因為與社會認知中學生基本形象相沖突,一直是被詬病的。在以學生為主角的學潮中,帶有反傳統意味的對學校、教師權威的挑戰,學生往往有著更大的主動性,成為主動發難的一方。從社會認知的層面來看,“學生”與“律師”或是“醫生”一樣也被看作“職業”之一種,但其社會身份的獲得是連帶而又自然發生的,專業程度顯然遠遠低于律師、醫生。“學生”身份的獲得雖然也需要經由一定的篩選(如入學的資格考試),但從他們踏入校門算起,即便是尚未接受任何訓練亦被稱作“學生”。“五四”后學生之所以被認為能夠擔負喚起民眾的職責,主要是因為他們被視為新知識的代表,所以與傳統的“士”或讀書人一樣,掌握新知識即代表著一種資格,也預示著需要承擔某些社會責任。但問題也正在于此,從學力的程度上來看,傳統的讀書人或者“士”至少是通過了一定級別的科考,“學生”身份實際上標識的則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而非結果。獲得“學生”這個社會身份并不自動等于學生就已經有了指導民眾的能力和水平。真正掌握知識,完成學業的表征正是其“學生”身份結束之時。也就是說,從總體上看,雖然學生想以學生身份作為各階層的領袖,但實際上他們承擔起這一責任的能力尚有不足。這種能力的不足可以體現在多個層面上,其作用于學生自治便有可能引起對自治觀念理解上的偏差,進一步加劇了學潮的激進化,并為此后學生群體的“黨化”埋下了伏筆。
注釋:
①比如,1904年,福州十三所學堂,除個別書院及普通小學堂外,其余各學堂學生建起青年自治會,每月聚會一次,“講求民族主義,自治精神”。無錫競志女學也曾設立自治會,分演說練習、運動練習、唱歌練習三部。此外,也有因校中學生“頗有敗壞名譽之事”以至“殊難管束”,進而提出設立自治會,“以保名譽”。參見:《紀學生自治會》,《鷺江報》1904年第83冊;《自治設會》,《女子世界》1905年第2卷第2期;《倡立學生自治會》,《直隸教育雜志》1907年第11期;《倡設學生自治會》,《教育雜志》1905年第3期等。
②討論“五四”后學生群體變化的論著甚多,如: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羅志田《課業與救國:從老師輩的即時觀察認識“五四”的豐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馬建標《學生與國家:“五四”學生的集體認同及政治轉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楊天宏《學生亞文化與北洋時期學運》(《歷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③1920年代是學潮及學生運動發生較為頻繁的時期,本文所謂的“校園學潮”主要從學潮發生原因進行區分,專指校園之內因教育原因而引發的學潮,并不涉及因政治原因引發的學潮。
④“五四”運動中各校出于聯絡的需要,還相繼成立了學生聯合會。具體的組織情況是,各校學生會分為兩部分,一為代表會,一為干事會,由各班級學生投票選舉代表及干事若干人組成。制度近似議會和政府,一司建議,一司執行。再由各校代表會干事會互選或推定出席總代表及總干事若干人,組織學生聯合會。參見: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中學生社編《史話與史眼》,上海開明書店1935年版,第79頁。
⑤上海大夏大學學生會長期以來都派代表列席校務會議,比如在建校周年紀念會、學校食堂的膳食等問題上,校方也愿意聽取學生會的意見,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學生自治是在重建一種新的師生關系。參見:《學生會與校務議會聯席會議紀事》,《大夏周刊》1926年第28期。
⑥據呂芳上先生對1919年到1928年間有記錄的學潮及學運的統計,教職員及學生方面在學潮中主要采用的手段為教職員罷教(5次),學生罷課(92次),演講游行、請愿(46次),停退散學(12次),暴力(23次),傷亡(9次),校方則有28次采取了召軍警入校的方式。參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第24-25頁。
⑦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五四”、“新文化”與此前的文學革命之間的異質性,之所以有“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樣的提法,是用政治與文化互為因果的邏輯將兩者勾連起來的,而歷史邏輯的轉換卻未必如此。“五四”之后,各方輿論就曾對“五四”究竟是“文化運動”還是“武化運動”有過爭執。參見: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3期。
⑧參見:知非《評梁漱溟君之學生事件論》、《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的問題》,陸才甫《學生無罪》,均見《每周評論》1919年5月18日第2、3版。
[1]陳寶泉.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報告[M]//蔡振生,劉立德.陳寶泉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蔣夢麟.西潮·新潮[M].長沙:岳麓書社,2000.
[3]可可.十年前學生生活之回顧[J].學生雜志,1928,(12):1-13.
[4]張莆沺.學生自治之研究[J].玉田季刊,1924,(4):40-63.
[5]梁治華.“學生自治”之討論[J].清華周刊,1920,(185):14-19.
[6]蔣夢麟.學生自治——在北京高等師范演說[J].新教育,1919,(2):118-121.
[7]陶行知.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J].新教育,1919,(2):193-201.
[8]胡適.對于學生界今后的希望[J].學生雜志,1921,(10):6-10.
[9]姜琦.學生自治的性質及其促進的條件[J].新教育,1920,(2):195-204.
[10]徐紹烈.學生對于學生自治應有的覺悟[J].學生雜志,1922,(10):59-64.
[11]宓汝卓.上海浦東中學學生生活概況[J].學生雜志,1922,(7):50-52.
[12]黃炎培.“學生自治號”發行的旨趣[J].教育與職業,1919,(16):1-2.
[13]曹念美.從十年來學生活動里所見的學校罪過[J].學生雜志,1923,(1):1-8.
[14]仙女生.改進學生自治的商榷[J].學生雜志,1925,(1):18-19.
[15]惲代英.關于學生修養學生自治及中等學校改英文為選修科目[J].申報·教育與人生,1923,(10):7.
[16]捷庵.學生自治的真意義[J].學生雜志,1927,(7):51-53.
[17]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M]//中學生社.史話與史眼.上海:開明書店,1935.
[18]舒新城.一個改革中學學生自治的具體方案[M]//呂達,劉立德.舒新城教育論著選: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9]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J].新教育,1920,(5):600-614.
[20]行知.自治與被治[J].清華周刊,1921,(223):4-8.
[21]李迪俊.敬告自治后的清華學生[J].清華周刊,1921,(223):8-10.
[22]朱仲琴.中國教育實際問題數則[J].新教育,1920,(1):113-116.
[23]涵冰.師道[J].教育雜志,1924,(4):3-5.
[24]常道直.民國十一年度學校風潮之具體的研究[J].教育雜志,1923,(4):1-20.
[25]既澄.學潮[J].教育雜志,1922,(1):3-4.
[26]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27]楊中明.民國十一年之學潮[J].新教育,1923,(2):295-312.
[28]任鴻雋,陳衡哲.一個改良大學教育的建議[J].現代評論,1925,(39):10-13.
[29]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M].長沙:岳麓書社,1998.
[30]向仁富.論1921年北京國立八高校教師索薪運動[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97-104.
[31]郭秉文.民國十一年的高等教育[J].新教育,1923,(2):259-261.
[32]楊天宏.學生亞文化與北洋時期學運[J].歷史研究,2011,(4):88-105.
[33]邵力子.學潮雜感(一)[M]//傅學文.邵力子文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34]侯紹裘.學潮平議[N].民國日報,1922-12-7(覺悟):7.
[35]研因.整頓學風[J].教育雜志,1923,(3):教育評壇1-2.
[36]陳宗芳.學校與風潮[N].民國日報,1921-12-06(覺悟).
[37]婁岙菲.蔡元培1923年辭職原因新探[J].教育學報,2008,(6).
[38]種因.學生底新紀元[J].學生雜志,1920,(1):1-4.
[39]老舍.趙子曰[M]//老舍.老舍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40]周作人.學校的綱常[M]//陳子善,張鐵榮.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
[41]梁漱溟.論學生事件[N].每周評論,1919-05-18(1).
[42]伏廬.“五四”紀念日的些許感想[N].晨報,1921-05-04(6).
[43]張維周.我主張學生要干預政治[N].晨報,1922-05-04(4).
[44]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45]婁岙菲.允文允武:1920年代學生群體意識的形成與變化——以女師大風潮為例[R].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1.
[46]孟祿.學生運動之意義[J].學生雜志,1921,(11):6-10.
[47]郁達夫.學生運動在中國[M]//吳秀明.郁達夫全集:第八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48]瞿世英.學生運動之失敗及將來應取之方針[J].學生雜志,1922,(6):5-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Autonomy and Student Strikes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LOU Ao-fe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students’councils were founded in most universities because of the advocating of students’autonomy.However,because of the inconformity of the function and ways of 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students’autonomy actually soon led to student strikes. The abuse of power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ion.The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dissatisfaction even through violence,which reflected the anti-tradition tenden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was the important trend of the radicalization.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students’autonomy;student strikes
G455
A
1000-5315(2013)06-0114-11
[責任編輯:羅銀科]
2013-05-02
婁岙菲(1980—),女,北京市人,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講師,研究方向為大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