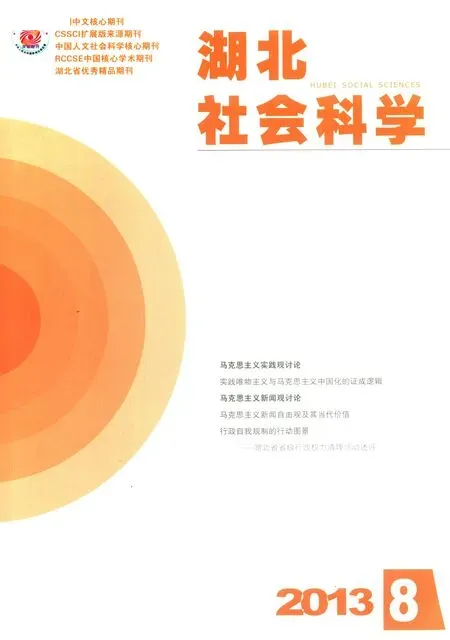論《美狄亞》的殺子復仇——女性的反抗與尷尬
龍 琳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美狄亞》于公元前431年于雅典上演,大概是三月或是四月的狄奧尼索斯節,而一兩個月后,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即將爆發。戰火前夕的歐里庇德斯只是在劇本的第三合唱歌里借歌隊之口頌揚了雅典的美好與熱愛和平,除此之外,整個劇本沒有其他的地方展示了愛國主義情結,因為歐里庇德斯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了他一直關注的婦女生活的主題上——女性的社會地位,女性反抗時的舉步維艱,以及女性的心理狀態和對男性社會的影響。
整個劇本分為五場,曾經幫助伊阿宋奪取金羊毛的美狄亞,在和伊阿宋生了兩個兒子之后面臨著被拋棄的境遇,伊阿宋將要和科林托斯國王科瑞翁的女兒成親,不僅如此,因為美狄亞有著令人不安的魔法,所以她還將被驅逐出境。美狄亞本是科爾喀斯國的公主,當初為了幫助伊阿宋奪取金羊毛,背棄家國,殺死弟弟,科瑞翁的驅逐將會令她徹底的無家可歸。走投無路的美狄亞經歷了痛哭悲嘆的絕望、輾轉反側的內心糾纏之后,選擇了令人震撼的復仇方式——設計害死了國王和即將新婚的公主,并且,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兒子。
美狄亞的殺子復仇歷來引起諸多學者的爭議,正因為對夫權的反抗和倫理上的缺失同時并存其行為當中,人們對她形成了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一種認為針對伊阿宋的背信棄義,美狄亞的報復如同劇中歌隊所說“是很有理由的”[1](p301),其行為蘊含了女性對于父權社會的反抗。對立的觀點則認為美狄亞因為愛欲受挫而瘋狂殺子,體現了人性的陰暗與殘忍,違背了社會的基本倫理道德,是古希臘文化中放縱原欲的必然結果。筆者認為,片面強調任何一個視角都無法完整的闡釋出美狄亞的形象,而美狄亞在復仇行動中的正反性質也并非完全對立,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邏輯。美狄亞的悲劇不僅僅是女性地位的悲劇,也是女性覺醒和反抗的悲劇,更是男女共同面對的文明沖突的悲劇。
一
社會在對待女性地位時的不公態度顯然是作品要展示的悲劇根源之一,被拋棄的美狄亞在第一場首次出現時有一段大段的獨白,令人驚訝的是,詩人并沒有讓她如尋常棄婦那樣先去指責伊阿宋的負心棄義:“在一切有理智,有靈性的生物當中,我們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們得用重金爭購一個丈夫,他反而會變成我們的主人;但是,如果不去購買丈夫那又是更可悲的事。而最重要的后果還要看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好丈夫,還是一個壞家伙。因為離婚對于我們女人是不名譽的事。”[1](p300)“一個男人同家里的人住的煩惱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積,可是我們女人就只能靠著一個人。他們男人反而說我們安處在家中,全然沒有生命危險,他們卻要擎著長矛上陣:這說法真是荒謬。我寧愿提著盾牌打三次仗,也不愿生一次孩子。”[1](p301)
借美狄亞這個外鄉女子的視角來批判雅典城邦對于婦女的態度應該更能觸動前5世紀舞臺下的觀眾,政治家狄摩西尼在作品中這樣描述當時希臘人的女性觀:“我們供養侍伴是為了尋歡作樂;豢養女奴是為了照顧我們的日常起居;而妻室則會給我們帶來合法的孩子;并且成為我們可以信賴的看家婆。”[2](p216)這段話中,我們不僅看到妻子的作用僅僅在于生育和看家,還能看到古希臘的男性按照自己的生理和社會需求對女性進行了不同的功能劃分,成為侍伴,女奴或者妻室。女性自我的生存意義被完全擱置,她的價值全然依托于符合男權利益的氣質、角色和定位。古希臘的女子沒有公民權,沒有受教育權,甚至沒有財產權,從出生到死亡,始終處于受監護的狀態,她不是由男性親戚監護就是由丈夫監護,并且只有通過他,她才能享受到任何一種法律保障。再沒有比以下這句話更能說明古希臘女性的失語的處境了,伯利克里在陣亡將士公葬典禮上說:“一個婦女最大的光榮就是不被男人所議論,不管恭維也好,批評也好。”[2](p217)
劇本中的美狄亞并非一開始就對男性的霸權保持警惕,從開場中保姆的話里我們得知“她倒也很受愛戴,事事都順從她的丈夫——妻子不同丈夫爭吵,家庭最是相安。”[1](p294)這意味著經歷變故之前的家庭也曾平和快樂,不過這安樂家庭的基礎是美狄亞徹底的柔順屈從。伊阿宋的變心給予了美狄亞展開新思想的契機:即便她認可男性的主體地位,做到了一個社會規定的一切——作為妻子逆來順受的賢惠,作為母親悉心教養了兩個孩子——她依舊被毫不猶豫的拋棄。伊阿宋的這種行為模式,是整個社會承認男性主體性的邏輯中的順理成章的結果,女性只有被安排被言說和被決定的命運。美狄亞來自黑海沿岸科爾喀斯國,較之于希臘,這里荒蠻偏遠,文明滯后,相對于更加成熟的父權社會,這里的女性擁有較為寬松的社會空間,文明落差使得美狄亞比當地的希臘女子擁有更明確的主體精神;而且,美狄亞不僅身為公主,還是偉大的夜神、魔法神和地獄女神赫卡忒的神廟祭司,擁有智慧的名聲。身份地位和智慧才能使她比一般的女子更具有先天的自覺意識和叛逆精神,所以這個有決斷的女子在劇中一開始質疑的不是伊阿宋喜新厭舊的個人品質,而是伊阿宋身上呈現的新的文明——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文明的奠定。
二
歐里庇德斯在劇中用了一些象征性的場面來暗示美狄亞覺醒前后的狀態,戲劇開場時的美狄亞“躺在地下,不進飲食,全身都浸在悲哀里;自從她知道了她丈夫委屈了她,她便一直在流淚,憔悴下來,她的眼睛不肯向上望,她的臉也不肯離開地面。[1](p294)而劇末退場時,美狄亞乘著龍車自空中出現,居高臨下的對伊阿宋進行了痛斥,隨后從空中退出。從躺在地下到站在空中,美狄亞意識的變化,心態的變化和主體地位的轉換顯然是作者想要刻意突出的。
在男性霸權的社會形態中,文化為了保持其內部張力,也賦予了像美狄亞這種遭遇冤屈的女性以行動或是反抗的權利,不過這反抗必須按照文化規定的行為模式——往往是自我毀滅或求助于更高一層的男性,如杜十娘,秦香蓮,這樣的行為模式才能保證不對男性中心的社會形態產生威脅。男性既可以為秦香蓮們一掬同情之淚,又可以在包拯的鍘刀中體驗到正義的驕傲與快感。在這種規定性的權力下,女性的反抗行為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成為了對男性的應和和屈從。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所說:“權力關系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印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3](p27)“只有在它被某種征服體制所控制時,它才可能成為一種勞動力,只有在肉體既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時,它才能變成一種有力的力量。”[3](p27)女性在被控制模式下的反抗行為反而構成了對男性權力的承認力量。
所以美狄亞行為的最大意義不在于復仇本身,而在于她最大程度的跳脫出了這一規定的行為模式,這個異域文明的代表對業已成型的男權社會展開了她的令人膽戰心寒的復仇方式:殺死國王和公主,最后還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兒子。
讓美狄亞親手殺死兩個兒子的情節是歐里庇德斯的創造,傳說中美狄亞殺死國王公主后,憤怒的民眾殺死了她的孩子。在科林斯近郊的神廟附近,曾有對美狄亞孩子們的祭祀:把七個童男和七個童女獻給女神以贖取居民之罪。另一說法是,美狄亞想使孩子們得到永生時,出于誤會殺死了他們。歐里庇德斯的創造使得美狄亞的主體性形象更為自覺。整個劇本中美狄亞的復仇過程只是表象,作者更加想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個女性的主體意識如何從蟄伏到蘇醒,如何突破了文化的規定性從而擁有了自身選擇權力的過程。
福柯認為,任何“主體”都是在話語中通過話語實踐建構的。并沒有一個自給自足,作為意義派生源頭的“主體”存在,而“話語”通過不同的方式構建個人,使個人成為可以具現話語的“主體”。美狄亞自我主體的建構,則是通過她用自己的話語方式選擇了壓制母性,拋棄女性被規定的社會角色,反抗男性對其的壓迫建立的。殺子行為在道德和倫理上雖然令人難以接受,但是擁有自己的選擇權,呈現自身主體性的角度上,誰都不得不承認,她是一位自由的斗士。
三
在希臘人的觀念里,真正的生育者被認為是父親,母親則被認為是父親種子的培育者和保護者。以父子人倫為軸心的家庭倫理中,保證父子血緣關系的延續和傳承是父權社會的核心,所以傳宗接代被上升為家庭倫理的最高道德層次。這也是為什么劇本要在第三場安排雅典國王埃勾斯出場的原因,埃勾斯因為得罪了阿芙洛狄忒,使他和他的姐妹都不能生育,在求神諭的路上遇上了美狄亞,美狄亞答應幫助他獲得后裔,以此換得復仇后的安身之地。他的出現不但給美狄亞提供了避難地,還進一步的強調了子嗣對于男性生存價值的重要性。而對此種觀念的接受,也構成了美狄亞復仇話語的一個重要前提。
福柯認為,各種“話語”不僅是思考,產生意義的方式,更是構成無意識與意識的心智活動、以及情感生活的要素,所有的話語都指涉了社會和歷史背景,是特定存在情境的產物。用他自己的話說,與話語有關的“不是思想心智或產生它的主體,而是它被部署的實際領域。”[4](p82)這意味著,話語主體在實施任何動作時,起作用的不僅為自由意志,還有背后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力量。正因為男性權力的無所不在,不僅僅限制在經濟和政治活動這類公共領域之中,而是進入了一切家庭和私人關系內部,才使得美狄亞在反抗男權的同時,也接受了男權社會父子相承,無后為大的觀念,把兒子看成了父親的財產,認為剝奪伊阿宋的子嗣讓他生不如死,這才是對其的最大報復。這意味著,她正是在接受了男權社會中父子核心的倫理觀的前提下實施了她的殺子行為。
父系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使得女性面臨這樣的困境:即便覺醒后的反抗行為,依舊籠罩在父權文化的陰影之中。美狄亞的行為雖然實施了報復后果,但這后果的承受者也同樣包括她自己。殺子之前的痛苦猶豫輾轉反側,最好不過的說明了這點。歐里庇得斯在第五場不吝筆墨的用大段自白展現了此時美狄亞綿延不絕的苦痛:“孩子們呀,孩子們!……在我還沒有享受到你們的孝敬之前,在我還沒有看見你們享受幸福,還沒有為你們預備婚前的沐浴,為你們迎接新娘,布置婚床,為你們高舉火炬之前,我就將被驅逐出去,流落他鄉……希望你們養老,親手裝殮我的尸首,這都是我們凡人所羨慕的事情;但如今,這種甜蜜的念頭完全打消了,因為我失去了你們,就要去過那艱難痛苦的生活;你們也就要去過另一種生活,不能再拿這可愛的眼睛來望你們的母親了。唉,唉!我的孩子,你們為什么拿這樣的眼睛望著我?為什么向著我最后一笑?哎呀!我怎么辦呢?……”[1](p324)這份在母愛和仇恨當中糾結輾轉的心情是如此的令人動容,它的感染力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讀者對美狄亞的殘忍行為的反感,報仇者自身的痛苦是如此的深重以至于她不僅是發起復仇行動的主體,也成了承受復仇后果的客體。
生兒育女的生理功能讓女性的天性中就擁有對孩子的疼愛,母親的身份雖然是男權社會賦予女性的社會角色,但經過十月懷胎后對后代的的疼惜憐愛也是女性的自然情感。而當男權社會完全忽視女性本體,片面性的強調母親對于男性社會的輔佐效果時,被激怒的反抗女性在拋卻社會角色的同時,也對自身的情感進行了扼殺與傷害。出走之后的娜拉何去何從,覺醒后的女性如何建立自身的話語來達到文明內部性別權力的和諧,女性如何能擺脫男權社會無孔不入的文化侵染,建立自身的話語體系,這個持久而艱難的任務是女性面臨的最大難題,否則,女性終將陷入如美狄亞般的尷尬處境。
文明的進步總是在內部諸多要素的碰撞和裂變中得以孕育,悲劇正為我們展示了這種文明內部的裂隙與對抗,美狄亞的殺子悲劇,不僅展現了女性于社會所處附屬地位的不公境遇,而且進一步揭示了女性在反抗時的步步維艱,尋求自身話語時的無所依托。而通過這悲劇,我們還看到,伊阿宋雖處文明社會中的強勢地位,但同樣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在劇終痛不欲生,稱自己“簡直完了”,痛苦絲毫不遜于美狄亞。[1](p332)這更讓我們意識到,文明中任何因素的失衡,后果的承擔者將是處于這文明中的任何一個個體,這場男性和女性的戰爭中,沒有勝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兩性關系是最能說明人類在何種程度上擺脫了自然界,而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所以,在文明進步的長河中,對于兩性文明失衡的質疑與探討一直是一個縈繞人心經久不息的話題,而這正是《美狄亞》這部偉大歷史悲劇的永久魅力。
[1]羅念生.古希臘悲劇經典[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H.D.F.基托.希臘人[M].上海: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3]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4]宋素風.多重主體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研究[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