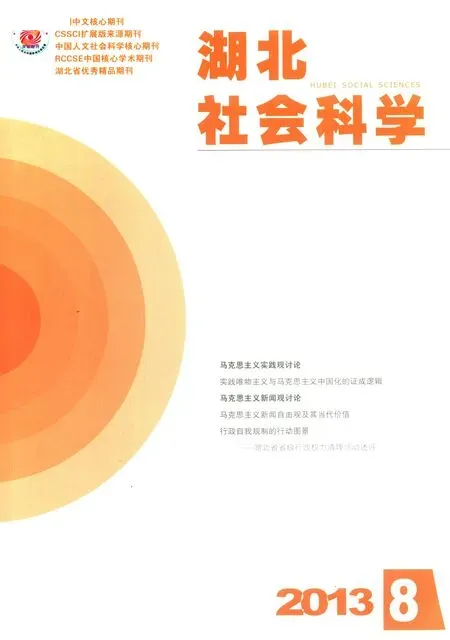思想品德結構的生存論視域
張耀燦,王智慧
(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思想品德結構的生存論視域
張耀燦,王智慧
(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
人的思想品德由思想、品德、政治觀、法律觀四要素構成,這四者都包含價值和意義雙重結構。思想品德價值結構的根據是人的主客二分式存在結構,這一價值結構可分為階級統治性價值結構和公共交往性價值結構,是人之思維的結果。思想品德的意義結構扎根于人的天人合一式的存在方式,思想品德之美和思想品德之信是兩種存在于思想品德中的意義形態,構成思想品德的意義結構,是想象的產物。
思想品德;價值結構;意義結構
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思想品德結構是動態存在。學界對于思想品德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對思想品德心理結構的探索,研究視角是心理學;這種結構是簡單結構,還需要探討其辨證的復雜結構。對思想品德結構的探索,每一論者都欲構建一個包羅萬象、完整的結構,或許正是由于這種學術抱負過于宏大,研究都失之膚淺。本文不擬構建思想品德的完整結構,而立足于人的主客二分與天人合一兩種存在結構來求索思想品德的價值結構與意義結構,以期實現新的突破。
一、價值與意義的基本關系
價值與意義是一對含混不清的概念,經常替代、混合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混用尚可理解,但學術語言的混用則后果嚴重,有待深入闡發。二者都是哲學概念,需要站在現代哲學的立場上才能索解。
(一)價值。
價值問題是人類有史以來的老問題,但價值論或價值學直到19世紀末才開始在西方系統地發展起來。價值論源于西方,是作為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反叛出現的,是為了給近代以來的理性主義糾偏。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價值的主觀性與客觀性以及價值與事實的關系,這兩個問題可以看作價值論的基本問題。在第一個問題上,價值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的,是價值主客體的統一;第二個問題是休謨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互相關聯且層層遞進的問題,即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關系問題與價值學何以可能的問題。研究結論是,事實與價值是一個統一的過程,這個統一的基礎即實踐。
中國價值論的研究肇始于真理標準大討論,這一研究從開始便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上展開的。伴隨改革開放30年歷程,價值論研究創造性地挖掘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價值論思想,形成了基本理論主張。這種主張從主客體統一的角度界定價值關系,認為它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以主體為尺度的一種客觀的主客體關系,是客體的存在、屬性及其變化是否同主體尺度和需要相一致、相符合的關系。價值既不是單純的主體,也非單純的客體,而是主客體的特定關系,這種關系以主體的生產實踐為基礎,暗含了真理與價值的統一。這種統一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真理內在地具有價值內容,因為人類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從來就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且不可分割。恩格斯說:“人只需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去估價這些關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的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不應當到虛幻的彼岸,到時間空間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處或與世界對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應當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1](p651)也就是說真理存在于人的實踐之中,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武器,而認識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改造是為人的,故真理必定有價值。第二,追求價值必須以追求真理為基礎。價值必以事實為基礎,不存在超越事實世界的價值,價值不過是實踐中關于客體的屬性與主體需要的一致關系。人類在追求價值過程中必須以真理為基礎,符合客觀規律是人類實踐活動獲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但建立在主客體關系基礎上的價值論也面臨著挑戰。批評者認為主客關系模式基本上屬于認識論模式,這種模式不過是研究認識問題的主客體關系模式的推廣,容易陷入哲學史上“效用主義”的窠臼。于是開始探索價值哲學的本體論(存在論)基礎,認為價值是人類特有的絕對超越性指向,是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的歷史生成,意味著人對自然的超越,標志著價值存在物的誕生和意義世界的確立。這就深入到生活領域,進入意義領域。
(二)意義。
如果說價值這個概念尚好把握,意義則更是一個歧義叢生的范疇,哲學家們已經從語言學、邏輯學、符號學、釋義學、精神分析學等層面來談論意義,這些都為從生存的角度理解意義奠定了基礎。英語中的“意義”一詞有兩種表達方式,一個是meaning,一個是significance。前者指出意義具有主體性,意義是相對于人而言的;后者與sign密切相關,存在于一物與他物的關系中,一物的意義在于對他物的指向性。英國語言家奧格登和理查茲在《意義的意義》一書中列舉了16種定義,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揭示意義的不同內涵。現代哲學的生存論轉向為理解意義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正如美籍猶太教哲學家赫舍爾所說:“人的存在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存在;他總是牽涉到意義。意義的角度是人所固有的,正如空間的角度對于恒星和石頭來說是固有的一樣。正像人占有空間位置一樣,他在可以被稱為意義的向度中也占據位置。人甚至在尚未認識到意義之前,就同意義有牽連。他可能創造意義,也可能破壞意義,但他不能脫離意義而生存。人的存在要么獲得意義,要么背叛意義。對意義的關注,即全部創造活動的目的,不是自我輸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2](p46-47)“對有意義的存在的關切是做人所固有的——它是強大的、基本的、發人深思的事,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心”。[2](p48)意義是對生存的提升,引導人進入澄明之境。正如對于“存在”難以下定義一樣,對于“意義”也很難下定義,只能描述其基本特征。其一,意義所指稱的并非是實在對象,而是某種精神境界,即意境,它具有無限性指向。意義不是實體,它抓不住;不是有限,它不可定義。它是人之生存的無限延伸,是與世界的合一,是天地之境界,無形、無象。這正是人的精神家園和安身立命之處所。人超越有限進入無限境界和永恒境界,這就是意義的旨趣。其二,意義是對終極的追問,是對人的終極關懷。“人最終關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其意義……它超越了人的一切內外條件,限定著人存在的條件……它超越了一切初級的必然和偶然,決定著人終極的命運。”[3](p697-698)對于人的關懷有初級的、高級的,有生理的、物質的,也有心理的,但意義層面的則是終極的。其三,意義所具有的無限可能性超出了邏輯界限,是直觀的對象,帶有審美的韻味。這種關于意義的智慧領悟,是存在論的一部分,康德在談到理性直觀時就曾斷言:“為了把對理性存在的概念置于直觀之下,除了將它人化之外別無他法。”[4](p11)胡塞爾則把這種針對客體主義的超驗哲學稱為人文科學,這種人文科學所指的正是意義。它不可定義,只可描述;它不是邏輯的對象,而是直觀的對象。通達意義不能靠說明,而只能靠理解,靠海德格爾所說的詩言。
(三)價值和意義的關系。
價值和意義的關系,學者已做積極的探索。張曙光認為:“在現有的哲學論著中,人生意義問題被歸結為人生價值問題,講的是個人對他人的、對社會的貢獻和他人與社會對個人的回報與尊重。但是嚴格講來,人的意義與價值并不等同。價值固然是屬人的,但人的生命及其人格畢竟是無價的。且人生意義雖然發生于人對其價值創造活動體驗,卻并不等于價值本身。價值總是為他的社會客觀概念,意義則是自為的社會主觀概念,它更屬于社會的個人,因為歸根到底意義是人的生命在其活動中的自我確證感和自我實現感。人在生活中從追求價值到尋求意義的變化,正反映了人在更高程度上的自我生成和自我覺解。”[5]價值與意義從共同之處來說,二者都是對事實世界的超越,價值世界對事實世界的超越和引領,是事實世界的導向,意義世界也是對事實世界的超越。二者都源于人的超越本性,這種超越本性正是對現實的引導、規范和糾正。價值建立在實然的基礎上追求應然,意義立足于當下追求永恒。二者的區分也十分明顯。其一,價值是個主客范疇,而意義是此在與存在的關系。盡管二者均奠基于實踐,但實踐又有不同的含義。南斯拉夫實踐派代表人物馬爾科維奇指出:“必須把實踐(praxis)同關于實踐(practice)純認識論范疇區別開來。‘實踐’(practice)僅指主體變革客體的任何活動,這種活動是可以異化的。而‘實踐’(praxis)則是一個規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種人類特有的理想活動,這種活動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價值過程,同時又是其它一切活動形式的批判標準。”[6](p23)這里,他區分了總體性的生存實踐和認識范疇的實踐,二者有重大區別。生存實踐是一種總體性的實踐,在這種實踐中,“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7](p486)通過這種實踐“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8](p85)生存實踐中的人,被海德格爾稱為“此在”,而非“主體”。作為認識檢驗標準的實踐則要單純得多,毛澤東的公式,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就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實踐。人是主體,認識對象則是客體,價值就是主體與客體間的效用關系,價值哲學與認識論相伴隨。兩種實踐反映的是人的兩種存在結構,生存實踐指向天人合一式的存在結構,價值實踐指向主客二分存在結構,二者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其二,價值是有限的,意義是無限的。盡管二者都是對現實的超越,但價值是在主客體視域中,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都實體化了,只能指向有限的存在物,即特殊的存在者。說某物價值再大,它一定也是有限的,不是無限大。而意義則不然,意義是此在與存在的關系,它使人皈依于存在這個大全,化作永恒,匯入無盡的歷史長河和高遠的天地之中。其三,意義為價值奠基。作為人之精神生活中的兩個組成部分,可以打個比方,價值是為精神生活蓋造高樓,意義則是為這座高樓清理地基。康德說過,人類理性非常愛好建設,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況如何。他認為,只要人明智起來,不管什么時候都不算太晚的,不過,考查地基如果做得太晚,工作起來總會更困難一些。人類的價值大廈如果沒有扎實的意義地基,將會整體塌倒。這也就是近代價值哲學意圖糾正理性主義偏頗而又不可能徹底的原因。尼采呼吁重估一切價值,而海德格爾則反對糾纏于價值,直接提出意義的問題。
二、思想品德的價值結構
人的思想品德由思想、品德、政治觀、法律觀四要素構成,這四者都包含價值和意義雙重結構。思想品德的價值結構根基于人的主客二分的存在結構,這一價值結構又可分為階級統治性價值結構和公共交往性價值結構,前者根基于生產的邏輯,后者則根基于交往的邏輯。
(一)階級統治性價值結構——不平等。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資本流通公式是:GW-G′。資本的價值增值就是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剩余價值的結果,資本只能在生產中增值,但離不開流通過程。生產過程才是資本剝削的秘密所在,而流通領域只發生等價交換,是價值的實現過程。在資本家完成了勞動力商品的買賣后,把工人領進工廠,“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9](p176)這就是人之思想品德的階級統治性價值結構的根源——階級統治性社會關系。在此理論基礎上,享譽世界的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洛維系統地提出生產政治理論。他認為:“生產領域也有自己的上層建筑,剛開始我把它稱作‘內部國家’,后來我稱之為‘生產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機構’,或者更寬泛地稱之為‘生產政體’。勞動過程的意識形態效果的確存在,但也存在著規訓勞動過程和形塑了一種生產的政治的獨特機構。”[10](p289-290)他在這里分析的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可以用來分析整個階級社會。統治階級的統治根基就在生產領域,在生產領域完成剩余價值的生產,統治階級利用各種方式維護其生產秩序的穩定,這種社會的價值秩序也內化為階級社會每個人的思想品德之中,在思想、品德、政治觀上體現出來。
1.階級統治性價值觀在思想上的體現。思想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階級統治性價值觀主要體現在價值觀上。奴隸主階級不但占有奴隸生產的剩余勞動,而且占有一部分必要勞動,還占有奴隸的人身——這個價值之源泉。奴隸社會是最殘酷的剝削制度,一切價值全在統治階級手中。地主階級則放棄了對佃農人身的占有,但對價值的剝削也異常殘酷,不但占有全部剩余價值,還占有部分必要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在封建土地制度下,佃農的人身自由只可能是半自由的。資產階級則文明得多,他們只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必要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則作為工資發給工人,這樣工人就有了正常的人身自由和生活必需品。工人出賣勞動力而取得工資成為工人階級基本的價值觀念,資本家也維護這種價值觀念。這種觀念的哲學表現即西方近代的主體性哲學,這里的主體是資本家,客體是工人和大自然。這種哲學的社會根基即生產實踐,主體對客體的關系是認識與被認識、改造與被改造、征服與被征服、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19世紀末期的價值哲學對這種主客征服關系進行了糾偏,但不徹底。只要剝削制度不打破,這種主客對立的階級統治性價值觀念就會永遠存在。
2.階級統治性價值觀在品德上的表現。生產實踐所決定的階級統治性價值觀念也反映在人的品德上,誠如恩格斯所說:“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11](p434)“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11](p435)道德的階級性體現在家庭道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多個方面,而職業道德是透視其階級性的好窗口。我們知道,原始社會末期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人類的職業活動就伴隨社會分工而形成,隨分工就形成紛繁復雜、多種多樣的職業,同時也產生了多種多樣的職業道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腦力勞動者就是剝削者、統治者。這些剝削者內部逐漸產生一部分游離于勞動之外的不勞而獲者,在資本主義社會甚至以剪息票為生。而大量的勞動者則被束縛于各種職業道德之中,受固定職業束縛,勞動則成為恥辱和痛苦。真正打破勞動的職業束縛則要到未來的共產主義,那時“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12](p85)職業品德的固化就是階級統治的體現。
3.階級統治性價值觀在政治觀上的體現。人的政治觀可分為公共政治觀和階級政治觀,階級統治性價值結構主要體現在階級政治觀上。原始社會未期,尖銳的社會沖突和政治斗爭,使“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13](p170)可見,政治統治是政治斗爭的必然產物,國家一產生便開始了對全社會的政治統治。政治統治的實質是階級統治,它是經濟上最強大的占優勢地位的階級為了維護和強化既定的政治關系與社會秩序,通過國家權力而對被統治階級的支配和控制,是人類政治生活中最高層次的政治行為。由于政治統治需要合法性基礎,剝削階級為了掩蓋赤裸裸的政治統治,他們往往創造出各種理論來粉飾,這種理論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政治觀上都有反映,這就是階級統治性價值觀念。這種政治統治主要根基于生產領域,奴隸社會表現為奴隸主對其家奴勞動的統治;地主階級通過地租的形式強制農民勞動;資本家的工廠就是其統治的王國,他們不但是企業管理者,更是階級統治者。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從表面上看,這種監督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對立而引起的管理職能,實際上這種監督就是統治,是在管理掩蓋下的統治。一旦工人出現消極怠工、破壞機器等行為,資本家便會采取開除、辭退等措施,工人被迫重新回到勞動力市場,選擇另外的剝削者。而勞動者的反抗一旦越出單個企業的范圍,資產階級的國家就會出面鎮壓,對付工人的是步兵、騎兵、炮兵。
(二)公共交往性價值結構——平等。
生產領域是價值創造和價值增值的領域,而交換領域則是價值實現的領域。《資本論》第一卷專門論述剩余價值的生產,而第二卷則主要論述資本的流通和剩余價值的實現,足見交換的重要性。從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是一個“驚險的跳躍”,這一跳躍如果不能順利完成,摔毀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資本家。從生產領域進入交換領域,這一轉換在哲學上的表現是從主體性哲學向主體間性的轉換,從生產實踐向交往實踐的轉換,甚至哈貝馬斯把這一轉換視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和現代性的繼續。他認為現代性作為“一項未完成的構想”需要從主體性的意識哲學范式向交往實踐的主體間性哲學范式實現轉換。“現代性批判”未能擺脫主體哲學的困境,需要重建現代性規范,這一重建的基礎即交往理性,用交往范式來取代生產范式,從目的行為轉向交往行為。這一轉向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交往全球化的反思,也是對傳統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重生產輕交換的理論糾偏。但這一轉換并非對生產領域主客關系的否定,而是對交換領域主體間關系的重視。商品交換領域是個平等領域,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不光是一般的商品交換要求平等,就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換也要求貫徹平等原則。這樣,生產領域的不平等就轉換為交換領域的平等。這一平等觀念在人的思想品德上有具體體現。
1.公共交往價值觀在思想上的體現。價值的創造在生產領域,但價值的實現則在交換領域,而交換的基本原則即等價交換,這就是價值規律。價值規律不允許不等價的占有,各種商品和勞務要在市場上通過彼此間的換位比較實現勞動的價值。一旦兩種商品的交換最終完成,就表明它們之間具有相等的價值,體現為相等的勞動耗費。商品交換的平等觀念也擴展到其他交往領域,于是平等成為人類彌足珍貴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階級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它簡明樸素,穩定持久,在現代社會成為基本的人權要求。這種平等觀念本來源自于交換過程的平等,但在人類公共生活領域又延伸為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此乃平等觀念的深化。平等是商品交換催生的,不過古代社會商品經濟不甚發達,平等觀念被等級觀念所壓倒。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空前發達,平等才被系統論證,得到空前發展并且深入人心。但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的平等不可能實現,平等恰恰是實現不平等的形式。社會主義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階級差別,平等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平等的實現提供了經濟基礎,必將為人類平等價值觀的發揚和創新提供新的現實和展望新的遠景。
2.公共交往性價值觀在品德上的體現。自從有了公共交往就有社會公德的要求,但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社會公共生活的空間和時間都比較小,社會公德問題并不明顯。近代工業文明是社會公德領域日趨擴大的社會基礎,這個基礎即商品交換和公共交往的擴大。中國近現代諸多人士對現代化的歷史追求就充滿對社會公德的關注。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指出:“我國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認為社會公德水平是決定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尺度之一;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實踐中要求學生“養成公德,培養公德感”;陳獨秀認為,封建倫常使社會道德隨落,國力衰微,中國之危因所以迫于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這墮落。平等的公德觀念的確立是現代公民的一個基本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擴大了人們的公共交往,公德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現代公德的基點是公共交往領域,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否定了過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虛假公共性。每個成員都有利用和享受公共財產和公共空間的權利,同時大家都遵守同樣的道德準則,丹尼爾把它稱為“公共場合中行動的平等”。[14](p324)平等的原則意味著公共領域中個體的道德自由與道德約束的統一。
3.公共交往性價值觀在法律觀的體現。平等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其秩序、正義、自由價值都圍繞平等而來。在漫長的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原始初民沒有平等觀念,也沒有不平等觀念,因為“他的欲望決不會超過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在宇宙中他們所認識的唯一需要就是食物、異性和休息;他所畏懼的唯一災難就是疼痛和饑餓”[15](p85)“不平等在自然狀態中幾乎是人們感覺不到的,它的影響也幾乎是等于零的。”[15](p109)隨著剩余產品的出現,商品交換產生,同時產生了平等與不平等的觀念。商品交換的過程產生了平等觀念,商品交換的結果又造成了不平等,產生了不平等觀念。法律起源于商品交換,法律的平等價值也產生于商品交換的價值規律。源于民商法律中的平等觀念,在商品經濟不甚發達的古代社會萌芽,也正由于古代商品經濟不發達,平等觀念也不發達,平等在古代社會主要是一種理想,不平等觀念才是現實。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空前發達,民商法律也空前發達,平等觀念成為時代的主導價值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為時代的口號。但這種平等也伴隨著不平等,伴隨著國家的專制與任性,于是平等觀念便躍進出民商法律領域,步入國家機器系統,把國家政治系統所固有的不平等觀念限縮到最低程度,這就是近代的憲法與行政法。其基本精神就是用平等的法律來限制國家權力,使其盡量與公民趨于平等。伴隨資本主義生產領域、消費領域、交往領域產生諸多不平等,法律的平等觀便進一步走進這個領域,盡量確保實質平等。這就是現代經濟社會法觀念產生的根基。
三、思想品德的意義結構
意義是人生所依憑的那樣一些存在狀態,凡能造成此種狀態的東西者可視為意義之源。“仔細檢視人的整個生活領域就可發現:愛、友誼、游戲、審美(藝術)、道德(修養)、信仰(理想)”,等等,就是這樣一些專門形態。它們的基本功能,主要不在求生存,而在為人生提供意義。”[16]成窮教授這里論述的是人追求意義有多種方式和途徑,他稱之為“意義形態”。結合人之思想品德來看,審美和信仰是兩種存在于人之思想品德之中的意義形態,美和信構成人之思想品德的意義結構,這與小原國芳論述的美育與圣育也是一致的。
(一)思想的意義結構。
思想的意義結構主要體現于世界觀和人生觀之中。世界觀與人生觀實乃一體,正是在生存實踐中才有世界的敞開,世界由此而分為人之生存世界、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人與世界是一體的,人的世界化與世界的人化二者重合,自然是人無機的身體,人是世界的靈明和展示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是人之生存體驗,而非對象化的審視。從生存論上看,世界觀與人生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審美與信仰均發生在生存論視域。
“按主客關系式看待人與世界的關系,則無審美意識可言,審美意識不屬于主客關系,而是屬于人與世界的融合,或者說天人合一。”[17](p121)從主客關系式來看,二者是彼此外在的實體,主體的本質是思維,它要通過認識而穿透對象,實現主客體的統一。而審美意識不管所謂的認識,它要借助于想象來實現人與世界的交融與合一,是觸景生情、情溢于景、情景合一,這種合一是對主客關系式的功利性、價值性的超越。主客關系式是一種功利性關系,關心客體的存在,主體欲占有客體,攫取客體,實現價值。而審美意識是超越利害的昭昭察察,《老子》里“昏昏的愚人”就是這種超越主客關系的天人合一境界之人。陶淵明的“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中的“醒”的狀態即是錙銖必較的主客關系狀態,而“醉”的境界則是超越現實存在物的審美境界。審美活動是人的生命的需要,審美追求的是人的生命意義,審美體驗是人與景的天人合一,審美享受是人對生命之美的愉悅感受。在審美中,人體驗生命的激蕩,獲得精神的滿足。
如果說審美是人生與世界的當下合一,那么信仰則是人對未來這種合一狀態的期待和憧憬,它也深深地扎根于人之生存超越本性中。從根本上說,信仰是一個生存論的精神事件,信仰的根源是人需要以某種意義彌補自我存在的殘缺。人生是有限的,而死是人生最終極的殘缺,如此殘酷的人生值得一過嗎?信仰所要解決的是將來的世界與人的合一,人可以死,但世界不能死,人要活在永恒的世界之中。信仰使殘缺的人生得以彌補,從而支撐人生活下去,實現人生的圓滿。盡管信仰是不可實證的,帶有不確定性,但卻是人之生存的最高精神根據。
(二)品德的意義結構。
如果說品德的價值結構拘泥于現實的功利追求,表現為僵硬的價值規則,那么品德的意義結構則是為這種規則提供最高的精神指引,使品德有了精神根基。有根的倫理生活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倫理生活主體有充實感或意義感,二是倫理生活主體的行為是發乎自然的。所謂充實感就在于人體驗到有限生活的無限、世俗生活的永恒,這種精神充實的品德成為美德和圣德。
品德之所以能夠成為美德,就是因為它的審美向度,也正是美的自由精神一步步把品德規則提升到自由之境。個體掌握道德的過程,包括從無律到他律、自律再到自由四個階段。無律階段標志個體尚未與生活世界發生有效的聯系,他還不是一個道德主體;他律階段的個體已經由于外在的權威而意識到規則的存在,但此時的規則尚是僵硬的;自律階段則標志個體已經很好地理解規則的社會意義,已接近道德的本質,因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18](p15)自由階段則是人對道德的自由把握,表現出品德的從容自如、超然淡定,這是一種審美境界。自由階段是人把“原無明確目的和目標的超主客關系的審美境界,按主客關系的思維方式,轉換成一種明確的目的和目標而加以追求,也就是把審美意識中之‘所是’轉換成道德意識中‘應該’”。[17](p251)這種審美意識貌似脫離實際,而從深層來看則決定著品德的水平、層次和境界。
人生信仰是一種普遍的信仰形態,道德信仰的形成要以人生信仰為基礎,人生信仰的形成和確立與道德信仰的產生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過程。道德信仰是在人生信仰的統攝下,在自律的基礎上對某種道德理想的篤信和奉行,是對道德現實的超越,以人格的超越來證明和顯示人性的神圣、尊嚴和純潔。而“達到如此境界,非心中掌握了或是上帝或是佛的那種真理的人不可”。[19](p184)有了品德信仰的牽引和規約,品德有了神圣性,此乃對品德深度的求索。“近代人的問題與其說是廣度,不如說是深度的問題。”[19](p185)正是深度出了問題,道德才陷入危機,這種危機的實質是品德信仰的危機。在此危機之下,品德異化為規則和教條,人表現為急功近利的俗人,只追求平庸和實惠。
(三)政治觀的意義結構。
政治觀不但有階級統治性價值結構,也有意義結構。缺失意義的政治將變成霍布斯所描寫的利維坦,它具有半神半獸的品質,在保護人的同時,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類把利維坦關進籠子的賦義行為,從此政治有了意義之維,人的政治觀也有了意義結構。霍布斯在《利維坦》的開端即指出:“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創造和治理世界的藝術,也像在許多其他事物上,被人的藝術多模仿,從而能夠制造出人造的動物。”“號稱‘國民的整體’或‘國家’的這個龐然大物‘利維坦’是用藝術造成的”。[20](p1)政治觀的意義之維,主要表現在人的審美和信仰上。
政治美學的實質就是把一部分人的利益打扮、升華為所有人的普遍利益,或者說賦予某些人的利益以“普遍的形式”。這種政治能夠喚起人們通過在場的政治想象到不在場的政治,使隱蔽的政治得以敞亮,在場的與不在場的政治不相同然而相通。這種政治鮮明地體現在中國古代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圖景中,從修身到平天下,從一己之私到天下大公,恰恰是一個政治藝術。偉大的政治家往往是有詩人氣質的,毛澤東就是一鮮明的例證。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詩意描繪,也正是為了最終創造自由人聯合體的目標,使政治真正向著美學生成。社會主義政治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更應該體現審美精神,當代中國人政治觀的審美維度理應擴展和張揚。
政治信仰從屬于人的意義維度,而超越階級統治性價值觀結構。政治價值觀存在于主客二分的存在結構之中,而政治信仰則只有從生存論上才能把握。從這個角度來說,政治信仰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精神內核,是人們對理想的政治形態的堅定和執著的追求。沒有政治信仰,人們就會滿足于現狀,喪失對現實政治的批判維度。政治信仰是對現實政治的超越,是對未來理想政治的開放性生成,正是人們的政治信仰在引領著現實的政治,為現實政治糾偏、解蔽。政治信仰還是現實政治合法性的證明,政治危機往往是人們政治信仰的危機,它使政府失去政治合法性。故政治信仰是政治存在和運行的精神支柱,沒有了政治信仰也就沒有了具體的政治信念、政治信心、政治信任。
(四)法律觀的意義結構。
近代以來,伴隨工具理性和法律社會化、現代化過程,法律從附魅到脫魅,進入一個世俗化、理性化的時代。現代人生存的困境直接動搖了現代法律存在的根基,這種現代性危機,直接導致了法律的總體性危機。這種法律的危機實乃法律的意義危機,而非法律規則的危機。質言之,現代法律喪失了應有的人文之維,對于公民來說,法律成了法律規則的匯集,而非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們法律觀應有的意義結構消失了。
“人類最早產生的法多是以詩歌的形式保存和流傳的……以詩歌的形式表現的法,被稱為詩體法。”[21](p14)其中“德拉古之酷律,如秋霜烈日,其法規自優美之詩句而成;梭倫之法,如春風駘蕩,稱為寬仁之法。梭倫者,詩圣也……梭倫之法典,來自詩篇而成也。”[22](p99-100)中國古代也認為“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這說明美是早期法律的應然維度。現代美學觀照下的法律是體現人之生存之美的法律,這種法律是一門藝術——用法律進行社會管理的藝術。人生活于法律之中,法律成為人之生活方式,人不但理性地參與法律,而且移情于法,體現法律的人文關懷。耶林一再強調法律情感的重要,認為法情感是整棵大樹的根,對權利侵害,不單是金錢的利益,滿足被侵害的法感情也是問題所在,近代法學的尺度完全是呆板的、乏味的物質主義尺度,即金錢利益本身。伯爾曼則更直接,“剝奪了法律的情感的生命力,則法律將不可能幸存于世”。[23](p39)
人之法律觀不但要有法之美,而且要有法之信。“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23](p39)法律信仰是整個信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法律現象的主觀感受、認識和升化,是人對法律所體現的正義的神圣體驗,是個人生活終極目的的認同和情感歸宿,是對法律心悅誠服的崇拜與遵從。法律信仰作為一個客觀歷史事實早已存在,蘇格拉底以死詮釋了自己的法律信仰。崇法、信法是法律得以存在的精神基礎,西方的自然法觀念一直作為西方人的信仰在神圣之地指導著實在法的運行。沒有信仰,法律便失去意義之源,現行法律將失去導航的北斗星。當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法律信仰這一維度是蔽而不彰的。法律信仰無疑會使人們相信,它不僅可以實現現實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它能夠給人以心靈的寧靜和皈依,驅散內心的浮躁與迷惘。有了法律的信仰之光,就照亮了僵硬的理性規則,人們在法治的大道上走得更堅定、踏實、執著、久遠。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美]A·J·赫舍爾.人是誰[M].隗仁蓮,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3][美]詹姆斯·C·利文斯文頓.現代基督教思想[M].何光滬,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4][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5]張曙光.生命及其意義——人的自我尋找與發現[J].學習與探索,1999,(5).
[6][南斯拉夫]馬爾科維奇,彼得洛維奇.南斯拉夫“實踐派“的歷史和理論[M].鄭一明,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美]邁克爾·布洛維.公共社會學[M].沈原,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嚴蓓雯,譯. [M].上海:三聯書店,1992.
[15][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16]成窮.意義求索與宗教信仰[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5).
[17]張世英.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9]小原國芳教育論著選:下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0][英]霍布斯.利維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21]葛洪義.法理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
[22][日]穗積陳重.法律進化論[M].黃遵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出版社,1997.
[23][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梁冶平,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
責任編輯張豫
G416
A
1003-8477(2013)08-0172-06
張耀燦(1937—),男,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智慧(1970—),男,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流動站博士后,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0YJC7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