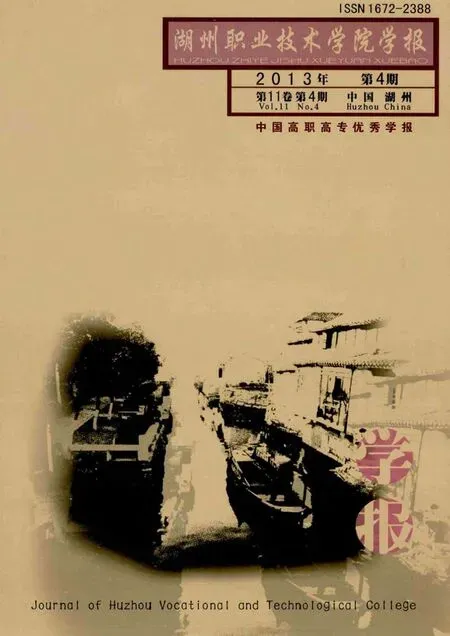蘇東坡與湖州秀才賈收的往來*
余方德
(湖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浙江 湖州 313000)
蘇東坡在湖州有不少朋友,為官者、秀才、寓居者、農婦,如著名詞人張先(子野),御史劉述(孝叔),得制科第一的陳舜俞(令舉),刻東坡墨跡于余姚縣治的長興人劉撝(行甫),隱于江淮的孫侔(少述),俞汝尚(退翁),溫父(節推)父子,樂清令周邠(開祖)等,頗傳韻事。而交往最久,感情最深的還數處士賈收(耘老)。
賈收人稱秀才。宋代秀才只是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不是漢代征辟的秀(茂)才,也不同于明清官學生員。他一生無功名,也未涉足官場。居湖州南門橫塘,即今蓮花莊西側,臨水有一小閣,雅名“浮暉”。蘇東坡任杭州通判時,常去吳山之巔“有美堂”。有美堂在北宋時名氣很大。據載,嘉祐初年(1056),宋仁宗為梅摯出守杭州,特制詩以寵賜之。嘉祐二年,梅摯便在吳山之巔修建有美堂。堂名就取自仁宗詩的前章:“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有美堂建成后,四方文人墨客留詩不絕。有一次,蘇東坡去時,正逢有美堂著人抄堂中所有題詠,隱名評定高下。揭曉結果:賈收的詩意、詩境、韻味最佳。蘇東坡本著詩人的本能,便將這首詩要了過去,仔細過目,吟詠一番。詩道:“自刊宸畫入云端,神物應知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嘗占一天寒。四檐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疏拙意,略無蹤跡到波瀾。”①[清]陳焯:《宋元詩會》,清刻印本(殘本)。蘇東坡也禁不住嘆道:“佳作佳作,有美堂被他寫神了……實為佳作也。”又問道:“這賈收何人?”有美堂的人告訴他:“賈收是湖州人,又名耘老,是湖州的一位秀才呢。”
“是一位窮秀才吧?你瞧這名字,賈收,假收,哪會有錢。人家推廣青苗法,哪個不是真收百姓的賦稅錢財啊?”有美堂的人禁不住都笑了起來。有人知情,說:“賈收不算窮,他雖無功名,但有幾畝田地,人又聰明……”“是啊。”蘇東坡說,“不聰明,怎能寫出這么好的詩詞來?”
不久,恰逢中秋,高大英俊的湖州知州孫覺帶了點湖州的土產和一壇烏程酒,專程到杭州去秘會好友蘇東坡。蘇東坡設家宴招待他,席上便問:“湖州有位賈收,又名耘老,你可認識?”
孫覺說:“聽說他很有才氣,詞美字秀。愚兄到任不久,整天瞎忙,尚沒拜會這位鄉賢。”
蘇東坡馬上表態說:“是的,這個人不能說是才高八斗,但卻不是一位平庸之人。這次杭州有美堂題詠評詩,知名者多也,但他名列榜首呢。看來也算是我們江浙的一位人物了。”
孫覺便將賈收的大名銘記于心。
孫覺湖州任第二年冬天,也正是王安石變法推行正力之時,江南夏秋以來一直飽受洪澇災害。孫覺負責江南運河湖州境內至淞江(今江蘇吳江松陵鎮)的堤岸維修。受江南轉運司的差遣,身為杭州通判的蘇東坡率人前來檢驗。①[清]同治《湖州府志》雜綴部分。到湖期間,孫覺設宴招待蘇東坡一行。因為政治原因,蘇東坡對此行不感興趣,而且情緒不高,不想宴席開始時,孫覺帶了一位身穿絲綢長衫,雖年過四十,卻神清面善的人,來到蘇東坡面前介紹說:“蘇大人,這位就是你曾問起的賈收先生。”
“賈收?”蘇東坡不覺眼睛一亮,忙從座位上站起,又問,“你就是那位在有美堂題詠的賈收?”
孫覺說:“是的。我們湖州城有名的秀才,賈耘老。”只見賈收不卑不亢,雙手微合,笑著問:“大人就是蘇通判、如雷貫耳的蘇子瞻先生?”
蘇東坡禁不住用雙手握住賈收的手,連連搖動說:“正是,我就是蘇軾。賈收,我好像在哪里見過你?”
“見過嗎?”賈收說,“不會吧?可能是因為我生了一張極為普通的面孔,這種面孔很多,你以為見過我。”“不,不,不!”蘇東坡懂佛教,他說,“這可能是緣分。有緣的人即使是初見,也好似相識了數年。久聞先生大名,知你詞美字秀……”“不敢,不敢。”賈收謙遜地打斷了蘇東坡的話,甚為尊重地說,“子瞻先生是詩書琴畫樣樣皆通,大名鼎鼎。想我草民一個,偶爾提筆寫幾句玩玩,怎敢與先生相比?”
蘇東坡忙高聲吟誦了賈收寫給有美堂的一首詞,博得席間喝彩聲。賈收也感動了,他想不到像蘇東坡這樣的名人卻能記住他草寫的詩,眼眶有些潮濕,心兒有些貼近,話語有些零亂,忙制止說:“蘇通判,不,蘇大人,子瞻先生,你別出我的洋相了,我不才,不才……”
蘇東坡仿佛失去了喝酒的念頭,忙吩咐孫覺:“孫知州,吩咐下人拿筆來,我來和賈收先生唱和兩首。”
孫覺十分了解蘇東坡,宴席旁一個人將屏風拉開,里面即是寫字臺,筆墨紙硯樣樣俱全。蘇東坡情趣上來,提筆就寫:“傾蓋相歡一笑中,從來未有馬牛風……”可見他的真心情。兩人連和了三首,方才入席吃酒。②邵鈺:《足音心跡集》,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10年,第76頁。不用說,蘇東坡那一天的心情轉好,喝到酒足飯飽時,他又提出要去賈收的“貴府”看看。
孫覺見時光尚早,正是午后雨收,陽光微現之時,便讓宴席散去。他陪蘇東坡,在賈收帶領下,來到距州府并不是很遠的南門橫塘,即今蓮花莊西側月河漾一帶。賈收住宅,雖不是豪宅,卻是臨水一閣,溪清柳綠,有房三間,清雅、干凈、舒服。蘇東坡走到閣前,見遠處田疇金黃,近水蘆白荷紅,連聲叫好,并說:“我老了,退下來就和你為鄰,也造個小閣,我們每天喝酒、品茶、吟詩,如何?”賈收聽了十分高興,連說:“好,好,好,你來小宅,已蓬篳生輝。如能與大人為鄰,實乃賈收終生之榮幸。”
賈收將蘇東坡讓于竹榻,自己和孫覺坐在竹椅上,搬上茶幾,便吩咐十余歲兒子敬上好茶水,大家方促膝交談起來。可惜的是,只談了十來句話,蘇東坡因貪杯,就在那張竹榻上鼾聲大作,呼呼入睡,弄得賈收兒子忍不住掩嘴笑出聲來。賈收喝了兩次才止住。身材高大的孫覺想到明日還要陪蘇東坡一行沿運河去松江,只能告辭去安排船只。
其實,賈收剛死了夫人,尚未再娶。賈收只得吩咐兒子去田間采摘些毛豆角,做了“熗毛豆”,自己去溪里摸了兩條魚,親自燒了魚,又炒了點花生米、雞蛋等幾個菜。
晚上,蘇東坡醒來,吃了晚飯,方才回湖州府內。
元豐二年,蘇東坡知湖州后,他和賈收已同老朋友一般,不拘行跡了。這時,賈收已納了小妾真氏。真氏只比他兒子大兩歲,生得十分嬌巧美麗,喜歡梳妝打扮,很得賈收寵愛。蘇東坡不太喜歡她,但這不影響他與賈收的友情。
一次,蘇東坡舟經水閣,賈收和小妾都不在家,只留下十六歲的兒子,蘇東坡就像賈收親人一般,獨自飲酒吟詩,又讓他兒子陪他觀賞月河漾周圍的風光,探看了幾家平民生活。有了“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香”;“從茲來往數,兒女自應門”詩句。后來,蘇東坡賦詩“便應筑室苕溪上,荷葉遮門水浸階”,也是有感于此閣而發。又有一次,坡公與客游道場山何山,途遇風雨,“舟人紛變色”,無奈回程,經賈收水閣小憩。這次,真氏為了取得蘇東坡的歡心,真的下廚去做了幾樣拿手的小菜,又取出私釀的米酒,將坡公哄勸著喝得醉醺醺的。坡公興起,命官奴秉燭,在閣壁畫風雨竹一支。吟詩紀事:“書生例強狠,造物空煩擾。更將掀舞姿,把燭畫風筱……明朝更陳跡,情景墮空杳。”“烏臺詩案”后,這幅即興的“風竹圖”被人摹寫刻石置于府學中。①邵鈺:《足音心跡集》,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10年,第278頁。
“烏臺詩案”中,蘇東坡被綁從府衙經館驛巷押往泊岸官船,驚動湖城百姓。賈收帶頭在駱駝橋上設下香案,百姓哭送太守,后又作解厄道場累月。
“烏臺詩案”出來后,蘇東坡被發配黃州任團練副使。元豐七年四月(1084),改任汝州團練副使,蘇東坡不想赴任,便在常州和潤州(鎮江)逗留,留戀太湖一帶山水。
在常州逗留時,他去潤州金山寺燒香拜佛,趕巧遇上了即將到湖州赴知州任的好友滕元發,兩人匆匆下山,盛宴交談。
滕元發到湖州上任時,蘇東坡托他去看賈收,并予以照拂。而且,也給了滕元發他在常州和潤州的住址,想讓賈收到太湖北岸去走走。滕元發到湖州不久,便遵囑去看望了賈收,約十余天后就安排賈收到常州去見蘇東坡。賈收到常州(一說在潤州)時,恰逢東坡買屋失利,奉旨復官,到山東沿海的登州去當知州。
兩人見了面,那份驚喜,那份傷感卻無法形容,徹夜長談,互通衷曲。喝著賈收帶去的烏程酒,品嘗常州風味的菜,吟詩唱答,感嘆世事。
東坡詩云:“五年一夢南司州,饑寒疾病為子憂”,“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誰從丘”;感嘆“可憐老驥真老矣,無心更秣天山禾”,頗生退隱之意,但不能如愿。此時賈收已老,滿頭灰白頭發,銀須飄飄,家境更顯清貧了,而且得了風痹之癥。可憐東坡當時因買房失利,也拿不出銀兩,他即贈耘老一幅竹石圖,說如果生活困難,可出售以作小補。如能保存,可傳其子無垢以留紀念。
元祐年間,他們在湖州又見到最后一面,該算是賈收有福了。從此,兩人只能書雁往來。紹圣二年(1095),東坡貶嶺南,舟經清遠時有寄耘老詩。詩中提到賈收的境況:“北雁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清齋十日不然鼎,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正虛。”世人傳誦的蘇東坡表達憤懣之情的名句,也出于此詩:“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欲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②嵇發根:《湖州史話》,合肥:黃山書社,2007,第94頁。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東坡66歲,遇赦自海南歸來。權衡再三,決定歸田西吳。他在常州寫信給賈收說:“某已買田陽羨(宜興),當上章。若許于此安置,將筑室以老焉。”又給湖州太守某的信中說“當至治下攪擾數日”,眷念湖州之情盈盈溢溢。然而當年七月,東坡病逝于常州友人處,既未定居陽羨,也未到湖州重會賈收,實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