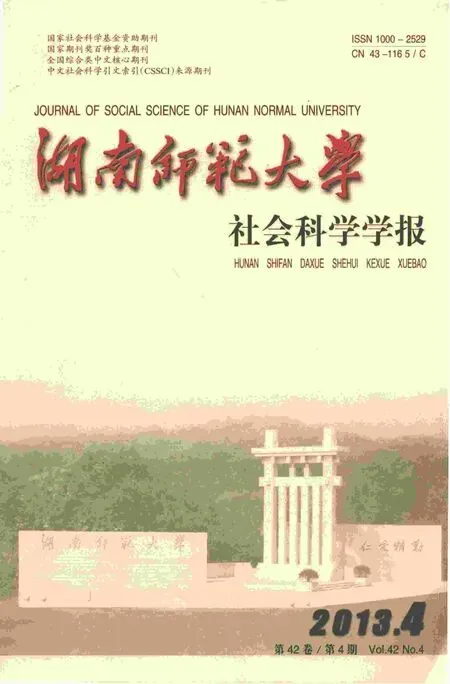市民社會的思想先驅:弗格森的啟蒙思想探究
項松林
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是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核心人物,是當時深具影響的市民社會理論家。在弗格森之前乃至同時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題主要是“國家”、“政府”。對于這一點,可以從那些經典著作的書名中得到最直觀的印象,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國家篇》)、西塞羅的《論共和國》、霍布斯的《利維坦》、哈林頓的《大洋國》、洛克的《政府論》……而據考察,弗格森是第一位以“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為書名的著作家,并在《市民社會史論》(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譯本譯為《文明社會史論》)中反復使用這一概念,更為關鍵的是其基本內涵已與政治社會、國家顯然不同。因而,要真正把握弗格森的啟蒙思想及其理論的原創性,最為核心的就是要緊緊抓住這一主題。
一、“civil society”范式:從“文明社會”到“市民社會”
在思想史上,“civil society”不僅是一個復雜、多義的概念,從英文的直譯上就有文明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等多重含義;而且還是一不斷流變的分析范式。歷史地看,主要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變遷:一是與自然狀態相區分的“文明社會”。與或是野蠻的、或是恐懼的、或是不便的“自然狀態”不同,“文明社會”最大的表征是有了“利維坦”式的國家、有了制定、裁決與執行公平正義的政府,因而在早期自然法與社會契約論者那里,“civil society”與“政治社會”是高度同一的。二是“civil society”與“國家”兩分。在這種意義上,“civil society”一般被翻譯為“市民社會”。三是“國家”、“市場”、“civil society”的三分。在這種界分上,“civil society”指的是一個既非政府又非市場的第三領域(the third sector),當前漢語界一般翻譯為“公民社會”,也有部分學者仍然使用“市民社會”這一概念術語。
長期以來,在“civil society”概念演變的第二階段上,即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相界分的方面,我們過分夸大了黑格爾的作用與貢獻,不同程度上忽視了之前許多思想家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所作的辨識與分析,尤其是忽視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弗格森在“civil society”范式從“文明社會”向“市民社會”意蘊轉變中的重要作用。
正如黑格爾所說,“市民社會是在現代世界中形成的”①,“文明”、“文雅”肯定是“市民社會”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作為一種分析范式,“文明社會”的概念之中沒有與國家相界分的含義,文明社會往往囊括的是處于文明階段的整個社會,既包括國家也包括市民社會自身。弗格森深諳這一點,在著述中,他經常有意識地將“市民社會”與“文明社會”區分開來,在涉及后者的概念時,他經常使用“polite society”、“polished society”。
弗格森不僅在概念的表述上對“市民社會”與“文明社會”有明確的區分,而且歷史地揭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起源,尤其是兩者的先后關系,從而有力地界分了市民社會與國家。與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同胞一樣,弗格森堅決反對與拒斥社會契約論者對社會與國家的先驗建構,無論是霍布斯式的單邊契約、還是洛克式的雙邊契約,抑或盧梭式的多邊契約。在《市民社會史論》的開篇,他就直接明了地指出,契約論者所謂的自然狀態概念違反了經驗和歷史事實,只是一種“臆想”。在《道德哲學原理》中,弗格森還深刻指出“絕不會有任何先于人類社會的契約”,契約“皆在社會成立后出現”②。在弗格森看來,“各國偶然建立了一些機構,事實上,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人類設計的結果”③。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群體中,弗格森最為強調社會之自生自發與“無意識之后果”,他雖然沒有沿襲斯密的“四階段論”,但他的社會演進“三階段論”——“野蠻社會”(savage society)、“未開化社會”(barbarous society)與“文雅社會”(polished society)也完全是自然變遷的歷史過程,并被龔普洛維奇(Gumplowicz)譽為“第一部關于社會的自然史”④。“社會的自然史”的要義在于認為社會的演進的動力機制是生存模式、生產方式與財產關系的變遷,并將其視為社會上層建筑之基礎,這充分說明弗格森不是一般意義上考察社會史、文明史、政策和藝術的歷史,而是隱含著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分的問題意識于其中,即從歷史源頭上揭示市民社會自身的歷史,并從這一歷史中凸顯市民社會先于、外在于國家。
為實現與維護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真正界分,弗格森還對國家的權力與職能進行明確的界定。弗格森明確斷言,國家的職能主要為“國防,公正的分配,國家自保和國內繁榮”⑤,并極力反對國家對人口的增長、對財富的經驗管理等方面的人為干預。弗格森曾尖銳地諷刺與挖苦道:“在人類生活更富足的地方,政治家自以為是他通過獎賞婚姻,誘惑外國人前來居住,并把本國人困在本土,使人口得到了增長。殊不知他就像寓言故事里的蒼蠅,為能轉動輪子,推動馬車而沾沾自喜:其實,他只不過是伴隨著運動中的物體而已。他奮力撥槳,只不過加速急流;他奮力搖扇,只不過加快風速而已。”⑥在弗格森看來,當政客插手人口與財富的增長,他只能增添麻煩,增加抱怨的理由,其他無能為力。其實,這方面也無需他們有所作為,“大自然要求強者應公正無私;但除此之外,她沒有把保存她作品的重任托付給強者不切實際的計劃。政治家能為青春的火焰添加什么燃料呢?他只要不熄滅這團火焰,那么它的作用就有保證了。⑦這充分顯示出,弗格森對市民社會的自主性地位充滿自信,斷然拒絕了國家所謂的倫理與道德的救濟。而在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雖是一個獨立的領域,但并不是自足的領域,在倫理上它只有通過國家這一更高級的統一體來整合,才能避免毀滅。就此而論,后來者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不僅沒有超越其思想先驅弗格森,反而滑向了“國家高于市民社會”的國家主義泥潭。
二、人性倫理與市民社會的精神
在《公民社會的脆弱倫理觀》中,塞利格曼在論及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深刻地評論道:“在很大程度上,市民社會的發展觀念是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背景下出現的,目的是要找到或者毋寧說是假定許多社會生活中日益感覺到的逐漸形成的矛盾的綜合。這些個人與社會、私人與公共、利己與利他間的對立,還有就是用理性還是情感來主導生活間的對立,事實上已經構成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基本要素。毫不奇怪,在今天,企圖回復到18世紀市民社會的觀念就是企圖重新承認那些私人和公共、個人和社會、利己和利他行為動力的綜合。”⑧對于市民社會之中這些復雜的“矛盾的綜合”,弗格森從人之復雜性、多樣性出發,不僅理順了個人與社會、私人與公共、利己與利他、理性與情感等的關系,而且有力闡揚了市民社會中自利、競爭、奮斗、協作等現代倫理精神,其獨到與創見堪與韋伯從“新教倫理”中揭示“資本主義精神”相媲美。
盧梭曾感嘆,“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于‘人’的知識”⑨。在啟蒙時代,有關市民社會中“人”的知識不僅非常欠缺而且相當混亂,甚至互相對立與排斥。比如:曼德維爾叫囂“私惡”即“公益”,把人看做是自私自利的壞蛋;而哈奇森力主人人都有分辨善惡的“道德感”,都熱心于“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在人性問題上,弗格森沒有在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還是友愛仁慈、人性是善還是惡的兩極之間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而是深刻地洞察出人性之復雜、人性之多樣:“關于人類的每一個描述都是錯綜復雜的:至善之中仍有惡,至惡之中仍有善”⑩。“如果說人性中有某些品質將它與動物天性的其他任何方面區分開的話,那就是人性本身在不同的氣候下,不同的年代里會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多樣性”?。具體地說,在弗格森看來,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還有“爭斗和分歧的天性”?。
在《道德哲學原理》中,弗格森將“自我保存的天性”稱為“自我持存原則”,即認為“人自然會對一切有用于自身之物產生欲望”。由此出發,他認為人追求欲望與私利的激情是正當的,“這一激情可以在自我持存法則中得到理解,其本身就是這一法則的具體應用”?。不過,他反對將人的“欲望”、“私利”僅僅庸俗化為謀取物質性或生理需求方面的東西或者說利益。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對“利益”進行語義辨析,認為“利益”(interest)這個詞應被寬泛地理解為“某種一般的效用和能帶來幸福快樂的東西”?,而不能將其等同于物質利益本身。那么,為什么追求自我利益的人經常被指責為是自私自利的呢?弗格森的辯護非常有意思,在他看來,自利常常被指責為自私,其過錯并不在于他們對自己關心的太多,而在于他們弄錯了要關切的東西。這種界分在弗格森的思想里甚為關鍵。也就是說,他并不反對人們對自我的關心,甚至不論程度如何,而他在意的是人們到底關心的東西是什么,僅僅是物質財富,還是諸如美德、榮譽、學識、智慧,等等,這是弗格森思想中較細致入微的方面。他反問道,為什么每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不認為一種好的理解力、一顆堅定的心、一個大度的胸懷是和胃或腭一樣是自身的組成部分,而且遠比他的財產或服裝重要??
在肯定人之自我保存的天性基礎上,弗格森還充分認識到:人天然具有結盟或聯盟的天性,不論是漂泊不定還是安居樂業,不論是協調一致還是紛爭四起,人類總是成群結隊?。在《道德哲學原理》中,他將這樣一種天性稱之為“社會法則”,并反復強調“如果自我持存法則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普遍的,也不能證明社會法則是無效的。引力定律的一般趨勢是使物體彼此接近,就像社會法則的趨勢是使人們去實現公共的善,或避免公共的害”?。基于人之社會本性,弗格森道出了諸多為當今社群主義者所津津樂道、廣為傳誦的話語:“人天生是社會的一員,……是整體的一部分”?;“我們應從群體中去看人類,因為他們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個人的歷史只不過是作為人類所思所感的一個細枝末節而已”?。需強調的是,弗格森這里論及的只是人性的一個面相,我們不能據此以偏概全地將其劃到社群主義的陣營之中。
其實,較之于人之社會性,弗格森更為關注人之“爭斗和分歧的天性”,這也是他與休謨、斯密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人性論上最大的不同。在弗格森眼里,人類不僅想和睦相處,而且也很喜歡對抗,兼有愛與憎兩種相對的感情。弗格森將這樣一種習性上升到人之本性的高度,其主要意圖在于強調市民社會中的人們應積極進取,應敢于競爭與冒險,應勇于奮斗與創造。為此,他非常煽情地進行鼓動:“人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不是安逸閑適的邀請,而是危險和困難的召喚;人類本身是出類拔萃的,決不是尋歡作樂的動物,也不是注定只會享受自然環境供他使用的東西。人就像狗和馬一樣,與其說喜歡所謂的享樂,不如說會按天性行事。處在安逸和富足中卻垂頭喪氣,遇到似乎要危及自身存在的警報時則精神振奮”?。弗格森還啟蒙民眾,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幸福是自己用雙手創造出來的,用他的話說,“在某種程度上,人不僅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而且還是自身軀體的創造者,并且自有人類以來,就注定要去創造,去奮斗”?。
三、市民社會的困境與出路
作為當時深邃的啟蒙思想家,弗格森不僅著力凸顯了市民社會相對于國家的基礎性地位,熱情謳歌了市民社會之自利、競爭、奮斗、協作等新風貌;而且在現代市民社會生發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般認為,在這一論題上,休謨最為樂觀,福布斯曾斷言:休謨對“風俗與道德的腐敗”、“分工的危害”均不以為然,“在休謨那里,也很難挖掘出‘異化’理論”?;即使是在公民人文主義方面極為著力的波考克看來,休謨沒有沉溺在對商業社會悲觀的習氣之中?。亞當·斯密的思想傾向較為復雜,學界爭論也比較多,但基本上都認為盡管其在《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中均對當時工商業的陰暗面如分工的異化、情感的異化等有所批判,但對自由競爭的商業文明基本上抱有積極樂觀的心態。而弗格森被認為立場最為悲觀,其對商業社會中分工的異化、德性的腐化、公共精神的缺失與政治奴役最為憂心忡忡。
第一,分工的異化。與傳統農業社會不同,以工商業為載體的現代市民社會有著精細化與多樣化的勞動分工。對于勞動分工,弗格森一方面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認為“商業的進步只不過是手工藝術的繼續分工”,并繪聲繪色地描述分工的功效:藝術家發現他越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任何工作中的一個特定部分,產品就會越完美,而且產量也會越多。制造商發現如果工人分工越細,個件上雇的工人越多,花銷就越少,獲利就越多。消費者同樣也要求每一種商品的做工會比那些雇來要一心多用的工人生產的商品更完美。?另一方面,他在專業化的分工中看到了很多問題:“在商業國家里,人們發現一個人只要扮演其中一個角色就夠了”,“藝術國家的成員除了本行以外,對人類事務一無所知”,“制造業最繁榮昌盛的地方的人們最不注重思考,而且不花氣力去想象,只是把車間看成是一臺由人做零部件的發動機”?。從這些簡短的話語中,我們能體悟到對于分工弗格森有這樣兩個層面的憂慮:一是,專業化的分工會導致普通勞動者的技能、知識、能力的單一性與片面性,從而導致人的單向度發展;二是專業化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地會強化職業分工,從而導致不同社會身份的固化。而后者是弗格森最為惋惜與痛恨的,譬如他對“政治家”與“公民—戰士”、“政治家”與“軍事家”之間的分工憤怒不已、耿耿于懷:“將造就公民的藝術和造就政治家的藝術區別開來,將制定政策和進行戰爭的藝術區別開來,無異于試圖分解人類性格、摧毀我們恰恰試圖改進的藝術。有了這種分工,我們事實上剝奪了保證自由民族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或者說我們為防御外敵入侵做好了準備。但是,這種防御可能導致篡權行為,而且國內也有成立軍政府的危險”?。
第二,財富與德性的腐化。在形而上的理論層面,弗格森也并不認為財富與德性是對立的,也充分肯定“商業包含了每一種可能營利的技巧,……是國家的偉大目標,人類研究的主要對象”?,甚至還反對將兩者對立的態度與政策,“一些關注公益事業的人們只想到人口的增長,財富的積累。另外一些人或許是擔心腐化墮落,只想到如何保持民族美德。人類社會對這兩者都負有重大責任。只是出于謬誤,人們把這兩者對立了起來”?。然而,弗格森又深感追求財富的欲望天然地具有腐蝕德性的傾向,它致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上而非德性上,“商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很容易就會走向腐化墮落,因為它們把財富看成是顯赫地位的基礎,而這種財富又不是靠個人的高尚和美德來維持的,還因為它們所關注的焦點是私利,認為私利是通向引人矚目的地位和榮譽的道路”?。在弗格森看來,這種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狂熱或者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他指出,“感官的需求是人類生活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如果把感官享樂看成是構成幸福的主體部分,這在思想上將是個錯誤,在行動上將是個更大的錯誤”?。
第三,公共精神的缺失與政治奴役。較之于古代社會,現代社會中人們日漸自由與獨立。對此,弗格森也認為這是社會的重大進步。然而,他又敏感地意識到:當個體將自我作為生活的主軸、將“公事”委托給“公仆”后,很可能就會出現政治冷漠、政治參與淡薄、公共精神缺失,特別是當公民只有追求自我利益的“私心”而丟棄“公心”的話,政治奴役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我們一心只想著我們牲口的繁殖,因而我們就看不到牲畜棚和草原以外的東西了。我們忘了少數人往往能讓多數人成為自己的獵物。我們忘了對窮人而言沒有什么比富人的金庫更具有誘惑力了。我們忘了要為自由付出代價時,勝利者的沉重的利劍就會失衡,插入相反的秤盤”?。
那么如何走出商業社會中潛在的諸如此類的種種困境呢?與盧梭建構“公意”的共同體、馬克思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思路取向不同,在弗格森看來,要治療現代性的病,要摒棄那種在享受安逸和便利的生活條件中所沾染的“脂粉氣”,要改變那種將人異化為機器上的零部件的車間,必須回返到古典傳統中去,重拾勇敢、愛國、政治參與等古典公民美德。
盡管弗格森曾宣稱“聰明、勇敢、富于愛心構成了人類完美的天性”?,但如果要讓他將其所心儀的德目表排一下座次的話,“勇敢”無疑是第一位的。對勇敢、勇氣及其重要體現的奮斗、競爭、尚武精神的推崇,是他的德性倫理中最醒目之處。與前所述,弗格森認為這種德性根源于人之“爭斗與分歧的天性”,并由此展開了對這類德性一連串的贊歌:“社會的競爭和自由民的煽動是政治生活和人類的基本動力”、“競爭是點燃美德的火炬”?,“一個朝氣蓬勃的人的習慣是在與困難作斗爭的過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享受安逸中形成的。洞察力和智慧是閱歷的結果,而不是在退隱和休閑中吸取的教訓”?。
在弗格森所推崇的德目表之中,“愛國”是又一重要美德。在弗格森看來,國民的幸福存在于他們對國家的熱愛之中,當共同體受到最大程度的熱愛,其成員的個人焦慮會得到減輕,其成員與公眾相關的才能也能得到發揮,“人的理智與心靈在履行社會義務和操持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可得到最好的培養”;因而,他認為每個人都應將國家看作是“全體國民的父親”,積極為其服務,以其利益為最高利益。?這樣的愛國情懷是典型的共同體主義的,是他人性觀的自然流露,他將人看做是“整體的一分子,一個組織或一部機器的一部分”?,并認為熱心追求整體的利益既是人們行為的最高目標,也是行為的崇高準則。對愛國德性之器重,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弗格森對市民社會之中人們公共精神缺失的強烈不滿,他經常譴責人們普遍對國家目標漠不關心、“沉迷于孤獨的消遣,或者培養出一種他們喜歡稱之為愛好的行當,諸如對園藝、建筑、繪畫或音樂的愛好”?,同時又“惟利是圖”和“見錢眼開”,逃避對國家的積極責任。
在弗格森的德性倫理話語中,政治參與不僅是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且也是公民的政治與道德義務,并被納入到德性規范之中。弗格森強調“參與”的德性,從根本上說,主要緣由有這樣兩點:一是對權力的不信任。在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群體中,弗格森最推崇社會秩序的自生自發,激烈反對理性狂熱與政治干預。他告誡人們:“政治制度也容不得輕信。盡管它們看上去不為人們的意志所左右,也無須接受人們的仲裁,但是,我們仍然不能依賴它們來保存自由。”二是與他的積極自由觀緊密相關:“自由是每個人都必須隨時自我維護的權利”、“人們是否有資格享有這一福祉只是取決于能否使他們理解自己的權利,能否使他們尊重人類的正當的權利要求;取決于他們本身是否愿意承擔管理國家和國防的重任,是否愿意投身于自由人的事業,而不耽于怠惰或者耽于用屈從和恐懼換取安全感的虛妄的希望。”基于此,他反復告誡人們不要淪落為陶工手中的泥土由君主來塑造。?弗格森對政治參與的濃郁情結,無論是前人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里,還是后來者阿倫特都望塵莫及。
四、結 語
弗格森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在道德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方面都有獨到的建樹,并在歐洲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然而長期以來,對其理論面相的解讀卻是復雜多樣甚至相互抵牾,譬如:哈耶克因推崇其“無意識后果說”與自生自發的秩序觀,將其定位為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人物;在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當代復興中,弗格森被看做是公民人文主義傳統中“最馬基雅維里主義”、“最后一位新羅馬主義者”?;而弗格森對古典公民美德與政治參與的“懷舊”,使他又常常被劃入社群主義的理論陣營。誠然,在一些深具原創性的思想大家們那里,思想面相常常是復雜而多維的,但如果呈現出極其矛盾之時,那就需要去反思是否存在問題。具體到弗格森而言,筆者認為無論在理解方式上還是對思想本身的解讀上都存在著一些問題:對于前者,那些試圖將其或置于自由主義或納入共和主義與社群主義之下的研究方式雖然很時髦但很有問題,因為在弗格森所生活的18世紀,這些“主義”譜系根本未成形,用它們來界定弗格森的思想顯然是不當的。對于后者,筆者認為當下對弗格森啟蒙思想的挖掘還不夠深入,在闡釋方面相當片面,甚至有片面取己所需的問題,哈耶克這樣,麥金太爾亦然。而其中最為要害的問題是沒有抓住弗格森啟蒙思想的核心關切,即對市民社會的啟蒙及其現代性反思。如果充分洞悉其對市民社會的深層關懷,弗格森的思想取向不僅不存在所謂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社群主義的理論張力乃至矛盾,反而是一嚴密的思想體系:從人性之“自我保存的天性”出發,勢必訴諸有助于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的市場機制,勢必認同“私利較之國家的精心安排更能保護商業和繁榮”?;從人性之“聯盟的天性”出發,勢必認為人是社會的一分子,勢必告誡人們不能只有“私心”還應有“公心”;從人性之“爭斗和分歧的天性”出發,勢必提醒人們勇敢、奮斗、積極參與的古典美德不可丟棄。由此更進一步地推而論之,人性是多樣的、人的需要是多元的,財富、自由、德性等對于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只論及某一方面,我們就或多或少偏離了人性本身,也就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民社會本身。
在現實層面,弗格森的問題意識與倫理關懷,對于當下我們積極培育公民社會亦具有很大的啟迪與警示價值。正如馬克思所刻畫的,在現代社會中,人有“公人”與“私人”這兩種不同面相”?,由于人們較為關注自我利益與私人生活,公民的公共角色不可避免地呈現為“消極公民”、“半公民”的態勢,政治參與的范圍往往就僅限于定期選舉,有的甚至連“投票人”的角色都不愿擔當,以致現代西方社會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公民“私人化”的癥狀。由此觀之,弗格森對愛國情懷、政治參與的積極強調是現代市民社會中日益嚴重的政治冷漠的很好解毒劑。基于此,最近有的學者撰文指出:“弗格森的警告發人深省:自由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民族精神的萎靡。而每一種體制的存續都有賴于個人活力,一個國家往往由于國民的邪惡而衰亡。精神萎靡可能導致的政治奴役,是最值得戒備的一種文明病。弗格森闡揚自由的德性,預言商業時代私人自由的擴張可能導致斷送自由的公共性危機,體現了啟蒙思想家深刻的憂患意識”?。
注釋:
①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97頁。
②???弗格森:《道德哲學原理》,孫飛宇、田耕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頁,第41頁,第41-44頁,第141頁。
③?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9,pp.20.
④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3頁。
⑤⑥⑦⑩?????????????????????????弗格森:《文明社會史論》,林本椿、王紹祥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1頁,第160頁,第157頁,第180頁,第11頁,第11頁,第17頁,第21頁,第14頁,第17頁,第62-62頁,第4頁,第49頁,第7頁,第199-200頁,第201頁,第254頁,第61頁,第162頁,第281頁,第47頁,第162頁,第261頁,第67頁,第282頁,第63頁,第62頁,第293-294頁,第160頁。
⑧布賴恩·特納:《公民身份與社會理論》,郭忠華、蔣紅軍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167頁。
⑨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62頁。
?Duncan Forbes: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308.
?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497.
?Fania Oz-Salzberger: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in Alexander Broadie (ed.),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9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0頁。
?高力克:《幽暗意識與蘇格蘭啟蒙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