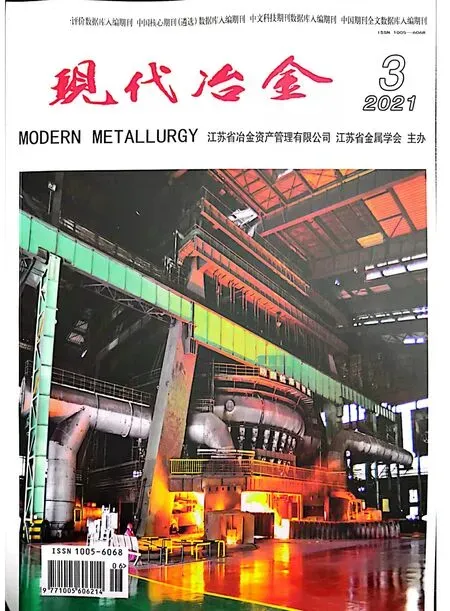寶鋼湛江高爐噴煤技術的進步
楊亞偉, 劉 煜, 羅 曉
(寶鋼湛江鋼鐵有限公司, 廣東 湛江 524072)
引 言
寶鋼寶山基地從1992年5月開始引進高爐噴煤工藝技術,經過十多年的研究與改進,形成了寶鋼獨有的一套噴煤工藝技術,在大高爐噴煤技術上取得顯著的成果,高爐噴煤比可達200 kg/t以上,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寶鋼湛江鋼鐵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湛江鋼鐵”)1BF、2BF噴煤設計是在總結和吸取寶山基地高爐噴煤設計經驗和技術的基礎上,由寶鋼工程設計,寶冶建設。在吸收寶山基地成功設計經驗的同時,也做了一些改進,譬如:2個高爐集中布置1個制粉塔,EM125型球磨機使用,噴吹罐代替倉式泵使用,自主研發長壽單管煤槍、濃相噴煤技術、高壓氮氣回收使用等等。整個噴煤系統包含集中供煤、CDQ處理裝置、制粉系統和噴吹系統。
在噴煤整體工藝設計上,湛江鋼鐵與寶山基地都大致相同,包括原煤輸送、煤粉制備、煤粉噴吹三大系統區域;原煤輸送都采用皮帶機輸送方式輸送、煤粉制備都采用負壓制粉工藝、煤粉噴吹都采用三罐并罐式總管加分配器的方式進行煤粉噴吹。
1 湛江鋼鐵高爐噴煤工藝簡介
1.1 原煤輸送系統
合格的原煤經過原料皮帶運輸至集中供煤配煤槽中,根據煤種配比單對煤種煤進行配重,設定對應給煤量,再由皮帶機輸送至制粉系統的原煤倉中。
1.2 煤粉制備系統
煤粉制備系統由三部分組成,即煙氣升溫爐系統、磨煤系統和收粉系統,這3個系統均有A、B、C、D四個系列。一號高爐煤粉制備工藝流程圖如圖1所示(二號高爐與一號高爐相同)。

圖1 煤粉制備工藝流程簡圖
干燥爐升溫系統是將150-200 ℃的熱風爐廢氣加熱至230-260 ℃后做磨煤干燥的熱介質。同時,又使制粉系統保持在惰性氣氛中工作,保證系統安全運行。
磨煤系統采用EM125新型中速球磨機,使用與寶山基地相同的負壓制粉工藝,在避免煤粉泄漏的同時也降低了整個制粉系統的漏風系數,降低整個制粉系統內的含氧量。
收粉系統采用了一級袋式收粉工藝,其特點是流程簡單、設備少、投資少。為了保證系統生產可靠,采用了防靜電濾袋和脈沖閥、防爆膜。
1.3 煤粉噴吹系統
煤粉噴吹系統由噴吹罐、噴煤總管、分配器、噴煤支管、煤槍組成。噴吹方式為三罐并罐式總管加分配器噴吹,這種噴吹方式設備簡單、有利噴吹、方便計量、減少自動計量的誤差率[3]。一號高爐噴吹工藝流程圖如圖2所示(二號高爐與一號高爐相同)。

圖2 噴吹工藝流程圖
煤槍使用內襯陶瓷單管煤槍,采用“濃相噴煤”技術,降低煤粉流速,減少管道磨損,同時也大大減少壓縮空氣的使用。
2 湛江鋼鐵高爐噴煤技術的進步2.1 2座高爐集中布置
1BF、2BF共同使用1個中控室,按標準每座高爐需配置集中供煤系統、制粉系統、噴吹系統共3臺控制電腦用于監視操作,2座高爐合并后只需配置5臺電腦監視操作,節約投資成本,減少人員負擔。同時2座高爐的集中供煤設備、噴煤設備也采取集中布置,減少占地面積,減少鋼結構等基礎投資,減少了人員占有率,如果2座高爐分開布置,2座高爐4個班組需要32人,集中布置后4個班組只需配置24人,減少人員配置,提高了工作效率。
2.2 使用EM125型球磨機
目前國內高爐噴煤中用的最多的中速磨煤機有EM型、HP型、MPS(ZGM)三種[1]。由于國內鋼廠原煤條件、工作環境、輔助設備的配置各有不同,因此選擇合適的品種型號,對保證高爐的生產、降低成本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EM型中速磨煤機因其安全性高、結構簡單、研磨件壽命長、維護量少等特點[2]在高爐噴煤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
2.2.1 設備結構
EM型磨機主要部件包括:底座、電機、減速箱、中間殼體、托盤、研磨元件、壓環、彈簧、彈簧壓架、分離器及液壓加載裝置,輔助設備有液壓站和稀油站。與輥式磨機相比,取消了密封風機的使用,加強系統密封性,減少了系統漏風率。
2.2.2 維護方便性、適應性強
EM型的研磨件無軸承,無需密封、潤滑、換油,免維護,不需要發生任何成本以及有計劃的停機,日常只需記錄磨損情況即可。內部結構形式對于異常出現大的難磨塊狀物如石塊、鐵塊等適應性強,只造成設備震動加大,不易對研磨件造成損壞。研磨件壽命長,更換周期長,大大減少大修時間及工作量,從目前使用看更換周期在3年以上。
EM型磨機適應性強,適用各種品質原煤,所研磨煤粉均能滿足高爐噴吹需要,日常生產中根據高爐需要調整合適參數即可。EM型磨煤機所研磨煤粉數據如表1所示。

表1 煤粉粒度表(湛江1BF)/%
2.3 噴吹罐代替倉式泵使用
與寶山基地使用倉式泵輸送煤粉的方式不同,湛江鋼鐵1BF與2BF之間的煤粉互送取消了倉式泵的使用,而是使用噴吹罐代替倉式泵,將1BF 3#噴吹罐返煤管道接到2BF煤粉倉,2BF 6#噴吹罐返煤管道接到1BF煤粉倉,在1BF或2BF制粉設備故障檢修時,煤粉供給不足可將1BF 3#或2BF 6#噴吹罐切出程序,進行手動送粉操作,保證高爐煤粉噴吹(返煤速度可達到40 t/h)。
2.4 自主研發的長壽單管煤槍
結合寶山基地多年來的高煤比操作經驗和國內外高爐目前普遍采用的煤槍技術,為降低噴煤槍冷卻氣量和工序成本,湛江鋼鐵自主研發出單管長壽噴煤槍,并在2015年9月25日投產的1號高爐、2016年7月15日投產的2號高爐上使用。生產實踐證明,該煤槍使用效果好、壽命長,由于取消了冷卻用氣,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2.4.1 湛鋼單管煤槍與外冷式套管煤槍的差異
(1)單管煤槍使用中是不需要通冷卻氣的,大幅度減少了冷卻氣的使用,降低壓縮空氣的消耗,減少生產成本。
(2)具有擋環的內襯陶瓷煤槍前端增加了擋環,有效解決了煤槍出口內襯陶瓷斷面尺寸不均勻的問題,實現了均勻噴煤。同時,擋環能有效防止內襯陶瓷位移的問題,確保煤槍的使用壽命;據統計,這種煤槍的使用壽命能確保在高爐的1個定修周期(100天)內不損壞,而且,在1個定修周期內煤槍可重復使用3次(3次臨時休風,每次可拔出再插入使用),而套管煤槍每次拔出后由于冷熱不均槍頭變形不能再使用。
2.4.2 湛江鋼鐵長壽單管煤槍的使用效果
通過在煤槍端部設置耐磨材料防位移鋼制阻擋裝置,消除了各個煤槍端口的內徑差異,風口圓周噴煤更加均勻。湛江鋼鐵2座5050 m3高爐使用這種單管長壽煤槍,都取得了很好的使用效果,在噴煤比180-185 kg/t、噴煤量90-100 t/h的生產指標下,煤槍操作參數如表2所示。

表2 湛鋼高爐煤槍操作參數
與外冷式套管煤槍相比,湛江鋼鐵高爐采用長壽單管煤槍,省去外冷氣取得了兩方面的好處:1)節省外冷氣消耗7200 m3/h,按0.1元/m3價格計算,每座高爐一年節約成本621.3萬元;2)減少了外冷氣對實際風溫的影響14 ℃,節約焦比1.2 kg/t,每座高爐成本節約862.1萬元/年。
3 結束語
在吸取寶鋼高爐噴煤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湛江鋼鐵高爐噴煤進行了多項工藝改進,大膽使用新設備,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新設備、新工藝的使用取得了很好的使用效果。雖然使用初期出現很多問題,經過不斷摸索、改進,逐漸形成一套湛江鋼鐵高爐獨有的新噴煤技術,設備運轉越來越穩定可靠、設備利用率越來越高,滿足高爐高煤比生產的需求,為高爐生產穩定順行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