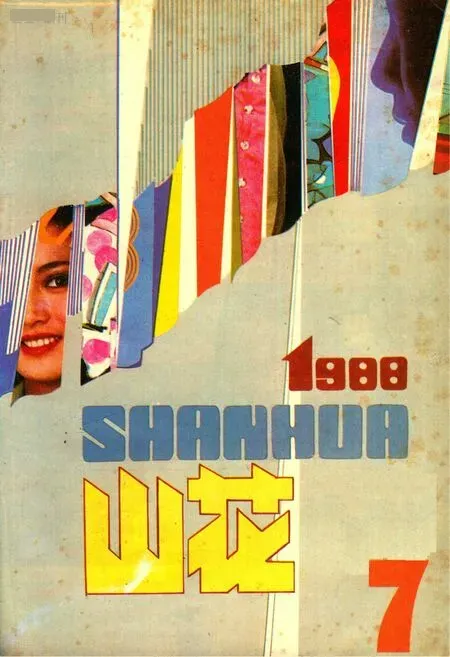人物
殘雪
蒲三在這些人當中算是個人物。“這些人”指散居于城市水泥森林中的失眠者。失眠者在京城是一個很大的群體,由于無數夜間活動的經驗積累,使得他們可以辨認出這個群體中的成員。比如在電梯間,或者在車庫里,有兩位失眠者相遇了,他們便會微微向對方點頭示意。至于他們據以辨認的標志,據說只能靠心領神會。那么存在著大規模的夜間活動嗎?有人說這事很難判斷。活動肯定是有的,外界關于這事傳說得很多。失眠雖沒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影響到城市的發展,但這種難以描述的夜間活動畢竟有點特殊。又由于這個人群在逐漸擴大,所以議論總是有的。
蒲三的出類拔萃之處在于不把失眠當失眠。他在早年當鍋爐工時就開始失眠了。一開始夜里還能睡四五個小時,到后來就只能睡一兩個小時了。而且天天如此。失眠影響了他的健康,他只好辭去了鍋爐工的工作,做了薪水很低的金融大樓的保安。做保安那一年他45歲。保安的工作就是在樓里面巡視,遇到糾紛去處理一下,沒事時也可躲在某個角落里休息一陣。蒲三覺得這個工作很適合于他做。做了一年多保安后,蒲三就發現了自己的睡眠規律,而且懂得了自己的失眠并不是疾病,只是睡眠異于常人罷了。保安工作事情并不多,蒲三只要一歇下來就躲進清潔工放工具的小房間,坐在小板凳上打個盹。他幾乎在五分鐘內就可以入眠,并隨時可以恢復清醒。有時候工具室鎖上了門,他居然可以在大門旁站著入眠,連雙眼也不閉上。如果這種時候有人叫他,他便微微一怔,立刻回應那人。因為他的工作的性質,他這手絕活并沒有人發現。他在失眠者當中也不是因為這個出名的。
蒲三既然練就了隨時可以入睡的本事,在他的生活中也就不再存在失眠的問題了。從此他并不認為自己到夜里就一定要睡覺,他成了個喜歡搞夜間活動的人。他的活動范圍一般是在老城墻下面的護城河一帶。那塊地方是像他這樣的夜貓子的聚集之地。
蒲三從小在京城生活,對老城墻這一塊比較熟悉,而且他的家離這里也很近。所以他深夜出來散步時,往往一走就走到這邊來了。剛開始的時候,他在這個幽靜的處所呆得很愜意,也并沒發現其他的人。蒲三走累了就在河邊的石凳上歇一下。他在河邊休息其實就是在睡覺,只是外人看不出來罷了。再說那么晚了哪里會有人守在那河邊觀察他?
人們是慢慢出現的。有一天,蒲三在休息時被河里的水響驚醒了。他看過去,那條窄窄的河當中好像是個女人。她喊“救命!”蒲三正在脫衣下河,女人卻又飛快地趟著水上岸了。蒲三尷尬地站在原地。
“這個時分還來河里戲水啊。”蒲三說。
“我活得不耐煩了嘛。可是你怎么在這里?這里原先是沒有人的,我從來沒遇到過人……你是人還是鬼?你這該死的!”
她氣憤地離開了。蒲三想,為什么她和自己都認為這里沒人?女人是去投水的,看到有人就后悔了,她不愿死在別人眼前。蒲三覺得自己特別能理解她的情緒。他為自己的在場感到歉疚。
又過了些日子,蒲三從高高的城墻走下來時,看到黑糊糊的樹叢里有兩個影子。兩個影子纏在一起,分不出男女。蒲三盡量不看他們,一直走下去,下到了河邊才停下來。這時候那上邊的人發話了。
“我們看到你天天來這里,你是如何解決失眠問題的?”
“你同我們一樣天天來,其實你何苦要天天來,像有人給你布置了任務一樣。”
蒲三聽清了,這兩個說話的都是男人。他心里有點激動,這種死寂的夜,卻原來是一場騙局。就像人看景色看久了,景色中就會出現雜七雜八的東西一樣。
“我沒有失眠的問題。我是來這里搞活動的。”蒲三說。
他說了這句話之后,那上面的那兩個人就開始笑。蒲三看見他倆像兩條蛇一樣舞動著。難道他的話真的那么好笑?
“他沒有失眠的問題,可是天天來這河邊占著我們的位子。”
蒲三感到慚愧,因為他說的是事實。他能感到這兩個男子的痛苦。可他自己呢,一點兒也不痛苦。他早就忘記失眠會有痛苦了。
他沿著護城河往東走去。走了沒多遠,他就感到了那兩個人在尾隨他。蒲三想,他倆大概想向他取經吧。誰不想戰勝失眠?
可是他估計錯了。那兩人中的一個將他用大棒打倒在地,使他在深夜領教了真實的睡眠是怎么回事——他昏睡到天快亮才醒過來。
這個事件使蒲三明白了,此地并非無人之地,有各式各樣的失眠者躲藏在樹叢里,甚至河里。那么,是他加入了他們,還是他們跟在他后面而來?應該是前者,可他怎么又老覺得是后者?他還沒把這個問題想清,又了遇到了新人。
新人坐在他常坐的河邊石凳上。是一男一女,一人占一個石凳。
那么多日子,這石凳都空著,這兩個人就像地下長出來的一樣。他們在看河水,聽到腳步聲,立刻一齊轉過身來。
“戶外空氣新鮮,比起室內來舒服多了吧?”蒲三和他倆搭訕地說。
“一點也不舒服。”中年男子陰沉地說。
“在失眠的時候,至少沒有屋里那么煩悶吧。”蒲三又討好地說。
“比屋里更煩悶。”還是男子答話。
“那你們還到這里來干什么?”
“我已經告訴你理由了。”
即使是在黑暗中,蒲三也隱約看到了他倆警惕的目光。他擔心木棒事件重演,就加快了腳步。可是那女孩叫起來了。
“你停下,我有話要問你!你,我看出來你精神抖擻。我想問你,你是如何樣處理好那件事的?”

陳紅旗生活照
“我告訴你答案吧: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存在那件事。好多年以前,我就將睡眠取消了。你們瞧,我多么灑脫!”
蒲三說話之際瞟見那兩個黑影從城墻上沖下來了。他果斷地跳進那艘小船,將船劃到河心,又劃到了河對岸。他聽到那兩個青年在說:
“你們怎么放走了這個人,他可是個人物啊!”
于是蒲三就從別人的話里得知了自己是個人物。
他還陸陸續續地在老城墻下面遇見了一些別的人。他的夜間活動只限于這塊地方,不光是因為只有在這里他才是個“人物”,也因為此地讓他產生信心。
黑暗中,那些人對他的存在感到好奇和愛慕,口中發出“咦,咦……”的驚訝聲。是的,正是愛慕。包括用木棒擊倒他的舉動。那是他們想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同失眠告別了。年輕人真頑皮。
夜間的病友之一追隨蒲三到了金融大樓。他是一名二十來歲的青年,他要親自證實蒲三取消睡眠這件事。小青年姓郭,是一名司機。
“蒲叔,我對您很崇拜。在土城墻那里遇見您以后,我就決定了要做您這樣的人。您一定會問我為什么,我告訴您吧:因為我要擺脫痛苦。我現在太陽穴這里就疼得厲害,所以我就來找您了,我班也不上了。”
蒲三斜眼看了看他,板著一副臉,說:
“沒有用的。我的太陽穴比你的疼得還厲害呢。你離開一點吧,影響不好,我正在上班呢。老黃!老黃!有情況嗎?”
小郭羞愧地躲到了圓柱后面。他一直站在那里,遠遠地看著蒲三,一直熬到了吃中飯時分。
送盒飯的車來了,小郭也要了一盒飯,他看著蒲三,滿心都是困惑。
“你還沒走啊,和我到工具房里來吧。”蒲三招呼小郭說。
小郭進來后,蒲三就把工具房的門關上了。
里面很昏暗,兩人站著吃飯,很快吃完了。
“蒲叔,您的精神真好。”
“噓,別說話,我在睡覺呢。我來教你,背貼著墻,雙手放在肚子上。好!關鍵是要專心。你往哪里去?好,去吧。”
小郭貼墻站著,他并沒打算動。他在想,蒲叔說自己要往一個地方去,那么,他想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但蒲叔說他已經上路了,他就權當自己正在旅游吧。忽然,大樓里響起了非同尋常的喧鬧聲,如潮水一樣,越來越近了。他又聽到面前的蒲叔仿佛在墻縫里講話,聲音嗡嗡嗡的聽不清。
小郭感到欣慰,因為他們將嘈雜的噪音關在門外了。他雖然沒有目的地,但他是在同蒲叔旅游,他要放松自己,輕裝出行。蒲叔的聲音終于在房里響起了。
“小郭,你走到了嗎?”
“還沒有呢,蒲叔。這里有團陰影,我該繞過去嗎?”
“你怎么問我?要自己決定!”
小郭本來是隨便說說好玩的,但是蒲叔一開口,他就真的看見了樹林和深溝,還有在云中昏睡的滿月。他的情緒變得激動起來。他要不要跳過那條溝?跳吧跳吧,別讓蒲叔笑話。他做了個起跳的動作,從墻上的金屬桿掉下好幾個拖把,弄得他褲腿上盡是水。
房門一下大開,清潔工老頭進來了。
“你這個該死的家伙,在里頭搞破壞啊!”
小郭看見房里只有自己一個人,蒲叔根本不在那里。他狼狽地走出去,屁股上挨了老頭一掃帚。老頭教訓他說:
“不要以為可以從蒲三那里學到什么,跟著他走,路只會越走越艱難。他啊,從來不走正道,屬于那種來去無蹤的人。”
小郭來到大堂里,看見蒲三站在大門旁邊。蒲三那渾濁的目光引起了小郭的興趣,他想,他是在工作還是在睡覺?他走到蒲三右邊,隔得很近地去觀察他,可是蒲三連眼珠也不向他轉過來。小郭心里對蒲三生出了深深的敬意。他不再猶豫了,抬腳向大門外走去。
清潔工追了出來,拍拍小郭的背說:
“這就對了,要遠遠地離開這個人,只有這樣才會有出息。你不是想撈個行政干部的工作干干嗎?心里頭要有主心骨。”
“我并不想當行政干部,我是個司機。”小郭說,心里直想笑。
“那也差不多吧。來找蒲三的人都有野心。你走了就不要再來了。”
小郭仔細打量了一下白發蒼蒼的老頭。他看上去大約快八十歲了,但那兩只眼睛卻亮得出奇,像錐子一樣刺人。金融大樓里面怎么會藏著這等人?小郭慌張起來,他在老頭目光的逼迫下匆匆離開了。
走到護城河那里時,小郭看見了女病友阿忙。阿忙坐在蒲三常坐的石凳上。小郭感到奇怪:阿忙怎么白天也在這里?難道她從昨天夜里起就一直沒離開這個地方?
“阿忙,你心里還害怕嗎?”
“害怕。可是我看著你,我覺得你已經不害怕了。你是如何做的?”
“我們一起走過河去吧!”
小郭說著就脫鞋,阿忙也脫掉皮鞋。他倆一塊下了水。到了河中水深的地方,因為兩人都不會水,就掙扎起來了。阿忙喊:“救命!”
那只木船過來了,兩人從兩邊分別攀沿著上去了。
小郭離開了阿忙,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家是在單身公寓16層,他進了房門,心里還在歡唱著。多么不尋常的一天啊。他叫了外賣,吃了一碗面,迫不及待地等著天黑下來。
小郭在人行道上追著蒲三喊:
“蒲叔!我到過那里了!!”
蒲三回過頭,陰沉地問:
“雙手緊緊地抓住樹椏了嗎?”
“抓住了!抓住了!下面有成群的惡狼!我可以懸空吊一整天。現在我全身都輕松了,哪里都不疼。”
小郭的心在怦怦地跳,他倆已經走到了古城墻的缺口那里。
那兩個男的從樹林里竄出來,其中一個一拳將小郭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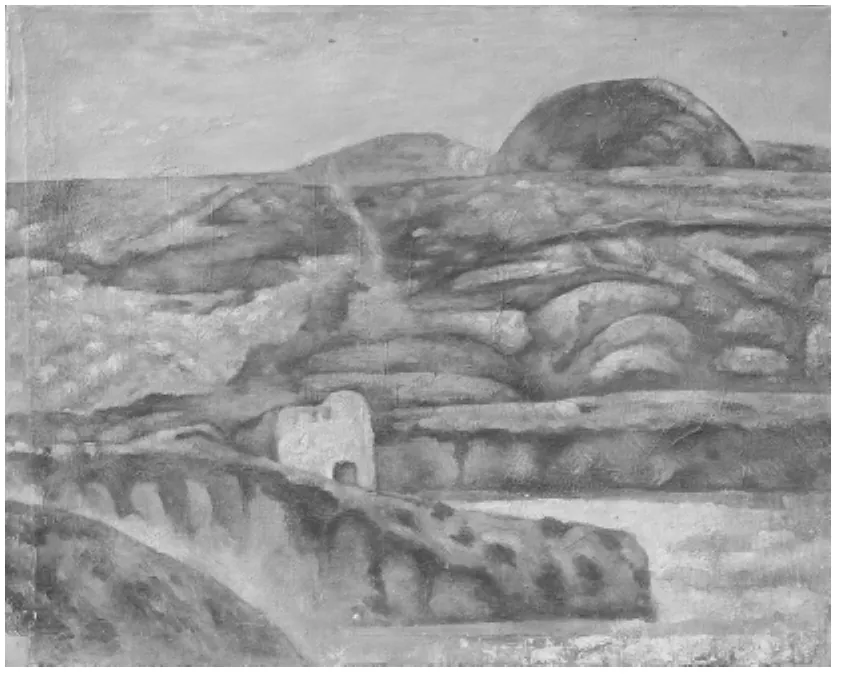
陳紅旗作品-《馬鞍山》 40×60cm 1987
“我,我是小郭啊。”他絕望地說。
他的肚子上又挨了一棍,他在暈過去之前聽見那人說:
“藝芳,我們還要干掉多少個這種貨色?”
蒲三鎮靜地繞過面前的騷亂,頭也不回地向河邊走去。
他朝著空空的河面說:
“都出來吧,呆的時間夠長了。”
河里一陣水響,有六七個人上岸了。他們朝市中心的方向走去,各走各的,默默無聲,很快就走散了。
小郭在晚風中蘇醒過來,他想起了蒲叔。他是同他一塊來這里的,他到哪里去了呢?他站起身來,看見阿忙滿腹心事地走過來了。
“阿忙!”他熱切地呼喚她。
“你是誰?”阿忙說話時用一只手遮住眼,仿佛在擋住強光的照射。“我是到那里去的,你不要叫我,我要悄悄地。”
小郭明白了,女孩已經見過了蒲叔。
“我是司機小郭啊,是你的好友!”
“我要上路了,那邊在等我,再見。”
小郭聽到了水響,河里駛來了兩只船,船上站了不少人。
小郭朝那些人大聲說:
“你們和蒲叔約好了嗎?”
沒有人回答他。他很羞愧,他不該問這么傻的問題。
那兩只船駛到東邊去了,又有兩只船過來了,船上也站了不少人。
小郭感到所發生的情況對自己有威脅。怎么河里會有這么多人都往東邊去,只有他一個人孤單地呆在岸邊?不是連阿忙也往東邊去了嗎?蒲叔啊蒲叔,你到底耍的什么陰謀?你去掉了我的痛苦,可我現在不知道該干什么才好了啊。白天里我可以開出租車打發時間,夜間時間這么長,我總不能整夜在這里走來走去吧?到城里面去閑蕩是危險的,三個病友都被謀殺了。只有古城墻這一塊地方是安全的,這是大家的共識。可今天是怎么回事?瞧,又來了兩只船,又往東邊去了!這些病友,要拋棄此地了嗎?
小郭在絕望中嘆息著,看著昔日的病友一撥一撥地往東邊去。忽然,他想起了清潔工對他說過的話:“……跟著他走,路只會越來越艱難。”
這句話給了小郭某種暗示。他信步亂走,走到了“白夜”酒吧那一帶。那里是謀殺發生頻繁的場所,街道亮得像白天一樣。他豁出去了,可是他不愿進酒吧,他只想在這些酒吧外轉一轉,要是能碰到一名失眠者就更好。
有一排出租車停在酒吧外,一個同行伸出頭來看見了小郭。
“上車吧,我把你送回家。”
小郭不愿和同行聊天,就鉆進了車子的后座。
后座有一個人坐在那里,很面熟。
“蒲叔,我又到過那里了。”小郭說,心里無比舒暢。
“你閉一會兒眼吧,夜還長著呢。”蒲三說。
小郭閉上眼,他聞到了蒲叔的氣息。蒲叔在河邊用一只瓢舀那些蝌蚪。他將那些小動物舀上來又撒下去,小黑點們在陽光下活跳跳的。蒲叔折騰些什么呢?小郭想到這里時,車子猛地一下停了。車里頭只有他自己。
他下了車,感到陽光有點刺眼。單身公寓的鄰居對他說:“早上好!”
他自己那輛桔紅色的出租車停在對面了,那上面積了些灰。難道他已經幾天沒出車了嗎?
蒲三夜里過得很快樂,因為大家都行動起來了。古城墻這一塊是如此地沸騰著活力,令他有點吃驚。他仿佛聽到這些男男女女們全都在壓低了嗓門說著:“蒲三,蒲三……”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每次夜風將那些悄悄話送過來,他聽到的都是這兩個字。白天里,他在金融大樓被人認出時,那人走攏來對他說:
“蒲三叔,您真是個人物。”
當時他還愣了一下呢。后來他心里冒出一個近乎無賴的念頭:就算全城的人都記住了他的模樣,也沒有關系。他要讓這些人都知道,失眠并不是一種病,反而是一種延長生命的技巧。也許,他們全都心領神會了。比如司機小郭就明白了。昨天他看到他滿面紅光地站在自己的出租車旁。現在這些人都從樹叢里走出來了,有好幾十人呢。他們都要往東邊去,蒲三站在那里擋了他們的路,所以他們擦身而過時就不斷地撞擊著他。蒲三每被撞一下,腦袋里就亮起一朵火花,這火花令他渾身感到愜意。他又一次回想起從前的那個日子。他無意中發現了這個團體,這個團體就把他造就為一名“人物”了。如果沒有這些病友,如果他們都不從樹林里和河里出來,他也就不是今天的蒲三了。所以不是他在傳播知識,反而是這些人將知識傳播給他,只除了小郭……但他果真是小郭的老師,而不是相反??

陳紅旗作品-《出工》 72×60cm 油畫 1992
眼看著病友們快走完了,蒲三也想跟過去看看。但他被一老頭攔下了。
“不,你不能去。那邊的空氣不適合你的肺。”
“我的肺?”蒲三吃了一驚,“我的肺出問題了嗎?”
“我沒有說出問題,我的意思是,到了那邊,空氣就變了。”
“那么我還是留在這里吧。”
“你最好留在這里,你不適合那邊。再說這里也需要你嘛。”
老頭去追那群人去了。
蒲三鉆進樹叢,想隱蔽起來,奇怪的是樹林里頭并不安靜,各式各樣的人都在里面交談著,還有人唱戲。他鉆來鉆去的,卻又沒碰到一個人。仔細一聽,似乎有兩個人都在說同一件事,即,他們能夠留下來是多么幸運,現在他們愛留多久就留多久,而那些走掉的人可就一去不復返了。蒲三覺得這兩個人說話的口氣有問題,他們聽起來不像是多么幸運的樣子,反倒是像在嫉妒那些走掉的人。大概他們也很想“一去不復返”吧。
“那邊的空氣到底如何?”蒲三沖著那兩人的方向高聲說,“有人說那邊空氣不同,可那邊也是京城,會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蒲三一講話,那兩個聲音就沉默了。而且所有的聲音都沉默了,只有風在吹樹枝——沙沙,沙沙。他在心里暗暗掂量:是留在這里好呢,還是一去不復返好?當然還是這里好,這里是他經營多年的老巢,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可以心想事成。他不嫉妒那些走了的,他們走了,又有人來,一撥一撥的,古城墻下是塊寶地。那老頭不是說這里需要自己嗎?可見自己是個老資格,是個人物,是這些人的主心骨。
蒲三從樹叢里鉆出來,走到護城河邊,坐在他慣常坐的石凳上。因為內心很舒坦,他的大腦一會兒就進入了休眠狀態。遠遠看去,他很像一個釣魚的老翁。
月亮突然就出來了,在水面閃著銀光。蒲三在似夢非夢的地方想起了他的家人,他知道這個時候他的妻子和兒子正在酣睡。他輕輕地對妻子說:“你受累了啊。”可他妻子的模樣并不像因他而受累。他分明聽到她在那間房里回答說:“我成了一位人物的老婆,這事真蹊蹺!”蒲三臉上浮起笑容。
一陣響動驚醒了蒲三,有人坐在同他并排的那張石凳上了,是位女孩。
“是阿忙啊。”
“我從那邊回來了,只有我一個人回來了,因為我惦記著您。蒲叔,我總拿不定主意,您認為這對我的病有好處嗎?這是個弱點嗎?”
“可能這是個弱點吧,一個對你的病有好處的弱點。你到了那邊,可又想著這邊的好處(并不是惦記我),你要把好處都占全。我們這種病就是一種要把好處占全的病,大富大貴的病,對吧?不過呢,我們也還是做了些好事吧,我們使京城變得美麗了一點。你同意嗎?”

陳紅旗作品-《剪羊毛》 72×60cm 油畫 1992
“我同意。我崇拜您,蒲叔。您為什么不肯上我家來呢?我想讓我父母看看我所崇拜的人。”
“我不愿去。我可不愿在你家睡著了,那真丟丑。”
女孩站起來要走了,她說自己和蒲叔說了話,心滿意足了。
蒲三還是坐在那里,他在等小郭。
小郭天快亮時才來。他說:
“早晨的空氣多么好啊!我是從東邊來的,東邊的空氣比這里還要好!他們將那邊改造成了一個大湖,滿湖都是野鴨子。”
“可你為什么要趕回來?”
“因為蒲叔在這里嘛。我應該將城市的變化告訴您。我著急地往回趕,我怕您提前回家了。”
小郭開著他的桔紅色的出租車消失在馬路盡頭。蒲三在心里說:“小郭正在開始他快樂的一天。”
蒲三沐浴著早晨的陽光,他在人行道上走得很快。盡管城市已經喧鬧起來,他的耳邊卻仍然響著夜間的低語:“蒲三,蒲三……”
他從飲食店買了大餅和油條,站在路邊吃完了,又掏出手巾擦了嘴和手,這才朝馬路對面的金融大樓走去。
他到得太早,交班的小伙子很高興,因為他可以提早回家了。
“蒲伯,夜里有人來找過您了,是一個蒙著面的漢子。他說您不在家里,他問我您到底在哪里。我心里一急,就說您大概在古城墻那一帶。其實我也是瞎猜的,我隱隱約約聽人說過。他找您會有什么事?為什么要蒙著面?見不得人嗎?”小伙子迷惑不解。
蒲三嚴肅地板著臉沒有回答,這是他一貫的表情,年輕的保安并不見怪。他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就回家去了。
蒲三走進空無一人的值班室,給自己泡了一大杯茶,慢慢地喝著。那人推門進來時,蒲三連眼皮也沒抬一下。
“我知道您埋伏在這里,這樓里并沒有情況,我不過在這里混飯吃罷了。到了下午,從這扇窗望出去,您可以看到太陽一天比一天早地落下。這里面這些年輕人越來越沒有耐心了。”蒲三聽見自己的語氣有點急躁。
“蒲叔,您這么一說我就放心了。您到過了古城墻那邊,現在又回到了這里。這棟大樓就是為您蓋起來的,我一直這樣想。您站在大門那里的時候,我看見那根圓柱微微地向您傾斜。”
蒲三抬起頭來時,那人已經不見了。走廊里竟沒有響起腳步聲。
他站起身來,從那扇窗戶望出去,看見那輪紅日正在冉冉上升。低頭再看茶杯,水里的茶葉正飛速旋轉,發出咝咝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