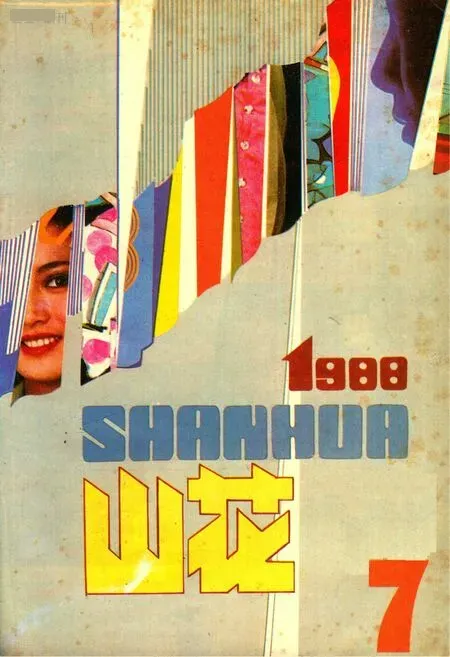梅花引
楊小凡
在故鄉,農歷十月初一是個坎。過了這一天,說入冬就入冬了。
白天從黃土里飄出來的霧汽,在深夜里先肅成露,再凝成霜,到早上就成了一天一地寡白的霜雪。有微風吹過,哪怕一丁點兒風也不吹,只要早醒的公雞叫幾聲、餓一夜的豬吭幾聲,或者早起的老人倚門長咳幾下,樹上的葉子就會撲簌簌地飄落一地。
村子是一天比一天瘦了,誰家的黑狗、白山羊和灰鴨子都縮了身子,村前的泓水也消瘦而寂靜,再也沒有夏天那汩汩的歡笑了。
十幾天前,人們就開始添加衣衫御寒了,上年紀的人已經穿得很臃腫。這樣的日子就算寒日了。陽世的人要添衣御寒,那另一個世界的親人們呢?不也得添衣裳嗎。當然,這是用陽世的標準衡量另一個世界。但,我們的心里還是掛念著已故去的親人。早清明、晚寒日,燒紙錢紙衣祭祖的規矩就這樣傳下來了。我常想,這確是一種形式,但這形式能傳下來幾千年,這也許就是人活著的一些意味,一種念想。
這兩天,我雖然費些勁兒,但還是調休了,我決定要回故鄉給逝去的母親冬祭。
進村的時候,已經快晌午。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村里竟無聲無息的靜,靜得能聽到小風在樹梢頭的嬉戲聲。
下車的時候,我只看到幾只母雞圍著村口那棵老桑樹在轉圈兒,像是在做一種游戲。它們見到我,像沒有看到一樣,只是咕咕地叫兩聲,接著又你追我趕轉起圈來。再向里走,就見一黃一白兩只狗互相咬著身上的毛,對我的回來也沒有發出一聲吠,只是其中一只白狗向著我哧吭了幾下鼻子。
自己平時回來的極少,連村里的人都不能認出一半來,但這狗們卻像知曉我是這村里出生的人一樣,一點兒也不生分,一點兒也不戒備。村子怎么是這般樣子?我疑惑著進了老家的小院。父親正倚在門框上吸著煙,臉上漾著安詳。見我進院子,他急忙走過來,笑著說,“乖乖兒,你怎么回來了?也不言語一聲。”
其實,父親是知道我回來給母親冬祭的,但他還是有些意外,這意外多半是由驚喜而生的。陪父親抽了支煙,我倆就蹲在院子里開始“花錢”。在這里,給親人燒紙不叫燒紙,而叫送錢。既然是送錢,就得用一佰元的紙幣在黃裱紙上,一下子一下子地打好,然后再把紙花成扇形,才能到墳地里燒。我和父親一邊“花錢”,一邊聊著。
“小的時候,村子里人歡馬叫的。這咋霜打的一樣,無聲無息了呢?”
“打工的打工,進城的進城。村里就剩這些老弱病殘和上學的孩子。”父親嘆口氣,又接著說,“這日月過的,真想不到!你看看咱村里,墻倒屋塌的,像又回到解放前了。真是越過越沒勁。”
我自清明那次回來后,一直沒有回村。這中間,父親在城里我們哥弟幾個那兒住了幾次,但總也不到兩個月。父親八十三了,他說一輩子在鄉里的小院住,慣了,住在城里像坐牢,憋屈死人。回來就回來吧,人與人是不一樣的,你覺得城里好,別人卻把它當成牢籠。反正現在也方便,時時都能打電話的。見父親對他的鄉村十分的不滿意,我就找著話題兒寬他的心。我蹲得有些不舒服了,父親就讓我起來坐著,他一個人在花地上的紙錢。
紙錢花好了。父親拾起地上的那張佰元票子,正要往上衣袋里裝,卻突然像想起了什么,隨機手就停在空中。他要干什么呢?我猜測著。這時,父親又從衣袋里掏出一塊佰元的票子,加上剛才那張,正好兩佰元。他看著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說,“給,這是羔子家退回來的。人家說你不回來吃大席,只收兩佰!”
羔子住在村西頭,比我大兩歲,我倆從一年級都在一個班里上學。
應該說,我倆小時候關系是相當好的,但后來我考上了大學,他窩在了村里,我們的隔膜就一天一天地長厚了,以至偶爾見面竟也很生分;像其他人之間一樣,遞支煙,笑一下,寒暄幾句,他便匆匆的離開。
兩個月前,就是快要過中秋節那幾天,父親突然打來電話說,“羔子從馬鞍山運回來了,赤腳光蹄的。你可回來燒張紙。”我舉著電話沒吱聲,心里算了一下,他才四十五歲呢,怎么說走就走了啊。我的心像被針扎的一樣,一陣一陣地疼,他畢竟只比我大兩歲呢。我本來是想第二天回來的,但夜里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最后還是決定讓四弟回村替我把花圈送上,把禮送上。因為,我真的不想看到羔子從手術臺上背回來的樣子。
我吐了口煙,望著父親說,“怎么又退了兩佰的禮呢?”父親表情平靜的說,“這是規矩,往禮不吃席的,退一半回去。”這時,父親把錢遞給我。我擺著手,心想父親怎么這會兒也給我客氣起來了。父親分明是看透了我的心,就笑著說,“給死人往禮的錢,我不能要,不吉利!”我笑了一下,連忙接了過來。
父親也起了身,他用胳膊夾著打好的紙錢,我拎著鞭炮,兩個人便走出小院門。這時,太陽突然從云彩里探出頭來,透過微風下稀疏的樹葉照下來,地上便斑駁陸離地晃動。
父親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們要出村到祖墳地里去。這樣的時刻,多少有幾分肅穆,我們爺倆一時沒有了話,任地上的樹葉在腳下沙沙地響。
到了村口,我突然被一種聲音驚住:這是古琴聲。
莫不是三弄叔又在撫琴?我向琴聲飛出的小院望了一眼,便確認這就是三弄叔的小院,殘垣斷壁上衰草搖曳,唯有那株帶刺的仙人掌,從墻頂蓬勃著向下蔓延著。于是,我立住了腳,這琴聲久違了二十多年啊。
這時,低婉深沉的琴聲宕開一幅與其說是雪夜,倒不如說是霜晨的畫卷:蒼茫大地,萬木凋零,唯有梅花鐵骨錚錚、迎寒傲立;高聲滑過,一股清新寒冷的帶著初升朝陽氣息的山風,伴著輕盈虛飄的琴音,撲面而來;琴聲漸緩,如幽溪穿月,讓我一下子進入了恬靜、安詳、遠離凡塵的境界;突然,高音又起,沉渾穿透,猶如破空而來的天籟,直入我心。

陳紅旗作品-《洗頭》 120×90cm 2006
這樣的時刻,這樣靜謐的鄉村能聽到這樣的琴聲,我真的要醉了。
這時,父親喊我了。我猶豫一會,還是回望了一下彌漫著琴聲的小院,向父親走去。
“三弄叔這琴聲,真是太美了。窩在鄉里一輩子,真虧!”
“虧?他作了一輩子呢。老天能讓他安生地走,就算對得起他了。”父親不以為然的話里,似乎還夾帶著更為復雜的嘆息。
“我覺得他挺好的啊,一輩子能文能武能伸能縮的。”我不解地說。
“你知道個啥?人在作,天在看。唉,他呀,開始遭報應了啊!”父親又嘆了口氣。
我真的不解,父親怎么會對三弄叔這個態度呢。他們是一個親爺的堂兄,只比父親小七八歲,今年也應該七十四五歲了吧。在我的印象中,三弄叔年輕時英英武武的,當過大隊的治保主任,也當過大隊的民兵營長。每次,只要在村口聽到他高脆亮堂的咳嗽聲,我就知道他準是又從大隊部開會回來了。于是,我心里便緊張得嘭嘭直跳,因為,晚上他肯定要給全村子里人開會了。我們孩子們,便有了熱鬧,可以圍在大人四周,嘁嘁喳喳地瘋來瘋去。
這個時候,馬燈下的三弄叔,總喜歡揮著手,像電影里的一個人,聲音很高地說著什么。但現在的三弄叔,又是個什么樣子呢?還是三年前那次回來,我見了他一次。那天,他正好從窯場回村子,就碰到了一起。記得,我還遞給他一支煙,給他聊了幾句。他說,他在幾十里外的地方給人家看窯場,身子骨還可以,自掙自吃過日月。
但那天,我突然覺得三弄叔以前的豪氣跑得無影無蹤了,人像被抽去氣的皮球,軟塌塌的,又像一只霜打過的老茄子。這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
想到這些,我也不由得生嘆。
這時,父親又開口了,“人啊,雖說是吃土還土,可陽世上走這一遭可不能錯了步,一步錯步步錯,報應就會找上門的。”
聽著父親這話,我覺得在父親的心里肯定是對三弄叔是有意見的。或許,三弄叔在父親心里是有著不可饒恕的過錯的。不然,八十幾歲的父親不會突然是這個樣子。于是,我便想知道,到底在三弄叔身上發生過什么。
“爹,你咋老說報應呢。有些事兒,也許不像你想的那樣呢。”
父親迎著微風向前走,并不回頭看我,而是說,“抬頭三尺有神明啊。羔子不也一樣嗎。人家都老老實實地出去打工,他卻帶著閨女放鷹,這不,閨女被人打死了,他也得了惡病,說走就走了。這不是報應,是啥!”
父親突然把話扯到了羔子身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再說三弄叔的事了。
可是,三弄叔的幾十年前的事兒,卻從我的腦里子浮現出來,越來越清晰,就像正在發生著的一樣。
那年臘月,冰琉璃掛滿了屋檐,我整天縮著頭、兩手插在袖筒里、弓著腰、不停地跺腳,天實在太冷。清鼻涕也沒完沒了的往外淌,我根本不想理會它,就抱著胳膊用兩個袖頭擦,兩只袖頭就明晃晃地泛著青光。那天晌午,我剛從學校回村,就聽到三弄叔那高脆亮堂的咳嗽聲,我一下子興奮極了:又要出大事啊!可不是嗎,早上一到教室,老師就鐵青著臉讓我們掏出語文書,把第十頁十一頁撕了交上去。這篇課文是已經學過的了,里面有一個叫鄧小平的人說的什么話。
當天晚上,三弄叔果真又把村里的大人們弄到喂牲口的牛屋里開會。屋子中間的火堆冒著嗆人的煙,人們卻不敢大聲咳嗽,實在嗆得不行,就在肚子里咳嗽幾聲,整個會場不時傳來吭吭哧哧的咳嗽聲。三弄叔舉著報紙在念,我分明聽到是“反擊什么風”。我在門外面,挨不到火堆里的一點熱氣,冷得有些抖。就在心里罵,是該反風了,天都他媽的想人凍死人了,還要什么風呢。
過的有三四天吧,那是個下午,村子里突然響起了銅鑼聲。這個時候,我好像正在掏麻雀窩,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便把兩枚光禿禿的麻雀蛋又放進墻縫里,從梯子上跳下來,朝著銅鑼的聲音飛奔而去。
銅鑼聲是從打麥的場里傳過來的。我跑過去時,大人們已經將麥場圍成了圓圈。我弓著腰,從大人的襠間擠進去,才看到里面的情景:一輛板車上裝著四根水桶一樣粗的木頭,三弄叔兩手掐腰,身后是兩個褂子外面扎著寬腰帶、背著長槍的民兵,板車前站著一個穿單衣的年輕人,脖子上掛著一個紙牌子,牌子上用墨汁寫著“地主小偷汪國慶”,汪國慶三個字個還打著血紅的×。
這時,三弄叔突然厲聲喝道,“這木頭是你偷的!?”
“是。”
“是你一個人偷的嗎?”
“是。”
“不老實!你一個人能裝上去?”
“能。”
“卸下來!再裝上去!”三弄叔的聲音像從地底下發出來的。
于是,汪國慶開始卸板車上的木頭。他用腿頂著板車框,弓下腰,用肩先頂著根木頭,一咬牙,用力向上便把木頭杠起來,腿離開車框,再一用勁,就把木頭擱在地上。這時,他臉上的汗,便淌下來。接著,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當第四根木頭擱在地上的時候,他蹲在地上,單衫已經被汗透,貼在背上,放著光。
這時,麥場上響起來高呼聲,“打倒地主小偷汪國慶!”有幾個婦女雖然喊著,但臉上卻寫著可憐兮兮的痛。
汪國慶在人們的吶喊聲中,站起來,低著頭,呼呼地喘著氣。
人們喊得都累了,聲音便漸漸小起來。這時,三弄叔開口了,“裝上去!”
“嗯。”
卸下來容易,裝上去難。但汪國慶畢竟是有把力氣的,那時他也就十八九歲吧。按說,正是有力氣的時候。
大概有一個多小時,汪國慶終于把四根木頭又裝上去了。我當時蹲在地上,并沒看清他是如何裝上去的。但有一點,我是看清了,當四根木頭裝上去的時候,我分明看到汪國慶從嘴里吐出了一口紅痰。
三弄叔也看到了,因為我倆的目光是在那塊紅痰上碰在一起的。于是,他就舉起手,帶著頭喊道,“打倒地主小偷!反擊右傾翻案風!”麥場里的人們又跟著喊起來。
喊聲停了。三弄叔又說,“走!到張樓村去!”
汪國慶走到板車的兩個把之間,掛上車攀繩,把板車按平,吃力地拉動了車子。
一路上,我都在回憶三十多年前的事兒。這回憶當然是由三弄叔引起的。關于三弄叔的事兒,我見到的我聽到的也真不少。粉碎了“四人幫”,那年我還在上小學。就是在那年冬天,三弄叔突然被人用繩五花大綁著,從村子里押走了。大概有一年多時間,他才回到村子。后來聽說,這事還是跟汪國慶有關,因為他在“汪國慶”三個字上打了血紅的×,差點成反革命了。這之后,三弄叔就不再是大隊干部,又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莊稼人。
我與父親到了祖墳地的時候,多少還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幾十個墳頭上,都蓋著一層干草,凄涼陰冷。在我的印象里,祖墳地還是清明時的樣子,紫色的小花迤邐地開著,青色的雜草,像綠色的花環一樣,芬芳四溢在一座座墳墓四周。當真是到了寒日,連我這美麗的記憶也都被這時令,一掃而去了。
我燃放了鞭炮,父親先給太爺,再給爺爺燒了火紙,然后才開始給母親燒。我給母親自然燒得多,而且還燒了幾打冥幣。對死人也是有親疏的,這就是人之常情。母親墳前的火紙伴著飛起的灰片飄向空中,父親便說,“給每個墳頭都燒幾張吧。”

陳紅旗作品-《吼叫》 160×150cm 2006
我與父親把剩下的黃裱紙點著了,快步走著,分別在每一座墳頭前丟下幾張。整個墳地,便煙霧繚繞起來。
煙霧慢慢散盡。我與父親又站在那里,吸了支煙,才離開墳地。該是吃晌飯的時間了。
走出地頭,父親突然停住。他用手指著右邊地里的那片墳頭,聲音很低地說,“那是老汪家的墳地。走的走,死的死,十來年沒人來上墳了。黃土不光吃人,也快把墳吃完了!”
我抬眼望去,那邊幾座墳確是算不上墳了,也就尺把高幾個土堆。我知道,這是汪國慶家的。汪家曾是富裕人家,解放前是有幾百畝土地的,從祖上都會制琴和彈琴。聽說,三弄叔七歲的時候就被送到汪家學制琴和彈琴。這樣說來,他叫汪國慶的父親應該是叫過師父的,他與汪國慶也是曾經十分親近的。
這時,我又想起先前三弄叔押著汪國慶游街的事來。
于是,我便問父親,“三弄叔真跟過汪家?”
父親對我的話有些詫異,扭著頭說,“這還能假。七歲去的,在人家一呆就是八年,解放了才回的。”
父親說著這話,語氣里流露出對三弄叔的不滿來。“忘本啊。國慶那孩子要不是三弄,能走得那么早嗎。”這時,我也想起汪國慶的死來。那次游街之后,他就得了吐血病,兩年多吧,他就不聲不響的歿了。
想到這些,我的心里不是個滋味。平日里沒往深處里想,現在想來,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村子里,竟有這么多恩恩怨怨,說不清道不明的事呢。一路上,我便不想再說什么。父親也不想再說什么,他依然在前面走著。他雖然八十三了,可走起路來,還咚咚地響。
進了村,沒走多遠,又到三弄叔那個小院前。
這時,琴聲還沒有停。我便又站住。父親知道我還是被這琴聲勾著,就沒再說什么,只顧自己朝前走去。于是,我便轉向三弄叔的小院。
琴聲越來越清晰。我站在院門口,不想驚動這琴聲。
我知道,這是古曲《梅花引》。我還知道,這琴聲已經進入第二部分:旋律急促剛健,節奏大起大落,跌宕多姿;琴聲散、泛、按三種音色不斷變化,時而剛勁渾厚,時而圓潤細膩,時而急徐清秀、悠長飄逸。我的眼前分明看到,一株紅梅于風雪中昂首挺立、臨風搖曳,錚錚鐵骨,冷香四溢,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了。
過去,應該是二十多年前是聽到三弄叔撫琴的。但那時是不懂琴聲的,更體會不到他竟有這般琴藝。于是,我對三弄叔便有一種敬佩的感覺來。
這時,琴聲進入了最后一章。寂靜的琴聲于喧囂之中,趨緩婉轉,裊裊回旋,欲罷不能,恍惚迷離無定,神秘虛無。我不禁想起“三弄魂消七弦琴絕,西窗月冷香如故,千回夢斷一闋,曲終濁酒更殘韻未休”這句話來。
我正沉浸在遐想之中。突然,一個高音顫過,琴聲戛然而止。
我醒了過來,疾步走進院里。只見三弄叔正坐在堂屋的當門,兩手撫琴,喘著粗氣。
見我進來,三弄叔并沒有站起來。看得出,他的身體太虛弱了,已經無力站起。我按著他的手勢,在東邊的條凳上坐下。掏出一支煙,遞過去,并給他點上。三弄叔吸了口煙,身體好像緩過來一點兒勁,便說,“今兒個回來的?”
“嗯。”
“該給你娘送寒衣了。”
“嗯!”我一邊應著,一邊看三弄叔面前的那架琴。
這是一架仲尼琴。琴體的腰部和頭部有兩個凹進的線條,通體沒有任何修飾,簡捷、流暢、含蓄、大方、內斂。琴面是梧桐老木,琴底應是古梓木,灰胎生漆使琴從里到外透出蒼松脆滑、拙樸古雅來。
看著這琴,我便問,“叔,琴是你斫的?”
“嗯。”
“有這手藝,咋不制幾架賣呢。城里流行著呢。”我說。
“唉,琴有命。降不住她了。你看,弦都斷了。”
“聽爹說,你的身體也不好?”我想起父親說過的話。
“這一世作夠了。肝子壞了,心也快死了。”三弄叔平靜地說。
三弄叔對我的到來,無驚無喜。話也咸一句,淡一句的。我知道,我與他之間不可能再有什么話可說了。于是,我站身子,說,“叔,我走了。你多保重啊!”
“走吧!我也累了。”
我走出屋門的時間,三弄叔是想站起來送一送的。可他最終還是沒有站起來。當年那個英英武武高聲大氣的人兒,怎么會是這個樣子。日月真是吃人呢,一天一天的吃,吃得你毫無戒備。
我在心里嘆著氣,離開了三弄叔的小院。
殘垣斷壁上衰草搖曳,唯有那叢帶刺的仙人掌,從墻頂蓬勃地向下蔓延。
晌午的陽光下,小院依舊溫馨地慵懶著。
回城半個月后,父親打來電話,話語平靜地說:三弄,跳塘死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他走的原因應該是從幾個月前他家的那場變故吧。那是一個滿眼翠綠的夏天,三弄叔唯一的兒子突然被抬回了村子,他是被城里的汽車軋了,軋得鼻子眼都分不清了。一個月后,三弄叔也病倒了。又過半年,三弄叔的兒媳婦帶著兒子也走了,走得無聲無息,沒影沒蹤的。三弄叔一個紅紅火火的大家庭,說散就散了,散得雨驟風停,無根無由的。
三弄叔出殯那天,我趕回了村子里。他的喪事辦得很潦草,這也是自然的事,因為他兒子死了,媳婦已經走了,家里一個人也沒有了。送走他的當天晚上,我跟父親睡了一夜。快到天亮時,父親吸著煙說,“他不虧,為了做琴的那幾根木頭,硬是把國慶這孩子的命糟踏了。”
難道真是為了得到那幾根做琴的古木,把國慶污為小偷的嗎?這是我從沒有想過的,現在我也不全信。興許,三弄叔并非單單是有這個私心,這里面可能還有什么隱衷呢。
離開村子的時候,我看到三弄叔的新墳就矗在我們那片祖墳里,若隱若現。明年的這個時候,新墳就變成舊土了。寒日那天,我也會給他燒一打紙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