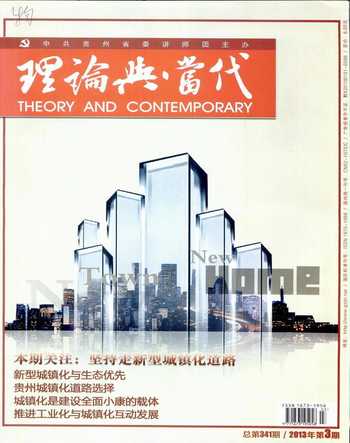散文集《疏影橫斜》賞析
涂萬作
“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王安石的詠梅詩,不經意地觸動了我讀散文集《疏影橫斜》時的心境,一時間暗香徐徐,情緒牽人。
我雖無緣感受那樣的課堂氛圍,但《疏影橫斜》卻為我展示了另一片瑰麗的文學天地。我是懷著學習與欣賞的心態閱讀這部集子的,而回饋我的不僅是文字和意境的唯美,還有那一腔純粹與真摯的情感。《疏影橫斜》共分四章,即“浮山夢影”、“天涯萍跡”、“心湖漣漪”、“夜郎留蹤”。每一章、每一篇都凝結著作者半生的行走體驗與心靈感悟,一翻開它們便不忍放下。
集子的第一章《浮山夢影》講述的是曾經的歲月,那一篇篇美文就如同一支支久遠的童謠,“共鳴”著人的懷舊情愫。我一直以為,懷舊是人的天性,是人生最美麗的懷想和追憶。而文學的懷舊,也許正是用來與流逝的時間抗爭的。因而,它不是簡單的昨日重現,而是經過漫長的時光過濾之后,所留下的那些最讓人心動的往事片段。不管過去的歲月如何艱苦,境況如何不堪,依然免不了要對那個時期經歷的人與事記憶猶新。正如淑媛老師所言:“歲月就像一汪靜靜的水,水底沉落著我殘破的夢。”
每個人心中都有著屬于自己的懷舊空間,都有讓自己充滿遐想的往事。那些往事就像窖藏的老酒,時間愈久,便愈發醇厚,愈發香濃,愈發讓人經久回味。淑媛老師無疑是一個素稔于文學懷舊的作者,她幾乎用了一個章節來講述那些沉淀的往事,如《沉落在水底的夢》、《路》、《老屋》、《冬夜記憶》、《浮山年俗》等。《路》中有這樣一段描寫:“鄉路彎彎,那里系著父母親的目光,留著兄長的腳印,灑有姐姐的淚水與汗水,承載著子侄們的希望;鄉路彎彎,牽著我對鄉土熱切的懷想,對故園深情的依戀。縱是山水相隔千里萬里,神魂兒卻總來來往往在這故鄉彎彎的鄉路上。”
這樣的感觸相信很多人都有,我也常常如此。哪怕是一條小河,一片落葉,一彎新月,都會喚醒我兒時的回憶,比如某一年的某一天,梧桐樹下的嬉戲:某一年的某一天,油紙傘下的倩影;某一年的某一天,落在手臂上的蝴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浮山年俗》一文,作者以其細膩的筆觸,將地處湘北浮山腳下的故鄉民俗盡情展示,讓讀者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一方水土”。浮山,即太浮山,武陵山支脈。陶淵明《桃花源記》所描繪的世外桃源就出自武陵,那是一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的詩情畫意所在。作者將著墨的重點放在“澆蠟燭”、“做粑粑”、“辦年貨”、“吃年飯”之類的純民俗風情上,寫出了中華民族文明傳承大背景下獨特的武陵年俗文化,看似十分遙遠,卻又近在咫尺。
淑媛老師來自農村,泥土的氣息與草木的清芬,氤氳著她的故鄉情懷,她將筆觸停泊在亙古的時令點上,唱出婉轉的旋律,就像《驚蟄》里寫的:“城里人不懂驚蟄,驚蟄只屬于鄉村,屬于鄉村的山水田疇,屬于鄉村的赤腳農夫和村婦,屬于山野間牛背上的牧童。男人催耕,女人播種,娃娃得意地騎在牛背上,吹響了牧笛,山村的驚蟄驚出了濃濃的春天的詩意……”如此生動的畫面感,分明是一幅水墨《鄉村春意圖》。
人常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如果不是有心人,縱是行了萬里路,又能收獲幾何?淑媛老師無疑是個有心人,第二章《天涯萍跡》即可見證。她在扉頁中寫道:“說是命帶‘驛馬,就將走遍天涯,但又如何真能天涯走遍。偶能踏訪名勝,游歷山水,留下一些美麗的記憶,便是對人生的裝點了。”
作者正是以“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理念來裝點她的記憶的。她曾在湘西鳳凰品讀沈從文,在古城麗江采擷靈韻,還在古羅馬斗獸場觸摸遠去的歷史,在巴黎感受盧浮宮璀璨的文明……每一次游歷過后,她都要讓心與文字膠著纏綿,然后欽乃出一篇篇游記散文。她的文字從容而靈動,就像她游麗江時寫的那樣:“麗江的詩意與古韻浸潤在四方街古老的青石小巷里,流動在那隨處可見的碧流清溪中,搖曳在家家戶戶門口窗前柔柔的柳條上,游動在那一座座或精巧別致,或粗糲樸拙的小橋下,蘊含在柔婉深沉的納西古樂中(見《美麗麗江》)。”而對于邊城鳳凰的理解更是別致:“鳳凰,這是一個只有在寧靜淡泊中細細品味才能讀懂的小城,這個小城拒絕張揚與矯飾,拒絕浮躁與喧囂,寧靜、淡定、從容,才是沈從文的鳳凰的本色(見《沈從文的鳳凰》)。”即便面對古羅馬斗獸場,也能表現出哲人式的解讀:“在熱切的盼望中與斗獸場灰灰的、冷冷的門洞窗洞相對時,古與今,歷史與現實,就在瞬間碰撞對接,古今之思,歲月懷想便悠然而來,讓人流連、徘徊……”(見《古羅馬斗獸場》)
當讀到《心湖漣漪》一章時,我漸漸被一種靜態的素雅所吸引。那是一種籬外幽蘭,暗香淺淡的含蓄之美。作者說:“每當日影西斜,或者月上竹梢,后窗窗欞和窗下書桌上就灑滿斑斑駁駁的竹影,神妙而靈動。有的夜晚,我會關了燈,靜坐窗前,仿佛是在與竹進行細語輕聲的傾談。”(見《竹窗隨想》)這樣的心境在她的《關于月亮》中亦出現過:“月亮是冷冷的,她是一個經歷了滄桑與磨難的失意女子,寂寞而溫婉,對世事,對自身,都只能是圓缺陰晴,聽其自然。任你浮躁喧囂,我自清靜無欲,冰清玉潔,自持自守,茫茫蒼穹獨寂寥……”
作者“心的漣漪”就這樣緩緩地蕩漾開來,在“蓮葉何田田”風景里徜徉,于是,一篇名為《荷》的美文便從她的筆下優雅現身。這是一篇體現淑媛老師婉約風格的傾情之作,出污泥而不染的花中君子,在她的引領下走過四季。情與景的交融,榮與枯的對話,為讀者帶來的是美的享受與心的撫慰。不妨采擷幾段——
“又是一日日春風,一夜夜春雨,荷葉出離水面往高里伸展,順風舉起肥碩闊大的葉盤。于是滿塘綠色的圓圓的荷傘撐起來了。最喜那輕雨后的荷盤滾動的水珠,有如翡翠盤中滾動的水晶珠,清亮圓潤,玲瓏剔透。”
“陽光,水鄉,荷塘。池水清淺,秋草黃。已是殘荷聽雨的季節,眼前一片零落蕭索。殘破的荷葉,折損的荷莖,褪去了翡翠綠的荷塘一片灰青……”
“荷,就這樣,走過四季,走過春的明麗嫵媚,走過夏的妖嬈華麗,走過秋的成熟蕭索,走過冬的冷落深沉,猶如人走過一生。”
一切景語皆陪語,散文的美在于文字美、意境美、思想美與情感的交相輝映。對此,集子的第四章《夜郎留蹤》便做了這樣的回答。
貴州,作者的第二故鄉,不僅留住了她的青春歲月和她鐘愛的事業,還有留住了她對文學的繾綣深情。她說:“自從踏上你的土地,就把一生的歲月交給了你,轉眼已是四十余年。不是故鄉,你卻給了我故鄉般的滋養:雖是異鄉,我對你的情感亦如我對故土家園。”
淑媛老師是用她的散文來詮釋她發自內心的寄語的,四十多篇謳歌多彩貴州、贊美神秘夜郎的文章,就像四十多個跳動的音符,所流淌出的是一串串優美、經久、動人的旋律。當細讀《納蟬意象》、《品讀獨山》、《用生命點亮花燈的人們》、《探訪長角苗》等篇目時,都會被作者帶到那詩畫般的意境里。
淑媛老師文筆優美、細膩、生動,一如她的優雅氣質跟謙和品格。就像她在隨筆《梅花引》中寫的那樣:“縱然是一棵楊柳,一竿修竹,哪怕是一叢蘆葦,只要是在月光下,在水邊,其實都是可以造出‘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境的吧?”
其實,淑媛老師就是一枝梅,只是靜靜地、婉約地開著,一任暗香襲襲。
(作者單位:貴陽日報)
責任編輯:郭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