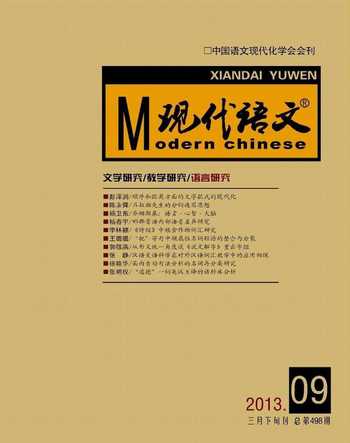“施罛濊濊”與“施罟濊濊”關系考
摘 要:“施罛濊濊”出自《詩·衛風·碩人》,在《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中的《目部》和《網部》分別引《詩經》“施罛濊濊”,《水部》引《詩經》作“施罟”,《大部》引《詩經》作“施罟泧泧”。本文將通過“罛”與“罟”,“泧”“”與“濊”的·音義考證來說明“施罟泧泧”“施罟”和“施罛濊濊”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訓詁 罟 濊
“施罟”所表意義見于《說文·水部》:“,礙流也。從水,薉聲。《詩》:‘施罟。”[1](P229)在《說文·網部》有:“罛,魚罟也。從網,瓜聲。《詩》:‘施罛濊濊。”[1](P157)可見兩者書寫存在差異。同時引此《詩》表讀音的有《說文·大部》:“奯,空大也。從大,歲聲。讀若《詩》‘施罟泧泧”[1](P213)《說文·目部》:“眓,視高貌。從目,戉聲。讀若《詩》曰‘施罛濊濊。”[4](P71)且兩者書寫形式也不同。
考察今本《詩經》,既無“施罟”,也無“施罟泧泧”,只有“施罛濊濊”。《詩·衛風·碩人》中有“施罛濊濊,鳣鮪發發。”本文將通過“罛”與“罟”,“濊”“”與“泧”的音義考證來說明“施罛濊濊”“施罟”與“施罟泧泧”之間的關系。
一 、“罟”與“罛”音義關系考
(一)語義方面
1.對于“罟”的解釋
《說文·網部》:“罟,網也。從網,古聲。”[1](P157)
《說文解字注》:“罟,網也。《小雅·小明》傳曰:‘罟,網也。按:不言魚網者。《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田以漁。是網罟皆非專施于漁也。罟實魚網,而鳥獸亦用之。故下文有鳥罟,兔罟。”[2](P355)
《說文解字約注》:“舜徽按:罟罛雙聲,受義同原,皆大網也。凡牙聲字皆有大義。罟字引申,又為凡網之稱。”[3](P56)
《說文解字系傳》:“臣鍇曰:網之總名也。”[4](P157)
《說文句讀》:“足見罟其總名,而羅罛等皆其小號也。”[5](P1019)
《廣雅疏證》:“網謂之罟,此網魚及鳥獸之通名。”[6](P224)
《宋本玉篇》:“罟,魚網也。”[7](P298)
【按】《說文》認為“罟”為“網”之義,《說文解字注》引《易》認為“網罟不專用于漁業”,并且以后文的“鳥罟和兔罟”為證。王筠《說文句讀》指出“罟為網的總名”,而“羅與罛”都指的是網的一種。王念孫《廣雅疏證》認為“捕魚和鳥獸的網都可以稱為罟”。可見,“罟”的本義為“網的總稱”,但也可以單指“魚網”。
2.對于“罛”的解釋:
《說文·網部》:“罛,魚罟也。從網,瓜聲。《詩》曰:‘施罛濊濊。”[1](P157)
《說文解字注》:“罛,魚罟也。《衛風·碩人》曰:‘施罛濊濊。《釋器》《毛傳》皆曰:‘罛,魚罟。”[2](P355)
《說文解字約注》:“戴侗曰:‘罛,蓋急流取魚之網。”[3](P55)
《說文解字系傳》:“臣鍇按《爾雅》曰:魚罟謂之罛。注曰:網最大者也。”[4](P156)
《爾雅義疏》:“《詩·碩人·正義》引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8](P671)
【按】《說文》《說文解字注》《爾雅·釋器》和《毛傳》都認為“罛”為“魚網”義。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認為:“罟和罛雙聲,受義同原,都是大網的意思。”再加之郭璞的注認為“最大的網就是罛”。可知“罟”與“罛”雙聲同源,語義有相通之處,即都有“大網”之義。從以上材料可知“罛”的本義為“魚網”,即“捕魚的器具”,但也有“大網”之義。
(二)語音方面
《鉅宋廣韻》:“罟,公戶切。網罟。”[9](P179)
《鉅宋廣韻》:“罛,古胡切。魚罟。”[9](P44)
【按】“罟”與“罛”的反切上字“公”與“古”同屬“見”母,反切下字“戶”與“胡”在上古同屬“魚”韻,可見“罟”與“罛”讀音相同。據《爾雅義疏》“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8](P671)與《說文句讀》“足見罟其總名,而羅罛等皆其小號也。”可知 “罟”與“罛”的區別在于: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罛”則為魚網之專稱。“罟”為網之大名,不專指漁,“罛”乃魚網之主稱。故“罟”與“罛”對言有別,散言則可通,故在《說文》中引《詩經》中的“罟”與“罛”可以互用。《說文解字引經考》有:“《淮南·原道篇》高誘注此《詩》‘施罟濊濊作‘罟。《說山篇》高注,《呂氏春秋·上農篇》高注引此《詩》又作‘罛。《淮南子·說山訓》:‘好魚者先具罟與罛。”[10](P444)由此可知,漁業上所用的網“罟”與“罛”在文獻中可互用。
二 、“濊”“奯”“泧”與“眓”關系考
(一)語義方面
《說文·水部》:“泧,瀎泧也。從水,戉聲。讀若椒樧之樧。”[1](P235)
《說文·大部》:“奯,空大也。從大,歲聲。讀若《詩》:‘施罟泧泧。”[1](P213)
《說文·目部》:“眓,視高貌。從目,戉聲。讀若《詩》曰:‘施罛濊濊。”[1](P71)
《說文·水部》:“濊,水多貌。從水,歲聲。”[1](P238)
【按】“泧”的本義為“抹殺”,“奯”的本義是“孔竅大”,據王筠《說文句讀》:“空音孔。謂孔竅大也。”[5](P1413)“眓”的本義為“高視的樣子”,“濊”的本義為“水多的樣子”。“奯”與其表讀音的“泧”字在意義上無關,同樣“眓”與其表讀音的“濊”字在意義上也無相關性,故可知這四個字在意義上沒有共同之處。
(二)語音方面
《鉅宋廣韻》:“濊,呼括切。水聲。”[9](P395)
《鉅宋廣韻》:“泧,呼括切。瀎泧。”[9](P395)
《鉅宋廣韻》:“眓,呼括切。《說文》曰:視高貌。”[9](P395)
《鉅宋廣韻》:“奯,呼括切。大開目也。”[10](P395)
【按】“濊”“泧”“奯”“眓”四字音同,在上古同屬于月部,曉紐。但其意義都不相同,可以用來假借。陸宗達在《說文解字通論》中講到用“讀若”的方法去注音,在注音中有意識地闡明了文字的分化和用字的通假問題。在今本《詩經·衛風·碩人》中用的是“施罛濊濊”,故可知“泧”字在“施罟泧泧”中只是音近的假借字而不是本字。
三 、“濊”與“”考
(一)語義方面
1.對于“”的解釋
《說文·水部》:“,礙流也。從水,薉聲。《詩》云:‘施罟”[1](P229)
《說文解字約注》:“鈕樹玉曰:此字疑本是‘濊,后人加艸也。《詩·碩人》作‘濊。又《說文》‘罛下引《詩》‘施罛濊濊。‘眓讀若《詩》‘施罛濊濊亦并作‘濊。舜徽按:‘由后人既加艸于‘濊篆上,知有不安,復于部末補‘濊篆耳。許以‘礙流訓‘濊,謂礙流之聲濊濊也。” [3](P36)
2.對于“濊”的解釋:
《說文·水部》:“濊,水多貌。從水,歲聲。”[1](P238)
《說文解字注》:“濊,礙流也。有礙之流也。《韓詩》云流貌。與毛許一也。濊又訓多水貌。《司馬相如傳》:湛恩汪濊。從水,歲聲。各本篆作,云薉聲。今正。按:《釋文》不云《說文》作‘。證一。《玉篇》‘瀏‘濊二字相連,與《說文》同。‘濊下云:呼括切。水聲。又于衛外于二切。多水貌。不云有二字。證二。《廣韻》十三末:濊,水聲。‘上同。證三。《類篇》:濊,又呼括切。礙流也。引《詩》‘施罟濊濊。證四。是知妄人改礙流之字為‘,而別補‘濊篆于部末,云水多貌,呼會切。不知部末至‘澒‘萍等篆已竟。水多非其次也。今刪正。《詩》曰:施罟濊濊。罟當作罛。‘濊濊今本作‘。大繆。” [2](P547)
《說文解字約注》:“鈕樹玉曰:前‘字本當是‘濊。此訓水多,疑后人增。李注《文選·長笛賦》:‘濊引《說文》‘水多,疑后人因之增入。舜徽按:許書若果有此篆,敘此亦不當在部末也。” [3](P89)
【按】《說文解字注》中“濊”作“礙流也。”故“施罛濊濊”譯為“魚網投置水中礙流,而發出濊濊之聲。”《毛傳》曰:“濊,施之水中。”故有礙流也。但值得注意的是 “”與“濊”字在《說文》中都存在,且意義不同,而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據《釋文》《玉篇》《廣韻》《類篇》四證,將“”的意義移到“濊”上,并認為“濊濊”今本作“”是錯誤的。在《說文解字約注》中引鈕樹玉的話也認為“”字本當是“濊”,疑是后人多加的字。張舜徽也同意此看法,并認為按照《說文》體例“濊”字也不應放在部末。可見“濊”與“”之間的關系需做進一步考證。
(二)語音方面
《鉅宋廣韻》:“濊,呼括切。水聲。”[9](P395)
《鉅宋廣韻》:“,呼括切。水聲。”[9](P395)
《集韻》:“,呼括切。《說文》:礙流也。引《詩》‘施罟,‘或作‘濊。”[11](P690)
《類篇》:“濊,呼外切。《說文》:水多貌。又呼括切。礙流也。引《詩》:施罟濊濊。”[12](P413)
【按】在《類篇》“濊”下引《說文》“水多貌”為本義,而以“礙流”為另一義,引此《詩》作“濊濊”。“”下引《說文》“礙流也”為本義,引此《詩》作“”,可見《類篇》對于“濊”兼存兩說。但從《集韻》十三末“”下引《說文》云:“礙流也。《詩》曰:施罟,‘或作‘濊。”又《鉅宋廣韻》中“濊”和“”都“呼括切”可知二字皆從曉紐,同在月部,故音同,且意義都為“水聲”,故可通用互換。再從字形上可知“”從“薉”聲,在《說文·艸部》中“薉,蕪也。”[1](P23)“蕪,薉也。”[1](P23)“荒,蕪也。一曰艸掩地也。”[1](P23)可知“薉”的本義為“蕪穢”義。以“薉”得聲的“”字是形聲字,聲旁也可以表義,故可知“礙流”之義由“蕪穢”之義引申而來,未必是妄人所改。故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改“”為“濊”字,又刪除‘之本義而謂“妄人別補”。筆者認為此種做法不太合理,依據各本作“”字及上述分析,應保留其本來面目,如若疑為后人妄改,或謬誤者,可在注中說明,切不可隨意刪除,以使后人讀《說文》,可以尋其脈絡,窺其全豹,而不至于混淆。
綜上所述,通過以上考證可知在今本《詩·衛風·碩人》中的 “施罛濊濊”中的“罛”字應為本字,但由于“罛”與“罟”兩者音同且意義相近,故在文獻中可互用。而“”“濊濊”與“泧泧”為音近的假借字,但按照《廣韻》《集韻》及《類篇》可知“”與“濊濊”不僅讀音相同而且意義相近,故筆者認為“”與“濊濊”可以互換,但究其孰為本字,實難判斷,若以上述論證則可判斷“”為本字,但只是一些材料的證明,不能充分斷定。因此筆者認為這是異文現象,只有細心鑒別,才能擇善而從。很顯然,《說文》中的這一異文異義,不僅無助于解《詩》,反而增加了對《詩》理解的難度。由此可見,對待《說文》引《詩》中的異文異義,需要仔細審辨文意和比較同類用例,只有這樣才能判明是非,才可以使后世能夠找出其源流,而不至于難以判斷孰為本字,孰為假借。
注 釋:
[1]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M].洛陽:中州書畫出版社,1983.
[4]徐鍇.說文解字系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
[5]王筠.說文句讀[M].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1983.
[6]王念孫.廣雅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
[7]顧野王.宋本玉篇[M].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
[8]郝懿行.爾雅義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陳彭年.鉅宋廣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馬宗霍.說文解字引經考[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中華民國六十年.
[11]丁度.集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司馬光等.類篇[M].北京:中華書局,1984.
(王丹 寧夏銀川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