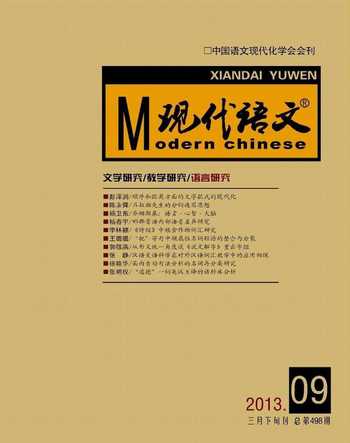論闡釋翻譯學的實踐維度
摘 要:闡釋翻譯學長期執著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一度被置于經驗主義的對立面,脫離語言解釋的實踐。筆者把語料庫語言學和闡釋翻譯理論相結合,在闡釋翻譯學研究中引入實踐維度概念,探尋解決闡釋翻譯的實踐路徑。在理論闡述之后,通過“道德”一詞英譯的語料庫分析,探討語料庫在闡釋翻譯學中的具體應用。闡釋翻譯學借助以語料庫形式積累的“體系化”經驗,通過譯者的主體選擇,使闡釋翻譯學擺脫單純的理論研究困境,從而建立可實際操作的開放理論體系。
關鍵詞:闡釋翻譯學 實踐維度 “道德” 語料庫
一、引言
闡釋學的詞源可追溯到希臘神話中眾神的信使赫耳墨斯(Hermes),從闡釋學后來所獲得的本體論解釋意義來看,翻譯和闡釋實為一體。翻譯可以理解為一種跨語言文化的傳通(communication),傳通涉及語內翻譯(解釋)、語際翻譯、符際翻譯(轉換),即雅各遜的翻譯三分法所涵蓋的符號轉換的每一方面。闡釋學翻譯理論研究經歷了輝煌后的挫折,究其原因,一方面與新的理論和研究范式的崛起有關,另一方面與其自身理論的發展不足密切相關。文獻回顧顯示,闡釋翻譯學至今仍然執著不放的焦點問題,基本上還是那些形而上的、純理論的思考。我國譯學界的闡釋翻譯學研究多從哲學闡釋學“理解的歷史性”“效果歷史”以及“視閾融合觀”出發展開研究(耿強,2006:39)。張德讓在評李河的《巴別塔的重建與解構》一書時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詮釋學研究在歷時線索上主要關注由施賴爾馬赫—狄爾泰—伽達默爾—利科等所代表的詮釋學傳統,在主題上主要關注對“理解”“解釋”觀念的一般認識論或本體論的討論。李河的著作突破了這個敘述格局,它根據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關于所謂“激進詮釋學”的研究,展開了一條由克爾凱戈爾—本雅明—海德格爾—福科—德魯茲—德里達等人構成的線索,提出以“居間存在”為基礎的語際翻譯解釋學(張德讓,2009:666)。然而,在筆者看來,李河所提出的“居間存在”雖然突破了結構與解構的二元對立,但并沒有跳出翻譯本身就是溝通這一傳統的闡釋學命題。張德讓(2010:66~72)本人提出的翻譯會通觀雖然結合中國古代的翻譯理論展開論述,但與李河的“居間存在”理論也是一脈相承的。
實際上,蔡新樂(2001:52~54)早在2001年就指出了通化翻譯對翻譯過程的“神圣化”的危險,這一努力可追溯到斯坦納在《巴列塔》一書中所闡述的通過翻譯重建通天塔的觀念。長期以來,闡釋翻譯學無法突破其自身,洪漢鼎在向迦達默爾要求翻譯其巨著《真理與方法》時遭遇的尷尬則反映了闡釋翻譯學被哲學本體化的事實。闡釋翻譯學不僅嚴重脫離翻譯實踐,在理論建設上也與其歷史上極其實用的解經學傳統以及當下翻譯實踐中常用的解釋方法嚴重脫節。闡釋翻譯學成為一種單純的本體論哲學思考,成為走不下神壇的理念,與翻譯實踐所建立的聯系大多是支離破碎的非必然聯系。
二、闡釋溝通下的理性與經驗
盡管闡釋學及闡釋翻譯研究大多聲稱源于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理論,然而對伽達默爾的繼承往往忽視了其闡釋學哲學中所包含的辯證法和實踐精神。事實上,辯證法和實踐精神又是密不可分的。伽達默爾指出:“(由于)理解與解釋的內在結合導致詮釋學問題里的第三個要素即應用(Applikation)與詮釋學不發生任何關系……這樣,我們似乎不得不超出浪漫主義詮釋學而向前邁出一步,我們不僅把理解和解釋,而且也把應用認為是一個統一的過程的組成要素。”(伽達默爾,2007:418)伽達默爾對于應用的闡述不僅充滿辯證認知,而且也是對實踐精神的弘揚。在接受杜特采訪時,伽達默爾詳盡地闡述了他所宣導的亞里斯多德“實踐”(Praxis)觀念的含義:
首先,人們必須清楚“實踐(Praxis)”一詞,這里不應予以狹隘的理解……我們所熟悉的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使“實踐”與對理論的“實踐性應用”相去弗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對理論的運用也屬于我們的實踐……它是一個整體,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實踐事務,我們所有的活動和行為,我們人類全體在這一世界的自我調整……(伽達默爾、杜特,2007:67~68)
基于伽達默爾對闡釋學所包含的辯證法和實踐精神的認識,闡釋學必然要關心闡釋的實踐維度。何衛國在《通向解釋學辯證法之途》一書中指出:“伽達默爾的解釋學辯證法強調實踐,強調參與,理解和解釋活動主要體現為一種實踐理性,而非理論理性。”(何衛國,2001:382)何衛國是國內較早關注到伽達默爾實踐理性思想的學者,我們把這種闡釋學的實踐理性稱為闡釋的實踐維度。這一概念把實踐和理論看成是闡釋過程中既相互區別又密不可分的至關重要的兩種維度。運用到闡釋翻譯學中,闡釋翻譯實踐得以納入闡釋學理論關注的視野,使得長期忽視的闡釋翻譯實踐可以上升到實踐理性去認識,實踐不再是單純的匠工,而是可以納入理論視野、可以被思辨和認識的翻譯行為和行動的綜合。闡釋翻譯過程、技巧、評價等實踐活動都可以納入實踐維度中來考察。
翻譯的闡釋實踐主要表現為譯者的闡釋翻譯經驗,其中可以條分縷析的是翻譯實踐中產生的實踐解釋方法。作為翻譯實踐的解釋方法一直游離于闡釋學的理論闡述之外,然而解釋本身是翻譯實踐的必然要求,是貫徹實踐理念的途徑,也是解決實踐問題的方法論。翻譯實踐的解釋方法是翻譯者藉以跨越文化障礙的手段和方式。闡釋實踐維度的提出使長期游離于闡釋學理論之外的經驗解釋方法得以被哲學闡釋學吸納,與此同時闡釋理論又得到了翻譯實踐的支撐,解釋方法和哲學解釋理論融為一體。
翻譯實踐維度概念的提出還突破了翻譯中的二元對立,使理論能夠自覺走入實踐本體去探討翻譯面對的種種問題,使行動研究成為可能,使資料分析能夠為最終的翻譯實踐服務,而不是為純粹的理論研究服務。翻譯行動研究反過來也進一步拓寬了翻譯的實踐維度,使主體的人(即譯者)和作者(即文本中的他者)之間形成對話,從而跨越時間、空間和文化的間隔,形成翻譯理解的通路。
三、實踐維度與“體系化”經驗
要在闡釋翻譯學中貫徹實踐維度的概念,必須解決理性與經驗長期對立這一哲學問題。把理性和經驗看成翻譯中的兩個維度既不等同于折中調和的整體觀,也不是飽受詬病的二元論。它本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針對的是闡釋翻譯理論研究中長期否定解釋實踐的現實問題,針對的是20世紀理論語言學研究中對身體(經驗)存在的否定的傾向。
在翻譯研究中,道格拉斯·魯濱遜(2006)的翻譯理論努力證明身體的在場,大膽為翻譯實踐張目,拓展了翻譯研究的思維空間。他一方面激烈抨擊西方語言科學研究中長期排斥身體經驗的歷史,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解構手段摧毀解決理性與經驗對立的可能性,因此未能就經驗進入理論視野提出可行性的實踐方法。實際上這也是其基于解構主義理論建構翻譯學所遭遇的未能突破的研究瓶頸。正如Anthony Pym在論述翻譯與哲學的關系時所擔心的那樣:
As formulated,the hermeneutic approach reflects aspects of the 20th century loss of certainty.Indeed,its tenets reappear in many contemporary approaches,certainly in Derrida (who started as a reader of Husserl)but also,perhaps paradoxically,in the move to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where positivistic conceptions of empirical science have nevertheless revealed the vast plurality of translatory practices.(Pym,2007:28)
由于闡釋學研究長期對理論的過度關注,其自身一度處于行動研究的對立面。因此要推動闡釋學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的結合,必須在二者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這不可能只是單純的理論研究,也不可能是單純的實踐研究,而應該是能夠真正使理論與實踐融通的一種東西,那就是“體系化”經驗。所謂“體系化”經驗是指對前人實踐經驗有組織地、系統地歸納和整理,并可以為后來者所用的直接經驗,不包括形諸文字的他人翻譯經驗的直接總結,而是指蘊含于翻譯實踐材料中、通過一定的組織加工方式可被使用者吸納的翻譯經驗。對“體系化”經驗的關注并不意味著放棄闡釋學的基本原則和闡釋實踐中的解釋方法,反而是為了更好地應用先前的翻譯經驗,更好地實踐翻譯的多元闡釋。“體系化”的闡釋經驗包括翻譯教科書中的例證、雙語詞典中的例句、翻譯手冊等紙媒資源,以電子媒介存在、可供軟件檢索使用的狹義語料庫資源以及以網絡形式存在并可以被搜索引擎檢索的廣義翻譯語料庫資源,這些都是闡釋翻譯實踐和研究的參考資料。
在定義了“體系化”經驗以后,我們需要探討譯者進入和利用“體系化”經驗的路徑。“體系化”經驗是對零散的、“個性化”經驗的歸納、總結和加工。傳統的非電子語料庫往往不具備方便(或者干脆不具備)檢索功能,資料的查找十分不便,雖然收錄于傳統紙媒詞典、教科書等的翻譯例證可以構成“體系化”的翻譯闡釋經驗供譯者參考,但由于這些例證的選取受到量的限制,有時候很難真實反映翻譯經驗的復雜性及其廣度和深度,再者由于例句被抽取以后無法有效鏈接回到整個譯文語境,造成譯者吸納翻譯經驗的困難。然而,隨著計算機與網絡技術的發展,翻譯經驗的“體系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翻譯經驗文本得到大量挖掘,內蘊于大量翻譯文本自身的翻譯經驗得以成為“體系化”的翻譯經驗,構成可供翻譯實踐和研究參考的現代語料庫資源。
現代語料庫,無論是狹義的雙語或多語平行語料庫、可被Concordances軟件讀取的單個或多個譯本的電子文件、分布于其他數據庫中的翻譯資源,還是在萬維網上可供搜索引擎檢索的網頁翻譯資源,都具有遠超傳統紙媒文本的資料檢索、對比、排序、篩選等功能,使“體系化”經驗集成和利用的途徑得以大大拓展,從而使現代語料庫成為匯集翻譯資源,架設翻譯溝通橋梁的工具。方便快捷的“體系化”經驗的建立使得譯者能夠較好地利用以往的翻譯經驗完成自己的翻譯工作,而且“體系化”經驗也被直接應用于機器翻譯的設計和輔助機器翻譯的開發利用中去。
現代語料庫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反映了翻譯研究中經驗主義的重新崛起。由于傳統語料收集的困難,傳統闡釋經驗文本具有強調主體性的“個性化”特征,其自身不具備(便捷的)檢索性,各經驗文本之間的聯系往往不夠緊密,經驗文本之間的串連難以為繼,因此闡釋經驗主體(譯者)對過去經驗的借鑒往往是在信息匱乏的情況下展開的,闡釋實踐往往容易走向為權威張目的道路,因此傳統的“個體”經驗闡釋學在翻譯理論和實踐研究中的應用飽受詬病,傳統闡釋翻譯學被指具有偏好經驗、忽視理性的不足。
基于現代語料庫的翻譯闡釋能容易地溝通翻譯的過去與未來,溝通中外翻譯經驗,溝通不同視域的經驗文本。作為居間調解者的譯者,在翻譯倫理規約下,通過對“體系化”經驗的自覺使用,使闡釋翻譯的實踐維度理念得以貫徹實行。關于語料庫在溝通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中的作用,梁茂成(2010:90~97)有很好的闡述:“我們一直強調翻譯溝通中外古今,翻譯自身的溝通同樣十分重要,語料庫恰恰滿足了溝通翻譯語料的作用,這是傳統語料(諸如紙媒詞典等)工具所不具備的優勢。”
然而,語料庫技術的發展并沒有最終解決一切問題,因為經驗的“體系化”并非是以單純理性代替主體經驗的實踐活動的過程,“體系化”的翻譯經驗是翻譯實踐緯度的一種要求和手段,它必須建立在主體的自覺介入和判斷的基礎之上,必須面對語料豐富所帶來的信息過剩問題。因此,語料庫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例如網絡詞典的興起所使用的某些新技術手段缺乏語言專家的指導,所產出的文本往往帶有隨意性和純粹資料化傾向,這樣反而傷害了語料庫的使用。再者,語料豐富所帶來的信息過剩問題,更加催生了對主體選擇的迫切要求。因此,在使用語料庫等新技術建設“體系化”經驗材料的過程中,必須同時保持闡釋學本體的解釋力,這樣才能應對人文科學研究走向完全資料化的偏頗。語料庫的使用絲毫不能降低譯者選擇的重要性,譯者選擇才是最終溝通理性和經驗的必由之路。
四、“道德”一詞英漢互譯的個案分析
對“道德”一詞英譯的個案分析主要關注的是翻譯闡釋實踐中解釋性方法應用的普遍性和譯者對“體系化”經驗吸收時主體選擇的重要性。首先,通過翻查金山詞霸軟件所收錄的《現代漢英綜合大詞典》,我們發現“道德”一詞的英語翻譯包括:
道德:morals;morality;ethics。
透過The Babel English-Chinese Parallel Corpus(http://corpus.nie.edu.sg/laohong/Babel.htm)檢索“道德”一詞的翻譯例證,歸納其翻譯的實踐方法,我們發現語料庫所包含的翻譯對應關系包括:
①道德(名詞):morals,morality and ethics;values and attitudes。
②道德(形容詞):moral,ethical。
③不道德:unethical,vices。
從上述列舉可以看出,“道德”一詞以及它的同義詞在翻譯處理中存在著復雜的情況。首先,“道德”一詞和英語中的“對等詞”存在著一對多的關系,有些翻譯采用了解釋性的方法,例如把“道德”翻譯成“values and attitudes”(見表1)。
再者,“道德”在漢語中的詞性處于未明確的狀態,這是漢語的語言特點所決定的,在英譯時必須考慮具體語境中的詞性問題(見表2)。
在漢語的機器標注中,“道德”被標注為名詞,然而由于其作定語的功能,翻譯成英語選擇了“moral”這個形容詞來對譯。最后,“道德”一詞的否定“不道德”在英譯時并非完全遵循拆字理解的方法,而且原文的形容詞通過此類轉換翻譯成了英語的名詞“vices”(見表3):
廈門大學盧偉教授開發的英漢雙語平行語料庫(http://www.luweixmu.com/ec-corpus/ logon.asp)為我們提供了“道德”一詞對應英語詞匯的更多例證。輸入“道德”一詞獲得的例句有126個,我們對其中涉及的非常規的英語對應詞匯或語境關系列表如下。
上述這些例證足以表明,雙語平行語料庫可以為翻譯闡釋提供豐富的語料例證,使得前人的翻譯成果能夠得到很好的借鑒,這樣也促成了譯者與譯者的視域融合,后來的譯者借助對前人經驗的“體系化”總結,使得視域融合從單純的橫向向橫向與縱向結合的立體融合發展。
闡釋學對“誤讀”的興趣同樣可以通過語料庫豐富的例證得到較好的滿足。例如在上述表4中,“I think keeping animals locked up in cages is criminal.”翻譯成中文是“我認為把動物鎖上關在籠子中是不道德的。”就可能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原文作者想說的說不定就是“把動物關在籠子里是犯罪”呢。通過這樣的對照,一些有意無意的“誤讀”就很容易被發現,其中蘊涵的闡釋學和文化意義也能得以很好地揭示。
計算機語料庫的建立,使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平行語料庫或廣義的網絡語料解決先前很難解決的問題。由于廣義的語料庫不僅包括為了專門研究語言收集的語料,還包括所有使用語言,并能夠從中檢索挖掘出信息的語料,所以像中國知網翻譯助手和各種電子辭典這樣的工具也是很好的語料,它們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翻譯例證。仍然以與“道德”相關的詞匯為例,它不僅列舉了“morality”一詞對應的翻譯“倫理”和“道德”的例證,還列舉了諸多非對應的翻譯例證(見圖1)。
語料庫的發展,部分實現了對包含前人翻譯經驗語料的體系化和結構化。通過雙語平行語料工具、語料編輯工具和語料檢索工具,實現了對前人經驗的結構化,但結構化如果能夠結合譯者判斷的體系化,前人知識就會轉化為當前翻譯的知識,從而為古今、中外的視域融合鋪平道路。經驗的體系化不能夠仰賴機器獨立完成,實際上機器完成的正是非價值判斷的那一部分,而價值判斷則留給闡釋者來解決,但機器的作用是為后者的判斷提供充分的依據,而這一切仿佛是給闡釋學插上了翅膀。
闡釋學所強調的不確定性在語料庫實踐中已經得到證明,由于諸多的不確定性的存在,翻譯表現為一種闡釋行為。如果考慮到意識形態、文化、語言禁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們便能夠發現,翻譯不僅是選擇,而且是闡釋性選擇。中國特有的外宣翻譯就遠遠超出了一般翻譯的范疇,除了信息的選擇要十分注意以外,還需要注意增添解釋性文字。而外宣翻譯中的解釋,正是闡釋學進入實踐的一個重要途徑。當前中國在全世界建立的孔子學院,實際上也是通過闡釋孔子達到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但必須注意其中的闡釋學原則,今天傳播的儒家文化決不應該是包含封建糟粕的儒家文化,而應是融入了當代社會倫理要求、且能夠為所在國人民接受的儒家和中國文化。這其中涉及的經典闡釋與翻譯問題不可謂不多。
闡釋翻譯甚至波及到自然科學的翻譯。科技工作者的論文寫作不應該是簡單的翻譯,而應該是譯寫結合的實踐工作,其中也包括順應國際期刊的規范。筆者曾為不少工科教師校改過論文,很多老師不能理解外國的編輯為什么特別強調要我們修改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語法錯誤。實際上,這里也涉及一個視域融合的問題:中國科技工作者所撰寫的論文、所體現的語言認知如果有悖于英語的表達,就不能很好地順應目的語的規范要求;而各國科學家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英語,那么英語最終只能成為“Englishes”,從而失去作為國際學術語言的資格。要解決這一問題,語料庫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大量的學術期刊數據庫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參考的絕佳資源,蘊含了大量“體系化”經驗的外文文獻為科技論文的譯寫提供了參考。
當然,利用“體系化”經驗來輔助闡釋實踐有其工具的局限性,那就是有些語料庫使用的語料往往不是經過仔細選擇的專家譯者的翻譯,比如中國知網翻譯助手和諸多網絡電子詞典,其中所包含的翻譯錯誤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這種“體系化”的經驗材料也是非常可怕的。筆者有一次讓學生翻譯“高等院校”一詞,學生給出的答案是“institutions of higher”,問其來源,說是手機中的電子詞典!可見,計算機語料庫并不能完全代替紙媒詞典等傳統工具書(包括其電子化版本),因為語料庫往往僅僅是語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不對語料的正誤做出判斷,這就需要譯者參與自主選擇,這也進一步證實了語言和翻譯實踐應用的闡釋性。
五、結語
長期執著于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脫離語言解釋實踐的闡釋翻譯學研究必然是死路一條。在闡釋翻譯學研究中引入實踐維度概念,結合語料庫語言學的發展,探尋解決闡釋翻譯學的實踐路徑,給闡釋翻譯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闡釋翻譯學因此能夠通過語料庫積累的“體系化”的前人經驗,依靠譯者的主體選擇,使闡釋翻譯學擺脫單純的理論研究困境,從而建立起可實際操作的開放理論體系。
(本研究受江蘇省教育廳項目[No.2012SJD740011]:“基于語料庫的雙語詞典例證選擇與翻譯研究”支持。)
致謝:感謝南京大學魏向清教授的悉心指導和對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1]蔡新樂.翻譯還是它本身嗎? ——“通化翻譯”辨析[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1,(10).
[2]伽達默爾,杜特.解釋學 美學 實踐哲學:伽達默爾與杜特對話錄[M].金惠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3]伽達默爾.詮釋學 I II:真理與方法(修訂譯本)[M].洪漢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4]耿強.對闡釋學翻譯研究的學科反思[J].外語研究,2006,(3).
[5]何衛國.通向解釋學辯證法之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6]梁茂成.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與語料庫語言學[J].中國外語, 2010,(7).
[7]張德讓.翻譯與詮釋學的會通——評李河的《巴別塔的重建與解構》[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6).
[8]Pym,Anthony.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A].in Piotr Kuhiwczak and Karin Littau(ed.),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C].Clevedon· Buffalo ·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7.
[9]Robinson,Douglas.The Translators Turn[M].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張明權 江蘇鎮江 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 2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