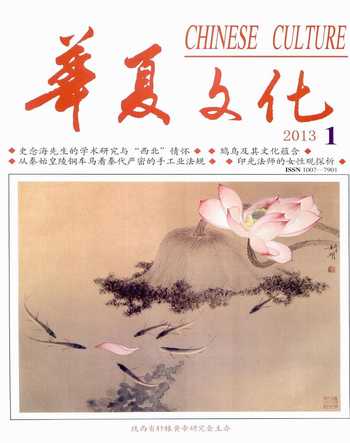信仰、道與文化自覺
田探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廣義的“信”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古文獻中出現“信”的頻率非常高。它不僅是“四德”(孝悌忠信)之一,還是“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一。中國古人十分重視社會領域中對于“信”的貫徹,如君臣之間的信、官與民之間的信,如“與國人交,止于信”(《大學》);朋友之間的信,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學而》),夫妻之間的信、人與神之間的信,如“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等。“信”在這里表達出的是信任、相信、守信、信仰等多方面的含義。信仰只是其中之一義而已,含義要小得多。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廣義的“信”作為人際關系之間的價值準則,其實用性的含義信任、守信、信用得到了較多的強調。即使《論語》中的“祭神如神在”,以及《曹劌論戰》中對神的“必以信”,也并不是在信仰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在說人對神也應該講信用,心中對神有所求,所以許諾給神的供品一定不要失信于神。這種觀念其實依然將“信”當做實用的工具性手段。相比之下,信仰概念的意義范圍雖然比較單一,但是它卻比“信”的其他意義具有更加純粹的精神性。在中國古代,信仰多與“道”相聯系,《論語》中子張言“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論語·子張》),表達對道德理想的追求與堅守;《大乘義章》中有“于三寶等凈心不疑明信”(《大乘義章》),表達對釋迦牟尼佛、佛教教義、佛教僧人的信仰;而《華嚴經》就直言“信為道元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除滅一切諸疑惑,示現開發無上道”(《華嚴經》),表達了信仰的重要性。
在中國傳統的儒學語境中,信仰更多表達的是“自信”。自信并不意味著自負和自戀,而是對自身力量的認知和運用,即在追求道的過程中,自己對尋求自己之“道”的自信,“道”會隨著這種自信在個體的實踐中逐漸展現出來,而自信也會隨著道的不斷展現而變得更加堅定。這種自信是對自己所探尋之道的自信,即對于人道的自信。然而值得追問的是,這種對于自我探尋之道的自信是否意味著人道對于天道來說具有某種先行性,換句話說實際上是人道決定了天道。但是,如果是人道完全決定天道,那么天道人道之分還有什么意義嗎?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是人道對于天道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天道是實踐人道的結果,那么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唯我論的深淵,而且在邏輯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及“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為人準則都可以成為信仰的對象。因為,從人道即是天道的理論來說,任何人在邏輯上都無法駁斥這種觀念,而只能從倫理道德,或者從其所導致的實用效果出發進行批判。但是這樣的批判缺乏理論的力量,而且理論上的爭論很容易滑落為對道德至高點爭奪的歧途,從而喪失對問題真正有意義的討論。
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信仰始終將自己保持在具有張力的天人境域中。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上帝永遠超脫于世俗,他是超越了一切感性和理性的認識的超驗實體,卑微的人永遠不可能與上帝相提并論。但是中國的信仰卻承認人可為圣,“天”與“人”之間的溝壑是可以溝通的。《中庸》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禮記·中庸》)從這段話不難看出,中國的信仰具有以下程式:即信(天道)——實踐(人道)——自信(天人合一)。貫徹其中的就是“道”。這里的天道并不是自在的自然規律和宇宙法則,而是已經進入主體視野的人之天,當然人之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主體對于天道的某種具體的認識,或者是在認識論領域內的“人為自然界立法”,而應該理解為在其中人道得以被引發出來。所以人之天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代表著一種歷史境域,此境域先于一切境中的事物并且使其成為可能。
我們以孔子對待鬼神的態度為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表達的是在祭祀神靈的時候要與神靈同在。有人認為孔子對于鬼神存在持有深深的懷疑的態度,這是誤解。孔子所理解的鬼神絕不是脫離了人世間高高在上俯瞰眾生且行使著對人間主宰的怪、力、亂、神,而是在祭祀神靈的過程中所揭示出的具有德性智慧的生活。《中庸》言:“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禮記·中庸》)“齋明盛服”祭祀活動正是使鬼神作為一種德性得以進入我們生命的方式。孔子在祭祀之時通過和穆中節、細密周致的禮樂儀文來引導和激發超出說教的德性與智慧。在祭祀的過程中向行祭祀者所敞開的是歷史所積淀下來的文化生命,這才是“天之道”。換句話說,祭祀成為我們自我覺醒、自我完善的階梯,是我們自覺地承繼文化生命的開放場所。雖然圣賢的身體已經死亡,但是文化生命并沒有消散于天地間,它還作為一種形態——“氣”游蕩于天地之間。對于尚未承繼文化生命的人來說,“天道”隱藏于天地之間消散為氣,“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禮記·中庸》),但是它又充塞于天地之間,“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禮記·中庸》)。中國古代哲學中從來都只有氣聚氣散,而沒有絕對的消失。生命雖然已經逝去,但是通過歲月的洗滌和歷史的積淀,它們的“道”已經深深地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辭上》)。此時,“道”對于尚未覺醒的常人來說是隱而不顯、暗而不彰的“鬼神”。這些飄蕩在天地之間的生靈始終默默地等待著獲得新生的機會。祭祀便是溝通“鬼神”,使它們獲得新生的一種方式。然而,祭祀中的禮儀只是一種引導,更重要的是通過祭祀的禮儀引發對于文化生命真誠的敬仰之情。所以《中庸》強調“誠之者,人之道”(《禮記-中庸》),孟子強調:“思誠者,人之道。”(《孟子·離婁上》)故此,文化生命(鬼神)的重生需要的是對它們持有堅定信念的真誠的心。只有具有這種信仰的人才能夠真正地覺悟,從而自覺地承繼歷史所遺留的文化生命。這與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理論進路是相符合的。
可見,信仰“天道”的實質是持有一顆對于古往今來所積淀的歷史文化生命的真誠的向往與敬仰,以及決心繼承的意志,這意味著一種覺悟。只有開悟至此,“天道”才可能向我們敞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就是因為它還尚未被承繼者所繼承,處于自在的狀態,是消散于天地之間的“氣”,但它又不是脫離了人的自在的宇宙法則,而是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淀,其中宇宙法則、自然規律也已經以文化的方式進人了歷史,因此,這里的“天道”實際上是“人之天”。
但是,對“天道”的覺悟僅僅是第一步,信道最重要的是要行道,所以第二步就是實踐道。實踐道就是將所信仰的“天道”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引,并以此為指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實踐。“天道”作為歷史積淀下的文化生命,本身雖然具有指引的性質,但是畢竟每個個體都處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之下,都具有不同的歷史語境。因此需要個體根據實際的條件對流傳的文化生命進行自我理解和運用,這其實就是消化“天道”,并且進行文化創新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化“天道”為“人道”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對于“天道”有所懷疑的個體通過實踐不斷加深對“天道”的理解,進而增強對“天道”的信仰和對自身生命力的自信;而且化“天道”為“人道”,實際就是作為文化生命承繼者的個體——“我”在創造新的文化生命,在創造新的“天道”。此時的“天道”就是我化舊“天道”而來的“人道”,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也是真實發生的文化自覺過程。
在此過程中,“我”作為個體獲得了對于“道”的真切體認,在“天道”與“人道”的不斷轉換中,“我”也由對“天道”的信仰轉變為“自信”。“我”的“自信”是來自于對于歷史文化生命的敬仰和欽佩,以及自我對“道”的踐履。因此“自信”永遠都包涵了對文化生命本身的尊重和信心,而不會淪落為抽空了歷史感的自以為是和對文化生命不屑一顧的蔑視。更為重要的是,建立在天人關系上的信仰具有極強的張力,它不僅消解了“道”的超驗性和信仰的神話性質,而且歷史的而又當下生活中的個體通過切身參與所信之“道”,使外在地指導和規定人的現實生活的“天道”失去了超然獨立于人的生命力,這個“天道”使離開了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由此,信仰存在的意義和根據牢牢地扎根于人的現實生活之中,從而避免了超驗的“天道”對現實生活中人性的控制和壓抑,使“天道”與“人道”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張力的系統。
由以上對中國傳統信仰特色的解析,我們可以總結出對于中國傳統信仰不同以往的觀點:即她是建立在天人互動上的一種中國獨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她排斥外來強制性的信仰,而力圖通過某種“斯文”的方式來引導和激發個體乃至整個人類的向“道”之心,她始終是溫和的、循循善誘的,文質彬彬的;她不會告訴我們現成的答案,而是提供開放的場所,讓我們自己去感受,去體悟,所以,她又如鬼神般神秘莫測。而當我們一旦感受到圣賢的生命,那種充滿著生機的文化力量和“浩然之氣”就如同“天命”般,深深地滲透于生命之中,充沛于五臟六腑,好像成為我們的本性,使我們不得不去實踐她、履踐她。這個過程不是外在的知識積累,而是生命力量由內向外的逐層展開。這種展開貫穿著我們的一生,所以她不是某種具體的生存技巧,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詮釋。這種詮釋并不是脫離了歷史語境的任意規定,而是奠基于歷史文化生命中的文化自覺,是在承繼文化中創造新的歷史文化。
(作者:江西省南京市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郵編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