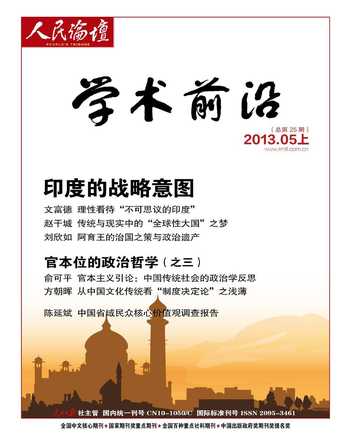歷史語境中的“重返亞太”
趙學功 劉長新
摘要 美國的亞太政策是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美國的亞太政策有幾次重要的調整,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五六十年代杜魯門政府至約翰遜政府的干涉時期,主要特征表現為遏制蘇聯共產主義在亞太地區的擴張;七十年代尼克松—福特政府時期的戰略收縮時期,美國減少了在亞太地區的政治軍事存在;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重返亞太時期,美國從戰略收縮轉為戰略擴張,更為積極地插手亞太事務,遏制蘇聯在亞洲的軍事力量。
關鍵詞 冷戰 遏制 美國亞太政策
【作者簡介】
趙學功,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美國史、國際關系史。
主要著作:《當代美國外交》、《巨大的轉變:戰后美國對東亞的政策》、《十月風云:古巴導彈危機研究》等。
劉長新,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在全球各個地區展開了競爭,而對于亞太地區的爭奪,始終是美國這一時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主要是由于該地區集中了中國、日本、蘇聯及東盟等重要的國家和集團,是當時世界經濟、政治及軍事的重心之一。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杜魯門政府到80年代的里根政府,美國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五六十年代杜魯門政府至約翰遜政府的干涉時期,主要特征表現為遏制蘇聯共產主義在亞太地區的擴張;七十年代尼克松—福特政府時期的戰略收縮時期,減少美國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重返亞太時期,美國從戰略收縮轉為戰略擴張,更為積極地插手亞太事務,遏制蘇聯在亞洲的軍事力量。
美國干涉亞太肇始
冷戰初期,隨著美國政府的全球擴展戰略的展開以及對蘇聯遏制戰略的確立,美國政府公開宣稱要推行以拉丁美洲為后院,以太平洋為內湖,以大西洋為內海,以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部署,力圖把全世界都置于美國的支配之下。①美國開始與蘇聯爭奪國際地緣政治中的“權力真空地帶”,亞太地區因而成為雙方爭奪的重要戰場。杜魯門政府于1948年通過的對外軍事援助基本政策及《共同防衛援助法》就將包括中國、菲律賓在內的亞太多國納入軍事援助范圍,杜魯門本人更是宣稱美國要完全控制日本與太平洋。②由此,反共成為美國政府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基調。這一時期的杜魯門政府及隨后的艾森豪威爾政府、約翰遜政府先后參與了中國的內戰、朝鮮戰爭并卷入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按照雅爾塔體制的劃分,美國犧牲中國在東北的利益換取了蘇聯對中國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的承認。戰后初期,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存在著戰略利益上的共識,即兩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徹底主宰中國事務,也沒有能力長時間阻礙中國的統一,因而兩國都主張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主導的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軍事力量架構。但是,雙方在深層次戰略意圖上卻存在著重大分歧,美國希望國民黨將共產黨的政治及軍事力量逐步吸收與溶解,而蘇聯則希望共產黨始終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及軍事力量。隨著戰后美蘇戰時同盟的破裂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加劇,美蘇在歐洲的矛盾逐步激化,在亞太地區的對抗前景也日益清晰,美國政府日益重視中國在亞太的戰略地位,認為蔣介石政府統一中國并成為穩定亞洲及抗衡蘇聯的角色對美國的亞太戰略至關重要。由此,美國把扶植蔣介石政權作為東亞政策的重點,將原來的“扶蔣,壓共,促和談”的政策轉變為全力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從1946年至1949年,美國政府給予了蔣介石政權以強有力的經濟及軍事援助。經濟援助方面,美國于1948年4月通過了《1948年援華法》,決定給予蔣介石政府4.63億美元的援助,其中1.25億為“特別贈款”,可由中國政府自行使用。軍事援助方面,美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裝備,武裝了國民黨軍隊數十個師,還派遣軍事顧問團向蔣介石提供作戰意見,幫助國民黨訓練軍隊。根據美國政府后來的統計,美國在抗戰勝利后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大概1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以及1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事實上直接卷入了國共內戰,包括幫助蔣介石重新部署陸軍、美軍直接占領關鍵的地區并控制重要的交通線等。③雖然到1948年末,杜魯門政府認識到國民黨政權的失敗已無可挽回,美國國務院也制定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4號文件,確立了從中國脫身的政策,但是杜魯門本人直到1949年2月才正式批準這一文件。而縱觀1949年至1950年的美國對華政策,繼續扶植國民黨政權對抗共產黨,阻撓中國革命的勝利,拒不承認新中國的合法地位仍然是對華政策的主導。
在中國大陸的形勢已經明朗的情況下,為了繼續確保其在亞太地區的霸主地位,遏制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張和社會主義運動在該地區的發展,美國建立了一個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沖繩、臺灣,到東南亞的所謂“弧形防線”,先后與日本、韓國、泰國、臺灣、菲律賓、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簽訂了共同防務條約和軍事援助協定,并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而隨著這一時期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對亞太地區的軍事遏制與干涉政策更是達到了頂峰。
二戰結束后,美國政府認為朝鮮對于美國稱霸亞太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價值,朝鮮被美國政府視為控制中國和亞洲大陸的前沿陣地。駐日占領軍司令麥克阿瑟曾多次指出朝鮮是通往大陸的橋梁,美國通過朝鮮就可以控制海參崴和新加坡之間的整個地區。④此后,在美國的提議下,朝鮮半島被一分為二。1949年中國大陸革命勝利后,美國擴大了對南朝鮮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積極訓練和武裝南朝鮮的軍隊。美國國務院認為必須“以在朝鮮的勝利來彌補在亞洲各地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外交挫折”。⑤朝鮮戰爭就在此背景下爆發了。
朝鮮戰爭爆發之初,杜魯門就宣稱,“如果聽憑南朝鮮淪喪,共產黨的領袖們就會越發狂妄地向更靠近我們海岸的國家進行侵略。如果對這種侵略行動不加以制止,那么就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⑥杜魯門政府認為美國必須采取強硬措施拯救韓國,阻止共產主義在朝鮮半島的擴張。1950年9月,杜魯門批準了針對朝鮮行動的NSC81/1號文件,正式確立了武力干涉朝鮮內戰,并逐步將戰爭升級,以軍事手段在朝鮮半島建立一個親美國家的行動方針。隨后美軍在仁川登陸并迅速越過“三八”線,企圖用武力強行統一朝鮮。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后,仍繼續奉行強硬政策,中斷和平談判,使得戰爭一直持續到1953年7月。這場持續數年的戰爭使得美國政府確信中國是比蘇聯更為危險的敵人,亞洲地區對美國構成了更為直接的威脅。朝鮮戰爭也成為中美關系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自此之后的20余年間,中美兩國對峙,成為針鋒相對的對手。⑦
這一時期,美國政府進一步干涉亞太事務的第三個表現是積極介入印度支那事務。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出于瓦解法國在亞洲的影響以及對殖民主義厭惡的考慮,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確立了美國政府的“不插手”政策,即不介入印度支那地區的戰爭與沖突。隨著冷戰時代的來臨,美國政府認為世界任何地區都與美國的安全利益相關,而在印度支那地區,杜魯門政府認為法國的軍事行動實際上是抵御來自于中國的共產主義的擴張。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美國放棄了原來的“不插手”政策,開始支援法國的印支戰爭,以阻止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取得勝利。
1948年9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第一個完整的印支政策報告,提出了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目標——防止中國對該地區的滲透,盡力消除共產主義的影響。報告指出,美國應該鼓勵、支持并積極參與法國和平解決印支問題。⑧1949年3月,美國政府又制定了PPS51號文件,即“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的研究報告,指出東南亞地區對“自由世界”極具重要性,這一地區必將成為東西方陣營爭奪的重要地區及蘇聯進攻的目標,美國應該幫助該地區的非共產黨勢力取得政權,要支持泰國及菲律賓抵制蘇聯與中國的蠶食,尤其是敦促法國與英國及印度合作解決印支僵局等。⑨此時美國的政策已開始向明確支持法國和越南保大政權的方向發展。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后,美國逐步確立起以遏制新中國為核心的東南亞政策,杜魯門政府及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逐步加大對東南亞非共產主義國家的軍事援助,全面干預東南亞事務,尤其是大舉介入印度支那事務。朝鮮戰爭爆發第三天,杜魯門就指示增加對法國和越南保大政權的軍事援助,美國的軍事顧問團也于7月份到達越南。此后,美國援助法國的各類物資及裝備源源不斷地流入印支地區,到1953年,美國的援助金額已經達到了5億美元。
艾森豪威爾政府上臺之后,美國政府繼續奉行支持法國在印支地區進行殖民戰爭的政策,美國的援助金額占到了法國印支戰爭軍費開支的78%。艾森豪威爾更是于1954年4月提出了多米諾骨牌理論,認為西方在印度支那的失敗將波及東南亞各國,并將對“自由世界”造成連鎖反應。在日內瓦會議之后,法國撤出了印支地區,從這時開始,一直站在法國背后的美國站上了前臺,美國軍事力量直接介入了印支戰爭之中,干涉的程度日益加深,并在約翰遜政府時期達到了頂峰,最終使得越南戰爭“美國化”。
從亞太脫身
侵越戰爭是冷戰期間美國對亞太地區軍事干預的頂峰,也是美國全球干涉政策的高潮。到尼克松上任之時,美國的內政與外交已經陷入困境。在國內,持續多年的越戰使得美國經濟變得極度畸形,社會分崩離析,國內問題成堆。⑩在外交領域,趁美國深陷越戰之際,蘇聯大力擴充了經濟、軍事及政治實力,使得美國在兩極對立中處于劣勢。西歐盟國及日本的經濟迅速發展,政治影響力得到提升,對美國構成了巨大挑戰,尤其是在外交領域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而與此同時,第三世界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促使美國的擴張戰略不得不開始做出調整,在此背景下,尼克松主義應運而生。
1969年7月23日,尼克松在關島作了一次關于外交政策的演說,這是他就任總統后首次發表的關于對外政策的聲明,該聲明提出了美國亞太政策的新方針。尼克松在演說中指出,美國將不再卷入像越南戰爭那樣的軍事沖突,并將減少在亞洲承擔的軍事義務。在新的時代里,美國仍將承擔大部分的責任與義務,但是其他國家必須分擔比以前更多的責任。他強調:“從現在起,我們只準備向那些愿意承擔責任以自己的人力來自衛的國家提供物資和軍事經濟援助。”11月3日,他在全國的廣播電視演說中更明確表達了尼克松主義的三原則,即:美國將恪守所有的條約與義務;如果某個核大國威脅美國盟友的自由,美國將提供保護;在涉及其他形式的侵略的場合,美國將根據義務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但受威脅的國家要承擔為自身防務提供人力的主要責任。
尼克松主義是尼克松上臺后為擺脫美國所面臨的困境而采取的現實主義的態度,是針對這一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尤其是亞太戰略所做出的戰略調整,這一戰略也被后來的福特政府及卡特政府繼承并發展。從本質上而言,該戰略是美國政府的遏制政策在新形勢下的繼續和發展,是“美國領導的新定義”。尼克松主義在亞太地區進行的戰略調整主要包括結束越戰、同新中國和解以及改善美日關系等。
尼克松主義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實現越戰的“越南化”來結束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卷入。尼克松本人將“越南化計劃”視為尼克松主義最重要最明顯的運用,認為“我們的整個戰略都取決于這項計劃能否成功”。為了實施“越南化”計劃,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繼續在越南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則尋求通過談判實現和平解決。從越南撤軍的行動在尼克松上臺伊始便開始實施。事實上,美國政府的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計劃與美軍的撤軍行動及談判活動是緊密配合進行的,尼克松的真正目的是利用越南人之間的戰斗為美軍的撤出創造條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尼克松甚至采取了一些嚴重的戰爭升級行動,將戰爭擴大到越南北方及整個印支地區。經過多年的談判,直到1973年才最終簽訂了停戰的巴黎協定,這標志著長達12年的侵越戰爭初步結束。之后在福特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徹底拋棄了南越政權,福特總統于1975年4月23日在演說中正式宣布,對美國而言,越戰已經結束。越戰對美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力量,成為二戰后美國從頂峰走向相對衰落的轉折點。同時,越戰還給美國人民造成了嚴重的創傷,給美國社會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
尼克松主義的另一項重要實踐是改善對華關系。尼克松與基辛格都將緩和中美關系視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實行政治、軍事收縮的重要內容。同中國改善關系,被認為將有利于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進而有助于美國順利地從亞洲地區撤出軍事力量。因此,尼克松在就任總統兩周之際,就授意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即國家安全研究第14號備忘錄,提出了“兩個中國”的政策,承認了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后來又在國家安全研究第35號備忘錄中提出應逐步取消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限制,以此作為接近中國的先聲。1970年1月20日,中美恢復了在華沙的大使級會談,此后,尼克松政府先后多次公開表示希望訪問中國。經過一系列的秘密溝通與交流,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的訪華計劃最終成行,雙方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這標志著兩國20多年的相互敵對狀態的結束。中美關系的正常化成為這一時期尼克松亞太外交戰略中的關鍵一環。
日本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盟國,基辛格認為,與日本的友誼是美國“太平洋政策的基石”。尼克松政府在亞太地區進行戰略收縮之際,非常希望日本能在亞太地區為維護美國的利益發揮更大的作用。而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加快了其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步伐。美國的期望與日本自身的期望不謀而合,于是尼克松政府調整了美日關系,其中最為重要的措施便是向日本歸還沖繩的行政權,因為這一問題始終是戰后美日關系發展的一個癥結所在。1969年11月,美日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確認美國將把沖繩的行政權歸還日本,到1971年6月,雙方達成最終協議,從而掃清了兩國關系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與此同時,雙方繼續保持并進一步發展了戰后建立起來的同盟關系。經過尼克松政府的調整,美日關系逐步從先前的從屬與支配、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轉化為平等與相互依賴的關系,日本在美國政府的亞太戰略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回歸亞太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政府推行的緩和戰略表明美國承認了自身國力的衰退,但是美國政府在緩和背景下進行的外交政策調整只獲得了部分的成功,并未從根本上扭轉美國國際影響和國際地位相對下降的趨勢。世界格局繼續向著多級化的方向演變,美國面臨的狀況更加復雜,到卡特政府時期,美國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比尼克松時期更加力不從心。里根總統就是在美國外交政策面臨失敗的背景下上臺的。
1981年,以重振美國國威為口號入主白宮的里根在上臺伊始就提出美國已不再是尋求緩和與妥協的美國,而是要抵抗蘇聯在全世界的擴張主義的美國。里根指出,“危機是迫切……是時候采取行動了”。由此開始,以武力為主要手段來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里根主義”正式確立。而與此同時,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迅速崛起,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格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基礎上,里根政府的亞太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調整階段。里根總統本人及其顧問都多次強調這一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國務卿舒爾茨1981年3月在其“太平洋的潮水日益高漲”的講話中稱,東亞太平洋地區對美國而言至關重要,美國仍是一個太平洋強國,并將在這一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更是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正從歐洲轉向亞太地區。
里根政府對亞太地區政策上的調整并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層次原因的。首先是亞太地區對美國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經濟意義。從二十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初,亞太眾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率一直高于世界其他地區,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際,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在1982年仍達到了4%,其貿易額總量也占到了世界貿易總額的1/6,占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了30%,美國在該地區的投資總額也不斷增長。其次,這一時期美蘇在亞太地區政治及軍事上的對抗日益激烈。蘇聯政府趁尼克松政府戰略收縮之際,大大擴充了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企圖控制北起日本海,南至波斯灣的海上戰略通道,并進而威脅東盟各國,使之脫離美國的勢力范圍。在美國看來,蘇聯的行動嚴重威脅了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及軍事利益。因而,里根政府力圖恢復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軍事力量,加強同蘇聯在這一地區的爭奪。
里根政府重返亞太政策最直接的體現是強化美軍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存在。從尼克松政府開始,美國在該地區實行逐步收縮兵力的政策,從越南及南朝鮮撤出美軍。里根入主白宮后,停止了前幾任政府的這一政策,取消了從南朝鮮撤軍的計劃,同時還開始強化美軍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力量。里根政府給美國第七艦隊增派了15艘洛杉磯型攻擊潛艇,配備了“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空母艦及“新澤西”號戰列艦,并計劃在幾年之內將第七艦隊的艦只數量從80艘增加到100艘。另外,美國還加快更新了亞太地區的空軍力量,為沖繩的嘉手納基地及南朝鮮的基地裝備了新式的戰斗機。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駐軍人數也有了顯著地增加。美國軍事力量的“重返亞洲”是里根政府整體政策的重要體現。
在外交政策方面,里根政府采取了全面轉向太平洋地區的方針,進一步穩固了美日、美中關系。二戰后日本成為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盟國,維持與日本的同盟關系是美國歷任政府的既定政策,但是里根政府對美日關系的重視程度超過以往歷屆政府。里根總統1983年1月在沖繩的演說中指出:“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言,沒有比美日關系更重要的雙邊關系了。”里根政府不斷加強與日本的政治同盟,并將同盟關系寫入聯合公報之中。日本政府也積極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成為美國對抗蘇聯的重要力量。在安全領域,美日雙方就日本要承擔更多的防務費用,分擔更多的責任達成了共識,同時雙方還進行了軍事技術上的合作。里根政府面對國際形勢和美日力量對比而作出的對日政策的調整進一步加強了兩國的戰略盟友關系,彌合了雙方在經濟貿易及防務問題上的分歧與矛盾。而在中美關系方面,里根就職后,一再聲明將遵守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的規定,發展同中國的關系。雖然之后由于對臺軍售問題,中美關系受到了嚴峻的考驗,但是經過談判,中美兩國又發表了關于解決對臺軍售問題的《中美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消除了兩國關系正常發展的最大障礙。之后,里根政府修正了對華政策,認為亞洲不僅是重要的,而且美國在同日本等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加強聯系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善同中國的關系。里根在向國會提交的《國家安全報告》中也明確提出,美國主要的國家安全目標之一就是加強與中國的關系,“一個強大、安全和現代化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
除上述的軍事及外交措施外,在經濟層面,里根政府認識到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才是保證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關鍵。同時,這一時期亞太各國的經濟還有著良好的發展空間及態勢,與美國的經濟結構也形成了互補與契合,因此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與亞太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并使之制度化與規范化。通過采取降低關稅、簽訂貿易協定等措施,美國與日本、東盟諸國的經貿往來有了大幅度提升。值得關注的是,里根政府還推動建立了“太平洋經濟共同體”,認為這將進一步密切美國與亞太地區國家間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的聯系,進而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
通過探討冷戰期間美國政府的亞太地區政策,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條清晰的線索,即冷戰期間美國的亞太政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美國的亞太戰略經歷了“干涉”、“戰略收縮”及“重返亞太”這三個主要的階段,并且每個階段都形成了自己的特征。美國的外交政策為何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的調整?這就涉及到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問題。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多種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包括國家的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等內部決定因素以及國際格局變動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等。影響冷戰期間美國亞太政策演變的因素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即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等內部因素,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以及亞太地區不斷變化發展的局勢等外部因素。冷戰期間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的戰略調整一定程度上適應了不斷變化發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格局,但事實也證明這種調整更多程度上是一種被動的調整,美國政府在實踐中仍然經歷了眾多的挫折與失敗。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核武器與美國對外關系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2BSS033)
注釋
紀勝利、郝慶云:《戰后國際關系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18頁。
Margaret Carlyle,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294-303.
資中筠:《戰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132、943頁。
《紐約時報》,1948年10月22日。
劉緒貽、楊生茂:《美國通史》(第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頁。
[美]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1974年,第394頁。
Doak Bamett, 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178.
Gareth Porter, Vietnam—A History in Document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9, 76.
FRUS, 1949, vol.17, part2, 1131-1133.
[美]拉爾夫·貝茨:《美國史:1933~1973》(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8頁。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中),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9頁。
NSSM36, Vietnamizing the War, April 10, 1969, NSC Files, Box 365, Nixon Project, National Archives.
[美]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1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428頁。
Nora Hamilton, Jerry A. Frieden,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Regional Dynamics and U.S.Policy in the 1980s,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1988, 78.
謝小川:“從里根遠東之行看美國的亞太政策”,《世界知識》,1983年第23期,第5~6頁。
梅孜編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匯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年,第123頁。
責 編/鄭韶武
"Returning to Asia-Pacific"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re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US Asia-Pacific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Zhao Xuegong Liu Changxin
Abstract: The US Asia policy had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global strategy during the Cold War. It experienced several key adjustments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80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first was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from Truman to Johns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US containment of Soviet expansion in Asia-Pacific; the second was the contraction period from Nixon to Carter, when US administrations changed policies and reduced military existence in the region; the third was the Reagan years of returning to Asia-Pacific, when the US tried to re-enter into Asia-Pacific and more actively intervened in the Asia-Pacific affairs so as to contain the military power of Soviet Union in Asia.
Keywords: The Cold War, containment, US Asia-Pacific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