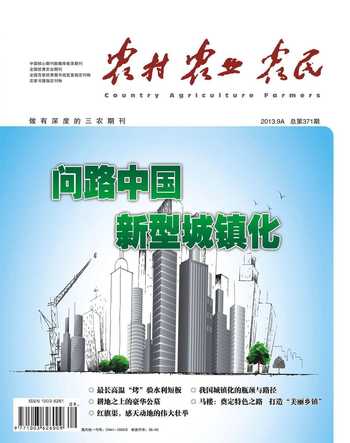我國城鎮化的瓶頸與路徑
宋健坤
我國城鎮化建設從規模上講將是亙古未見的,其總投資將超過200萬億元,從建設的時間跨度講,將超越30年,歷經幾代人。
我國城鎮化建設所受關注超乎尋常,目前已經至最高決策層面。從多次的政策調整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化發展并非一帆風順。
必須承認,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確存在亟待解決的帶有全局性的若干原則性問題,這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瓶頸。而要實現我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這些瓶頸顯然需要突破。
城鎮化不能等同于全民城市化
我國之所以選用“城鎮化”而未按國際慣例使用“城市化”一詞,其出發點與落腳點均在于解決占我國人口超過半數的廣大農民的歸宿問題。這就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在“鎮”字上下功夫,在“鎮”字上尋求突破,在“鎮”字上最終求得落點。那種通過在“圖上作業”,在全國地圖上“圈上幾個圈”,再下達指令搞上幾個所謂“城市群”,試圖以此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國城鎮化發展的路徑問題,其設計的邏輯起點就存在錯誤。
目前,全球各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都在“回歸自然”,都在強調走“生態保障型”的設計理念與實現路徑,普遍持“反大都市化”理念。事實上,歐美城市化發展,即便是在二戰后經濟與人口高速發展階段,也始終未脫離人性化的軌跡,其城市化發展脈絡清晰:村、鎮、中小城市、大城市鱗次櫛比,相互銜接,不存在“突兀”的所謂城市群。尤其是德國的城市化發展充分印證,從設計理念到空間結構布局,真正在實踐我們今天正在提倡的“城鎮化”特征。
之所以不能提倡“城市化”,主要原因是其導向易使人們走向大都市化。而“城鎮化”的“鎮”,并非是狹義的村鎮,而是指廣義的非大都市而言,可以將其理解為小城市。不可否認,邁向大都市化是廣大百姓之所愿,卻不是我國國情所能承載的,更不應成為科學決策的依據。
我國城市承載力持續下降,以水資源為例,目前我國一個東部的小城鎮的水消耗量與中部地區中等城市及西部地區大城市持平。這說明,東部地區的人口聚集已經接近極限,空間布局如若再以這種超大方式作為邏輯起點去設計、去推動產生新的城市群,甚至到水資源更為缺乏的中部、西部地區去復制若干個城市群,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城鎮化”發展不單純是理念問題、國情問題、理論路徑問題,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吃,城鎮化發展也要如此。
城鎮化必須涉及土地制度改革
我國城鎮化中最突出的矛盾集中在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上。農村土地是集體土地所有制,土地數量固定,但集體數量可以變化,這就使得土地衍生出“分配和再分配”的利益問題。我國城鎮化的下一步發展,最大難點在于對現有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城鎮化在部分地區的運行,事實上已經演變成“賺取土地差價的運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指出,近年來政府從征購價格和土地批租價格間所賺取的差價最低估計為30萬億元人民幣。
土地制度如何改革?是將土地從農民手中“贖買”后再全面實施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還是有條件地將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全面國有化,或者在國有體系下繼續實施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配置”?管理權的選擇方式,是向現有地權擁有方傾斜,還是向索取地權的利益方傾斜,抑或是增加自己的“權利地租效益”?目前看,土地制度無論以何種方式設計,最應堅守的原則底線,是要避免城鎮化成為新一波掠奪農民土地的全面運動。
土地問題是聚集我國所有問題的核心。由其衍生出的地租,就目前農民個體而言,其全部意義包含農民一生生存的全部成本:房屋、生活費用、工作等。在這輪事關農民生存的土地制度的改革設計中,如果把土地使用權改革作為突破口,在土地進行確權并實施合理補償之后,對土地使用權進行私有化、家庭化、集約化的改革,同時對土地管理權實施有效改革,調整其謀取地權利益的偏好,那將釋放出大量勞動力和產生巨大的農業效益。
城鎮化不能再催生第二個四萬億
我國今天城鎮化建設,在一些地方已演變為“透支財政”的“大比拼”。從世界范圍來看,任何國家的城鎮化發展都是工業化演進的結果,大量農村廉價勞動力擁入城市,在給企業創造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歷史上的城鎮化更是工業化財富滾存的結果。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不是通過工業化的財力積累,再經過經年累月的堆積而發展起來的。奢想依靠透支財政來使城鎮化實現“烏雞一夜變成金鳳凰”,顯然是“背離邏輯”的。
國際社會普遍看好我國城鎮化的原因,在于其對釋放投資產生的巨大渴求,這對目前普遍低迷的國際市場具有吸引力;國內省市熱衷城鎮化的原因,在于其覬覦中央政府可能實施的“第二個四萬億”政策,他們對飽食上一次中央政府的美食仍意猶未盡。正是這一邏輯的使然,國內建新城、造大城不絕于耳,各地比、學、趕、幫、超之風甚盛。
以提高廣大農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城鎮化發展,其本意是想通過科學有序的建設,一方面拉動消費和投資,實現帶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借助經濟發展與財力的增加,實現全國農民生活水平質的飛躍。但是現實狀況是,地方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舉債來進行。例如,完善城市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對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財政資金,目前地方政府的財力顯然不能承擔這巨額開支。
城鎮化設計權必須改革
前不久,《人民日報》曾詳述當前我國城鎮化建設存在的問題:一個年財政收入僅4億元的縣,欲打造成“東方迪拜”;一座年財政收入僅50億元的城市,要投資千億元造“古城”;西部一座缺水城市竟爆出要挖26個人工湖,最大的達10平方公里;北部一座新造的“大城”,大街上空空蕩蕩,花費數十億元建設的人造景點被拆除……時下,在“拉大城市框架,建設××新城”等口號下,從小縣城到省會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到沿海發達地區,造“大城”的沖動正加速上演。文章尖銳指出:“我們究竟需要一條怎樣的城鎮化道路?”
的確,我國城鎮化到了該解決“設計權”這個樞紐性問題的時候了。僅就“設計權”而言,城鎮化的設計觸及三方利益:中央、地方及宏觀指導部門。從戰略考慮,我國城鎮化的設計權應該分為:戰略設計、發展規劃、產業指導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的設計,應該由三個主體來執行:中央政府負責戰略設計;地方負責發展規劃,宏觀指導部門負責產業指導。這樣,各盡其職,各有側重,避免交叉,互補互益。
對中央政府而言,今后關注的重點,應是國家在國際戰略的定位以及國家在戰略層面對大區域的掌控,即“戰略發展大綱”,而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規劃設計問題;地方則應專注于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設計,并且要在當地人大的監督之下,按嚴格程序履行;而像國家發改委這樣的宏觀指導部門,應將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國際產業發展的新動態,不斷提出新的產業政策指導建議,為地區或行業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參考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指導部門在未來應起到承上啟下作用。
城鎮化應法制化
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舉世公認是最快的,但必須承認未必是最好的。這里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我國經濟發展的效率未必是最高的,例如我國在資源利用率上始終處于低效率的區間;其二,是指我國經濟發展的決策效率未必是最好的,例如中央在城鎮化上重點講民生、講內需、講拉動,地方的城鎮化則重點喊土地財政、喊擴權、喊利益重構。這種矛盾已經反映在經濟、金融、財政、行政等各個不同的領域。
因此,必須有法制的概念介入,從設計到決策,再從決策到執行,必須將決策的完整鏈條都納入法制化軌道。
為何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國城鎮化建設從規模上講將是亙古未見的,其總投資將超過200萬億元,從建設的時間跨度講,將超越30年,歷經幾代人。如果政府力圖“鐫刻自己的烙印”,那么如此長卷到最后,究竟是一幅構思完整的偉大的不朽畫卷,還是一幅巨大的“涂鴉”長廊?甚至若無序發展,最終能否完成這項工程都將難料。
城鎮化建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升級版母版。對城鎮化建設的“系統風險控制”應該關注,莫讓經濟發展因城鎮化建設無謂成本的過高堆砌而最終受到羈絆。
作者系中國城鄉一體化建設專家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