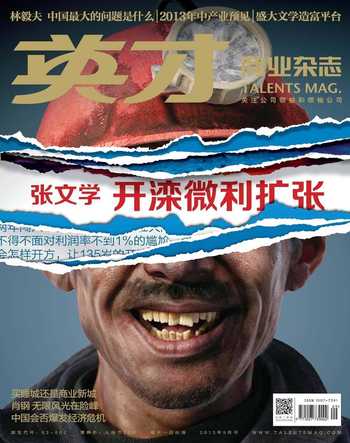林毅夫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趙福帥


自2012年6月從世界銀行卸任回國,林毅夫便陷入了各種爭議與質疑的漩渦。
“中國經濟仍有潛力保持20年增長8%”、“中國應該堅持投資驅動,不能轉而依靠消費”……后者在輿論眼中,則與吳敬璉“用強勢政府海量投資支撐高速度增長的發展路線已經走到了盡頭”的觀點針鋒相對,而被瘋狂炒作。
在接受《英才》記者專訪時,林毅夫對此很是無奈:“現在的人習慣用微博,看標題,然后對標題進行批判,好多標題并沒有很好地總結我的思想。”
要理解林毅夫的諸多觀點,首先要了解他的思想體系——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長期致力于人類發展命題的求索:占世界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走向繁榮。實際上,二戰后的60多年,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績效令人失望。全世界只有中國臺灣和韓國兩個經濟體從低收入躍居高收入;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其他絕大多數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二戰后,后發國家普遍認為,要擺脫貧困就必須發展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大產業,這實際違背了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當時被認為最沒有希望的一些東亞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導向戰略,從勞動密集型中小產業起步,取得了持續快速的增長。
到1980年代,主流看法又認為,后發國家要擺脫停滯與危機,必須采取休克療法取消各種扭曲,迅速建立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體制,結果卻是經濟停頓、政治動蕩;中國、越南等采取“比計劃經濟還糟糕”的漸進的雙軌制改革,雖然積累了分配、腐敗等問題,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
2008-2012年世界銀行任職期間,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逐漸成熟:各國產業發展要以市場為基礎,遵循比較優勢。根據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原理,這樣能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與積累,結果要素稟賦結構與比較優勢不斷升級,產業結構便不斷接近發達國家。這個過程中政府不能無為而治,而應因勢利導,解決外部性與協調性問題,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
林毅夫還配套提出了可操作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雙軌六步法”。
中國的產業選擇
《英才》:你認為哪些國家的哪些產業是中國新的比較優勢所在?
林毅夫:作為學者,我提供的只是一個分析框架。在這個框架中,必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已有的產業已經在全世界最前沿了,那只能自己發明新的技術或產品;另一種是現有的產業還沒達到前沿水平時,去找更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參照來進行技術、產品創新。從歷史經驗看,成功的追趕國家通常是找現在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來講是兩到三倍、過去二、三十年發展很好的經濟體作為參照,他們的產業很可能就是追趕國家的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
如果一個國家二三十年發展都很快,就代表這個國家的產業基本符合它的比較優勢。這時它的資本積累和工資上升也很快。原來符合它比較優勢的產業很快就會變成它的夕陽產業,它的夕陽產業就是追趕國家的朝陽產業。
到底要選擇哪些產業,這不是政府決定的,主要看私營企業是否有積極性進入。所以第一步就是通過這個框架找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樣既防止政府太冒進,也防止各種利益集團尋租。
第二步,要看是否國內有民營企業進入這個產業。如果有,那為什么你的要素生產成本比參照國低,卻不能與之競爭?一定是交易費用高。交易費用高的原因是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環境,還是人力資本不足?國家和企業就可以共同來消除這些瓶頸。
第三步,有些產業可能國內企業還沒進入,那為何不把參照國的夕陽產業吸引進來?他們一定有積極性利用國外較低的要素生產成本,政府可以把他們進入的瓶頸消除。另外,有些產業、產品20年前根本不存在,參照國可能沒有這種產業。但如果已經有民企自發地發現這種機會,表現出盈利能力,國家也應該幫助排除交易費用的限制。
《英才》:后發國家總是承接先進國家放棄的產業,會不會永遠落后?
林毅夫:實際上不會。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按比較優勢發展都可以創造最大的剩余,這是相同的。但后發國家的資本回報率一定高于發達國家,因為資本相對短缺,因此積累資本的積極性和人均資本的增速會高于發達國家。
《英才》:按你的說法,光伏不就是朝陽產業嗎,前幾年發展很火,政府因勢利導,有大量補貼、幫扶,結果出現這樣大的問題。怎么解釋?
林毅夫:基本上我只是講對外部性的補償,我從來沒有講補貼,也沒有保護。如果一個產業要補貼才能生存,它就違反了前面講的要符合比較優勢。有一點補貼也不過是對外部性的補貼。因為總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可能失敗,別人就能避免同樣的錯誤;他也可能成功,就有很多人跟進,他沒有壟斷利潤。
國內對光伏產業有些說法,常講跟世界是在同一起跑線上,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可以是三歲的小孩,也可以是十八歲的小孩,哪個跑得快?所以即使在同一起跑線上,你的進入還是違反比較優勢的。其實并沒在同一起跑線上。
《英才》:在企業界,大家都非常關注政府出臺的各種政策。
林毅夫:企業當然會追求他們的利益,一種途徑是提高效率,一種是增加政府的租金。所以我講的因勢利導框架,一方面是要避免政府冒進,二方面是避免企業尋租。
沒有一用就靈的理論
《英才》:關于新結構經濟學,熱議的一個焦點是政府與市場,可能有些各說各話?
林毅夫:現在有人過度強調市場,有人過度強調政府。強調市場萬能的就會認為我過度強調政府,強調政府萬能的就會認為我過度強調市場。但我覺得成功的國家,實際是兩只手都在用。
從二戰到現在,只有13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達到每年7%或更高,且維持25年以上。他們有兩個共同特征,一是市場經濟或走向市場經濟,二是都有積極有為的政府;從二戰到現在,180個經濟體長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他們普遍的是,一段時間過度強調政府,一段又過度強調市場,在兩者間不能平衡。
政府可能好心干壞事,過猶不及,但也可能不及猶過。認為政府都是壞的,最好不要有政府,就像新自由主義,那就是不及猶過。
《英才》:有觀點質疑你的理論可能成為政府扭曲市場的工具,而你的書里具體談如何避免政府做不該做的、或該做的沒做,談的少,為什么?
林毅夫:其實任何理論都可能被誤用。好多爭議實際是沒有好好看我的書,他是拿他的框架去套。只要聽到講政府,馬上就反對;另外一批人,你一講市場,他就開始反對。
如果我談政府的作用,就可能導致政府犯錯;那你過度談市場,也可能導致市場犯錯。任何國家必然存在體制和機制問題。我們看到的理論模型都是理想的模式,連發達國家也沒達到。而且理論是不斷被揚棄的,發達國家的理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英才》:有觀點認為你的理論是建立在善人政府的預設上。
林毅夫:我的理論并不是建立在一個善人政府的基礎上。任何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最大的目標是什么?我想就是長期執政,進而青史留名。我讀了那么長的歷史,也跟那么多中外領導人有直接接觸,我確實沒看到一個領導人說,當領導人的目的是把國家毀掉。
但是經濟發展沒有現成理論一用就靈,領導人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可能好心辦壞事。成功了就像鄧小平,青史留名了。但更多領導人在瞎子摸象過程中,實際經濟發展差了,他又要長期執政,怎么辦?只能加強控制,結果經濟就會更差。
《英才》:各級官僚未必這樣,他們可能就是想升官發財。領導人力量大,各級官僚的力量可能更大。
林毅夫:所以要對官僚體系有一個考核制度。好的領導人就是要懂得抓住大的方向,同時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來調動官僚體系。
問題根源不在投資
《英才》:現在大家都愿意投資房地產,這能滿足中國產業升級的需要嗎?
林毅夫: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況,我們確實需要調控,因為大部分國家出現金融危機都跟房地產泡沫有關。為什么有這樣一個泡沫?我覺得相當大的原因跟我們的金融體系有關,再加上我們對產業升級也沒有比較好的因勢利導。
尤其這輪房地產價格飆升是在2008年之后。我們當時推行4萬億的反周期政策,實際是以貨幣政策為主,不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因為政府提供的13不到,23靠信貸。
然后就出現“貸款創造存款、存款創造貸款”。如果項目是1億元,4年建成,我們批準后一次性把1個億都撥到賬下。可是第一年只用2500萬元,剩下7500萬就存在銀行。這就有個問題,儲蓄利率非常低,貸款利率非常高。比如貸款利率是7%,第一年只用2500萬,但必須為整個1億按7%付利息,那2500萬的貸款利率就不是7%而是28%了,夠高吧。這樣就變成鼓勵讓企業去做短期的投機,房地產是短期投機非常好的方向,回報很高,尤其在泡沫沒破裂前。
所以我一直主張,現在面臨一個周期性下滑,確實需要政府發揮積極的反周期作用,但更多要靠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同時金融體系的管理要改善。我們2007—2011年,GDP增加20萬億,貸款增加30萬億,儲蓄增加40萬億。儲蓄增加怎么比GDP增加多一倍?那就是“貸款創造存款、存款創造貸款”。
《英才》:這次“錢荒”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認為中國不會出現東亞那樣的金融危機,或者發達國家現在這樣的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我們有那么多外匯儲備。中國現在的危機主要是流動性的危機,并不是銀行的資產呆壞賬非常高,這跟由于銀行呆壞賬高造成的對銀行體系信心不足有本質差異。而且我們資本賬戶也有控制,所以即使有些問題,也不會變成大量擠兌或資本外逃。
我想錢荒有點像打預防針,當然會痛一下,可能還發燒一兩天,但這樣就給經濟體系中的一些問題比較高的預警,然后進行必要的改革。
《英才》:金融體系改革,政府最主要得考慮哪些問題?
林毅夫:銀行體系改革很重要的一項是信用管理體制的改善。國外一個貸款批準后,是按投資周期給錢,而不是一次性都撥給。第一年2500萬到賬上,支付2500萬的利息。但其他7500萬還是承諾,國外一般是0.25%-0.3%的利率,我們卻是按利息收,7%以上,差20-30倍。
金融體系要改革的最主要問題是金融結構。我們到今天70%的生產活動還是中小型農戶、制造業服務業的中小企業。他們創造就業最多,所在行業基本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投資回報率也最高。但目前以大銀行、股票市場為主的金融結構中,他們得不到金融服務。
《英才》:你認為中國經濟應該堅持投資驅動,不能過早過多刺激消費。但外界對此有很多質疑。
林毅夫:有人看到別人怎么說,就跟著怎么說。另外沒有分析問題根源,把中國的問題都認為是投資造成的。
作為發展中國家,維持經濟穩定、快速、可持續發展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是我國的首要任務。提高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目的,短期內增加消費也能增加經濟增長,但經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是投資而不是消費。沒有投資,就不會有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結果勞動生產率不能提高,增加消費成了無源之水,繼續增加就只能靠舉債,越積越多,危機就來了。
我國確實需要深化改革開放,解決雙軌制遺留的各種扭曲,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我國的投資在如何避免潮涌現象、產能過剩、低水平重復等也有許多改善空間。但放棄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改為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顯然是頭痛醫腳、因噎廢食、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張。
《英才》:這背后是不是收入分配的問題呢?
林毅夫:我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分配的問題。收入分配改善,消費會增加一點。但并不是說要以消費為主。發達國家以消費為主都出了問題,我們能以消費為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