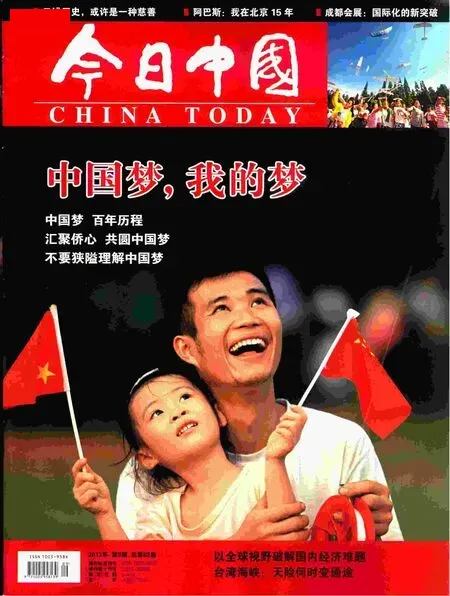饞宗公案
半窗靈鼠齋
老派中秋
小辰光福州路上三樣東西,最討我歡喜:書店,臺風和月餅票黃牛。喜歡臺風,是因為怕熱,這個擱起來不講,黃牛和書店其實是一件事情,家里多出來月餅票,我就拿給黃牛,打個折扣拿了現錢,直接沖進古籍店,買新印的舊書。臺風今年一直不來,有點掃興,其他兩樣,書店好比是麻雀、鴿子、鷯哥、斑鳩、鵪鶉,蹲在這個地方一動不動:黃牛呢,像是大雁、燕子、天鵝、拍賣行從業人員、候鳥,時節一到就出動。現在這個天氣,即使外面再熱,黃牛伯伯也是不能退縮的,都要出來了吧,想你們啊親。
很長的一段時間,家里每逢中秋,各種月餅票紛至沓來,吃不掉發愁,后來父母退休,我辭去公職,每年送月餅的只有忠心耿耿、20年跟在屁股后面的設計師小朱。于是再也沒有和票販子們打交道的機會,就這么一盒杏花樓,自己要留著過節。
吃客,或者按照時髦的說法,炫食族,現在的情形,是人人怕病,又都一怕吃苦,二怕花錢,所以不管吃月餅的,還是做月餅的,都深惡痛絕一個甜字。月餅常常被拿出來示眾,特別是傳統的豆沙、五仁、白果之類,養生達人振振有辭,誰誰吃月餅,糖尿病了,急性壞死性胰腺炎了,諸如此類,我就只好搖頭不語,對于月餅,就是吃這一口甜,這是我比較老派的思路,那些潮來兮的廠家,把月餅做淡,里面加進去七七八八的海鮮也好、水果也好、冰沙也好,一概讓人覺得:這,不是月餅。
日本的點心,非常傳統的老店鋪,源吉兆庵之類,一定是甜得非常純粹,因為它們沿襲下來的,就是明朝的味道。而且點心要做得品相好,糖這種東西,太關鍵了,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可塑性好,形狀色澤可以諸般變化,這一類全世界都公認的尤物,一邊是防腐,一邊是審美,兩手抓兩手還都挺硬,輕易去做改變,實在令人嘆惋。要是五六百年一家老派點心店,突然貼張告示說對不住大家,今天賣的糕點,我們要改口味,本來是豆沙的,即日起改放象拔蚌,顧客會答應么?玻璃窗還想不想要?指責月餅甜的時尚寵兒們,費勁心力花光了半年的積蓄漂洋過海的去巴黎,除奢侈品以外,也會對Laduree的馬卡龍趨之若鶩,站那兒排半天隊你吃的是哈么事,一大口糖拌杏仁粉而已。
怕甜,少吃一口就好,但是那一口,得地道。
我心中地道的上海中秋節,40年以來沒有變化,要有幾個老店的月餅,廣式蘇式倒無妨,應景么還是廣式,因為看起來富貴氣一些,有一鍋芋艿老鴨煲,懶的人也盡可以去廣式燒臘店買烤鴨,家人團聚之時,我要給侄女買一根全世界最大的棒頭糖,她現在還小,只認得這個。
下來就是上海灘最嗲的蘇式月餅的時間了,對,西區老大房的鮮肉月餅。愚園路或者南京西路木齊路,幾個老大房烘烤鮮肉月餅的攤點前,一年四季都有人排隊,一到中秋,排隊的人不亞于靜安寺買凈素月餅的善男信女們,鮮肉月餅,分明是吃貨們的一種信仰。什么最性感?是爐子上觸目驚心地寫著“當心燙痛”這4個字,是拿到手里欲罷不能的輕軟和扎實,更是齒牙間湯汁和肉糜的完美融合,酥皮那就更不談了,宋詞里輕解的羅衫。
顧家西瓜
我讀小學四五年級時,墻壁上老是掛著一幅李清照畫像,銅版紙印,1980年代中期時興掛歷,我每天看這個瘦女人,穿著一身白衣服,站在菊花叢前低吟。鼎鼎有名的薄霧濃云愁永晝,就是那個時候背出來的,每天路過看一眼,那還背不出來?
這幅畫的作者叫“顧炳鑫”,他是誰?我肯定不認識,把畫掛出來的父親也不認識,父親認識另外一些畫家,以后我會慢慢寫,例如沈柔堅或者華三川,但是這位字畫都修長清朗的顧先生,不認識。
我那時已經開始正式地拜了師傅學畫畫,山水,在家里臨徐北汀和潘韻南北兩家的課徒稿。山水,實在沒有人物好白相,小孩子對所謂境可奪人之類,不明覺厲,陌生得很,空下來反而喜歡看張大千、謝稚柳的美人,月餅盒子上任率英的嫦娥也照貓畫虎畫一張,當然畫不像,所以對人物畫家尤其尊敬,墻上每天念叨名字的顧炳鑫,簡直就是大神,人生中第一個偶像。
某天我又對著這幅畫出神,低我兩年級的弟弟跑過來,說顧炳鑫,我認得的。我說豈有此理,你這么點大的小孩子,每天就知道中午拿一毛錢去門口小煙紙店買桃板吃,怎么會認識這么了不起的畫家,去一邊擦鼻涕去。他有點委屈了,說真的認得啊,班上同桌好朋友姓顧,那天問我曉得顧炳鑫伐,我說曉得曉得,我們家墻上掛著個柴爿一樣的女人,畫這幅畫的叫這個名字,我哥每天叨叨叨要念的。同桌說那是我爺爺。告訴你,我到他們家都去過得來。
我于是拿出自己的一毛錢,拼上弟弟的一毛錢,請他吃高端洋氣有檔次的辣橄欖,桃板之類先放一放,意思你能不能也帶我去看看顧炳鑫。他被辣橄欖嗆得四面找自來水龍頭,幾乎痛哭流涕地答應下來。第二天我們就去了,原來這么近,就在愚園路四明新村,從我愚園坊的家,出門過馬路,1分鐘也不要。1980年代,四明新村很空曠,人也干凈,每家宅子前,植著花草和高高大大的樹,記得走進去沒幾排,就是顧家。正是盛夏,天就跟現在一樣的熱,看見個老先生,汗衫短褲,在房間里走跳,個子不高,人很精神的樣子。
我們仗著是小孩子,不管不問地就沖進去看,原來老先生在畫一幅很大的畫,畫桌不大,房間也不算寬敞,所以畫兩筆,就要把畫拿遠了看效果。現在當然很輕松,畫家都是把一整堵墻都貼上鐵皮,弄點磁鐵一吸就好,便捷極了。那時候,再大的畫家,遠看自己作品,都是難題。記得陸儼少先生是敲兩個釘子,拉根線,上面夾很多夾子,和晾衣服相類似。顧先生呢,他就是直接把畫放在對面的一個大櫥上,櫥頂上放兩塊小鎮紙,壓住了,然后退到畫桌前看。
這時電風扇嗡嗡嗡,老是把畫的邊角吹起來,我就大著膽子過去,看見櫥邊有兩只大西瓜,抱過來,一邊一個壓妥帖,顧先生點點頭,繼續看畫,畫畫,我們三個就擠在邊上,也看。等他收了筆墨,我直別別問,依就是顧炳鑫?他指指桌子上的信殼,果然上面寫著“顧炳鑫啟”四個字。看到我臉上快活的表情,老先生說,小朋友慢些走,阿拉一道吃西瓜好伐,對,就是櫥邊那個,剛才替我壓畫的西瓜,還要謝謝你幫的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