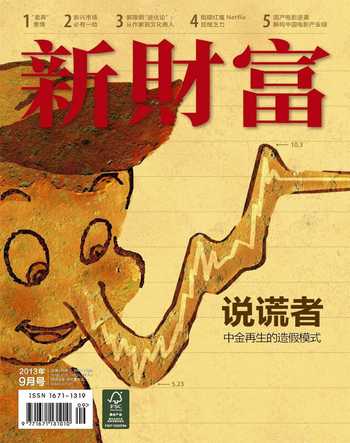新興市場必有一劫
陶冬
美國先陷入危機,但也率先復蘇。危機打殘了歐洲,逼瘋了日本,現在輪到新興市場了。雖然暫時看不到亞洲金融危機式的經濟全面崩盤,不過伴隨美國的QE退出,在去杠桿的收縮中,新興市場會左支右絀,慢慢陷入泥淖。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聲勢浩大、長達十年之久的新興市場熱開始散去,危機的陰霾越聚越深。
第三世界,曾是世界的不毛之地,每隔數年便爆出匯率危機、債務危機或軍事政變。不過近十年,它們就風光了起來,經濟起飛,股市興旺,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沒有令它們凋零,反而使之變得更強大、更具活力。好事者從BRIC(金磚四國)開始,為新興市場起下各種名字,編織出一個又一個神話。
三大要素,打造出了新興市場的神話。首先,生產線轉移、產品外包,為以中國為首的一批新興國家帶來了就業。這個罕見的歷史性機遇,制造出東亞的騰飛,也為南亞地區經濟提供動力,產生出內需。其次,中國需求為大宗商品帶來超級牛市,成為拉美和非洲經濟的轉折點,令它們的經常項目大為改觀,由此經濟出現生機。第三,全球流動性泛濫,利率降至不可思議的超低水平。低利率使重債國的債務負擔大減,熱錢涌入使經濟建設和消費變得可能。
生產線轉移、商品需求熱和資金涌入三大要素中,前兩個屬基本面因素,但是第三個要素資金涌入則屬虛火。海外熱錢流入令當地貨幣升值,拉低通貨膨脹,央行有空間減息,更多熱錢流入本國貨幣債市,形成自我循環。更有甚者,發達國家央行近年大肆擴張貨幣發行,但是銀行并未將流動性中介至本國企業或個人手中,大量游資涌入新興市場,炒高了當地的資產價格,推高了當地的借貸水平。
從純基本面因素看,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結構、生產率并未見明顯改善,只是它們的借貸成本由5年前的12%變成5%,分攤到30年的國債上,財政可持續性自然大幅改善,基礎建設紛紛上馬,內需故事被吹噓為與發達國家“脫鉤”的本錢。
其實,新興市場從來沒有與發達國家脫鉤,盡管新興國家對發達國家需求的依賴度有所下降,發達國家的流動性仍是它們跳不出的如來手掌。新興經濟熱,根本就是全球超高流動性、超低利率的產物。
一旦美聯儲打算放緩QE的步伐,潮水退下,裸泳者自然浮現。新興市場中,有一批高杠桿、高貿易赤字、高財政赤字國家。這些“三高”國家,資金呈收支赤字,需要海外資金不斷流入來填補資金短缺。一旦海外貨幣環境有變,資金外流,則貨幣供需失衡,匯率下挫,觸發更大的恐慌性資金外逃,央行被迫加息來穩定市場情緒,其結果是經濟形勢迅速惡化,導致更多資金出走避險。
值得一提的是,各國央行在處置資金出走上,均有政策失誤。資金外逃初期,它們處在心理否認狀態,拒絕承認本國經濟有問題,更多指責投機者。當匯率暴貶時,要么推出不合時宜、效果不佳的行政干預,要么大幅加息令本國經濟雪上加霜。政策不當,令資金信心更加脆弱,加速資金外流。
當然,盡管“三高”國家遭遇資金外逃、股市浴血,筆者暫時還看不到亞洲金融危機式的經濟全面崩盤。新興國家今天的外匯儲備已非當年吳下阿蒙,銀行體制大體健全,匯率也有浮動空間。短期來看,這是信心危機,而非國際收支危機。
但是,美國的QE退出才剛剛開始,估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流動性的緩慢收緊,勢必減少甚至逆轉資金流入,國際收支逐步弱化,內需必須收縮,經濟基本面轉差。同時,不少國家和企業近年趁美元債成本低而大肆舉債,進行基建或海外并購。現在利率升、匯率跌,一批企業債務違約只是時間的問題。盡管危機短期不至爆發,新興市場普遍面臨借貸杠桿過高的問題。在去杠桿的收縮中,筆者相信債務危機、經濟危機會逐步深化。
縱觀戰后世界經濟史,美元強勢下新興市場例必出事。美國經濟復蘇、房地產復蘇之下,美聯儲貨幣政策緩慢收縮勢在必行,其結果是美元匯率的持續強勢。上一次美元連年走強始于1992年,這個大環境下,墨西哥危機(1995年)、亞洲危機(1997年)、俄羅斯危機(1998年)、阿根廷/巴西危機(2001年)先后爆發。
這場全球危機,美國乃始作俑者,卻又是贏家。雖然美國先陷入危機,但也率先復蘇,危機打殘了歐洲,逼瘋了日本,現在輪到新興市場了。筆者認為,新興市場危機目前只是序曲階段,去杠桿中新興市場會左支右絀,慢慢地陷入泥淖。美國人又笑到最后。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或補充,
請發郵件至xincaifu@xcf.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