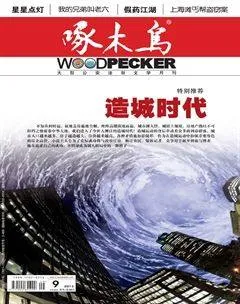神仙之鳥灰喜鵲
韓開春

時莊人管灰喜鵲叫“三喳子”,這跟它“喳喳喳”的叫聲有關。它的模樣像極了花喜鵲,都有一條長長的尾巴(這幾乎成了它們區別于其他鳥兒的標志),要不是個頭略微小點兒,顏色稍微有點兒區別(一個黑白分明、一個灰白相間),在一般人的眼中,它們幾乎就是孿生兄弟。
但灰喜鵲和喜鵲確實不是同一種鳥,雖然都屬雀形目鴉科,名字也很像,卻不是同一屬種。喜鵲屬于“鵲屬”,真正跟它關系近的,是一種拉丁學名叫Pica nuttalli的黃嘴喜鵲,除了嘴巴的顏色不同之外,其他部位都跟喜鵲沒有兩樣。而灰喜鵲則屬于“灰喜鵲屬”,在這個屬種里,只有它獨苗一根。所以,灰喜鵲和喜鵲的關系,不是親兄弟的關系,至多算得上是叔伯家的堂兄弟。同樣相近的關系,在我老家常見的鳥類中,大約還應該加上烏鴉,雖然它們的名字相差很遠,人們對它們的喜好程度也相差甚遠,但它們都屬于鴉科。
堂兄弟三鳥中,人們最喜歡的是喜鵲,原因是它能給人們報喜,聽到喜鵲叫,好事就要到;最討厭的是烏鴉,同樣是叫聲,人們卻認為它帶來的是晦氣,老鴰一叫,壞事來到;而灰喜鵲處在中間,它既不會給人帶來喜訊也不會給人送來噩耗,它那“喳喳喳”的叫聲對于人類來說毫無意義,所以人們對它的態度是既不特別喜歡也不特別厭惡就很好理解了。
人類中,名人大約是活得很累的一群人,不管是好名還是惡名,一旦出了名,就成了眾矢之的,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惡名自不必說,即使是好名,得到的也未必全是好處。好處自是盡人皆知,能得到許多現實的利益,但是壞處也顯而易見,至少你再想過安安靜靜沒人打攪的生活是萬萬不能了,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名”這個東西說到底也是把雙刃劍,真正活得瀟灑的反倒是那些默默無聞的平頭百姓。鳥類大抵也是如此,好名聲也好,惡名聲也罷,太多地吸引了人們的眼球,總會不得安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鴉科三兄弟中,灰喜鵲反倒是最幸運的一個了。
因為平凡,所以自在。灰喜鵲在莊上的遭遇正是如此,因為不出眾,所以不受人們關注,人們對待它們的態度,就像對待莊上的那群小屁孩兒,上東下西,隨便你怎么去野,只要不干出上房揭瓦、上床撒尿的過分事情來,基本上沒人去管。所以它在莊上出現的幾率,僅次于麻雀,屬于第二多的鳥類。你看它們三五成群甚至十幾只一大伙,一出動就是一大幫,一呼啦飛到東,一呼啦飛到西,唧唧喳喳,呼朋引伴,好不瀟灑快活,全然不像喜鵲那樣要么形單影只,要么夫婦二人,雖然受到人們的歡迎,卻也小心翼翼,更不像烏鴉,在莊上一露頭就要遭人唾罵、被人驅逐。
灰喜鵲在我們莊上是衣食無憂的,它的食性很雜,跟大多數的鳥類差不多,既不是堅定的素食主義者,也不是如伯勞、老鷹之流非肉不食,五谷雜糧、草籽樹果、螞蚱青蟲,莫不是它口中之食。所以你想餓著它,實屬不易。當然它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它的食譜中就有兩種東西是其他鳥類所不敢或不愿意碰的:一種是椿象,時莊人稱之為臭鱉子的小蟲,渾身散發著難聞的刺鼻臭味,不要說吃,就連碰了以后都會令人作嘔,就這樣的一種小東西,卻是灰喜鵲的美食,不知它怎么吞咽得下;另一種是松毛蟲,渾身長滿了長長的毒毛,沾到皮膚上就會起一片水皰,火燒火燎地疼痛,這樣的一種小蟲,光那身鮮艷的顏色就是一種警告:“別惹我,惹我沒有好下場。”事實上也是,大多數鳥兒見到它們都退避三舍,惹不起,咱躲得起。灰喜鵲可不信這個邪,你不讓吃我就偏要吃你試試。我就親眼見過一只灰喜鵲在莊子西頭的那片松樹林里叼起一只肥嘟嘟的松毛蟲,在粗糙的松樹皮上左蹭右蹭,不一會兒松毛蟲身上的那身令人望而生畏的毒毛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成了灰喜鵲腹中的美食。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護體的金鐘罩,我就有破你的一指禪。從這點來看,灰喜鵲還是個聰明的鳥兒,并不一味地莽撞行事,懂得開動腦筋來解決問題,頗像它的堂兄弟烏鴉。
能體現灰喜鵲聰明的,還有一件事,就是它有儲糧過冬的習慣。深秋時節,如果你用心,一定會時不時地發現一兩只灰喜鵲銜著楝果或是螞蚱之類的食物,悄悄離開大部隊,鬼頭鬼腦地四處張望,在確信無人跟蹤之后把叼著的食物塞進瓦縫或者墻洞中收藏起來,等天寒地凍食物匱乏之際,它再飛過來取出果腹。所以,在莊上寒冷的冬天,你偶爾會在下雪天發現一兩只凍餓而死的麻雀,卻很少能看到因凍餓而死的灰喜鵲。
偶爾,這個可愛的家伙還會客串一把小偷的角色,就連干這樣偷偷摸摸的事兒都是集體行動。小時候生產隊的倉庫就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三四只灰喜鵲在屋外蹦蹦跳跳,看似在玩耍,實則是在刺探軍情,起的是個偵察兵兼哨兵的作用,在確信沒有危險后,它們會發出一種信號,讓同伴們趕緊入室大快朵頤。這樣的舉動,常常會令看到它們的人忍俊不禁,覺得它們真像一群又可笑又可氣的小無賴。
按說,這樣的一群聰明且吃穿不愁的鳥兒在我莊上過的是一種神仙般的日子,但是神仙偶爾也是有苦惱的。如果這個苦惱的根源是來自一個七八歲的孩童,那么,這個“神仙”有時是會受不了的。我七八歲的時候,就有這么一次讓它們很失面子。
那天,我們家翻蓋廚房,廚房的屋頂是用麥秸蓋的。那時,鄉間的廚房大多是草頂,極少見到有瓦頂的。草屋的好處是冬暖夏涼,不足之處是過段時間就得換草。蓋房的時候有人專門往上面扔草把,有人專門往上面送泥,還有專門和泥的,當然屋頂更少不了人鋪草,因此,請了好多的人,很熱鬧。
中午時分,正在玩泥巴的我忽然發現鄰居家的屋角露出一截灰喜鵲的尾巴,一向就對小動物特別感興趣的我突然心生奇想:何不把它捉來玩玩?便一個人躡手躡腳地順著墻根摸了過去。可能是我的動作太輕,灰喜鵲居然一點兒都沒有察覺危險已經降臨,當它的尾巴落到我手中的時候,它想逃已經為時太晚了。
這一幕讓屋頂的大人們看在眼里,他們除了大聲喝彩外,更多的是驚訝。他們說,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小的孩子赤手空拳抓住一只大鳥。于是,在那個缺少娛樂的年代,在那個相對閉塞的鄉村,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這一“壯舉”就成了大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在孩子們的眼中,我也因此成了“英雄”。
可我這樣的“英雄”舉動是建立在這只灰喜鵲的痛苦之上的,之后的幾天里,無論我想什么辦法,它都不肯進食,我把食物塞進它嘴里,它也給吐出來,整整兩天,它拒絕進食也拒絕喝水,到了第三天,它終于抑郁而死。我清楚地記得,它的眼是睜著的。很多年之后的現在憶及此事,我還在想:它到死都不瞑目,說明它心有不甘。會不會是覺得栽在這么小的一個孩子手里,對它來說是奇恥大辱?或許,它真的是給氣死的。
或許,那只灰喜鵲真是大意失荊州,可這一失足卻成了它的千古恨。好在,之后它們再也沒給莊上的其他孩子成為這樣“英雄”的機會,它們的生活也并沒因此受到任何影響,它們在我們莊上繼續快樂似神仙,這樣的結果多多少少減輕了一點兒我心中對它們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