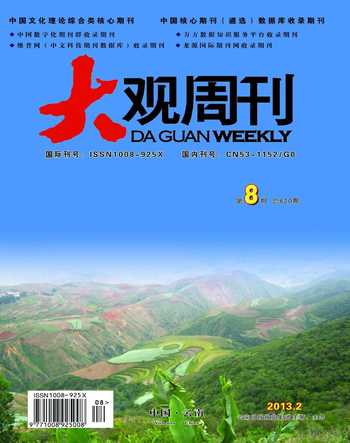對自然資源用益物權問題的一些思考
嚴馳恒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布局并作出全面部署,強調要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及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等一系列生態文明制度。制度建設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而法律角度的研究恰恰能為其提供理性層面的建議。
依據我國《礦產資源法》的規定,我國對于礦產資源實行單一的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正是由于在我國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屬于國家,所以《物權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將采礦權視為一種用益物權,而立法之所以如此定位,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土地和礦藏等自然資源的有序開發和利用,保障權利人履行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義務。
正是基于上述對于采礦權乃國家所有、用益物權的定位,我國才相應地實行了采礦權的有償取得制度,根據國務院《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第九條和第十條的規定,在我國依法取得采礦權,一般而言須繳納采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價款。當然后續還包括礦產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等。
眾所周知,礦產資源的兩大特征乃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也就是說國家出讓的供特定人開采的礦產資源在經過開采后就不復存在了,對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都是一次性的。但根據物權法的精神,用益物權是一種限制物權,即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對標的物進行支配,權利人并沒有完全的支配權;而且用益物權是一種有期限物權,有一定的存續期限。并且筆者認為,所謂用益物權,標的物必須具有能反復使用的特性,否則立法就沒有設定用益物權的必要了,因為在使用后連所有權客體都消失了,還談何所有權、用益物權!這樣看來,采礦權就很難稱其為用益物權了,首先,在采礦權行使中,用益物權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不得破壞準許開采范圍以外的礦藏及維護生態環境上,而對于所準許開采的礦產資源,似乎是沒有限制的,采礦權人事實上取得了近乎所有權人的地位,可以任意處置;其次,采礦權的存續期限也無從談起,采礦權作為一種權利,其客體應是所開采的礦產品,但礦產品一經開采使用便不復存在,所謂的存續期限實際上只是國家許可權利人開采的期限,這與用益物權作為有期限物權的含義截然不同;再次,經過開發后的礦區就沒有了再次開發的價值,當初用益物權的客體已經消失,即使可以再次使用,其價值也是大大降低的,那么又如何再次設定客體相同的用益物權呢?
綜上所述,國家在采礦權出讓的過程中出讓的并非物權法層面上的用益物權,而更接近于所有權。而將采礦權界定為用益物權,并以用益物權的標準去衡量、評估采礦權的價值,顯然是大大降低了采礦權及其背后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的價值。甚至可以說這種行為是一種變相的國有資產的流失,似乎也正是造成當前社會對于“煤老板”等采礦權擁有者爭議的眾多原因之一。
通過物權法的立法規制和建立自然資源的用益物權制度來加強對于資源和生態環境的保護的初衷固然是好的,但如何才能真正使制度、法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還需要有更務實的審視。就采礦權而言,首先,無論從理論角度抑或實務角度而言,采礦權的出讓都應定位為一種“準所有權”的出讓而非用益物權的出讓,即使實踐中由于各種原因的限制無法以所有權之名進行出讓,也不應將其簡單得視為用益物權而貶低其價值,對其法律性質、客觀價值都應有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樣一方面是基于礦產資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調整利益分配機制。其次,對于采礦權的價值應有更客觀、合理的評估,既要包括所出讓的礦產資源的合理價值(綜合考慮市場供求關系和礦產資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礦區土地、草原、林木、水源等的使用費,還要考慮國家在前期勘探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最后,對于采礦行為給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國家可以收取一定的環境治理、恢復費用,作為環境保護的基金。
我國在采礦權領域出現的問題在其他自然資源的使用、出讓上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和生態文明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從法律角度而言,通過立法建立切實反映自然資源市場供求關系和稀缺性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利用稅收等手段補償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對于環境的破壞,加強對于濫用自然資源和破壞生態環境的執法、處罰力度,才能保證自然資源的“等價有償”和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才能切實保護國家的自然資源所有權、保障公民的環境權益,也才能真正促進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