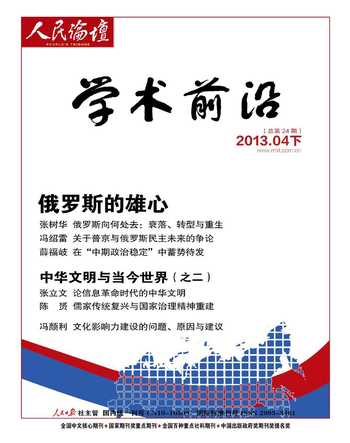政治強人語境下的獨特威權(quán)邏輯
摘要 近二十多年蘇俄民主政治的演進呈現(xiàn)一種在外交上先親西方、后與之疏遠,國內(nèi)政治先民主、而后又趨于保守化的循環(huán)。歷史的制約決定了當代俄羅斯民主政治既不可能太過于遵從西方民主,但也不會過于回歸前蘇聯(lián)的舊制。在當下的發(fā)展進程中,俄羅斯民眾還是傾向于選擇帶有威權(quán)主義色彩的政治強人普京,在實現(xiàn)強國目標的同時,創(chuàng)造性地探索屬于俄羅斯自己的民主之路。
關(guān)鍵詞 普京 俄羅斯 民主政治 政治強人
當代對于民主政治問題的討論,離不開一個重要國家,那就是俄羅斯。近一百多年世界政治的發(fā)展進程始終與俄羅斯人關(guān)于民主問題的理念與實踐息息相關(guān)。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改革政策,一度使人們對于蘇聯(lián)民主的前景寄予極大的希望。但是,此后蘇聯(lián)的崩潰和90年代的艱難轉(zhuǎn)型又使人們對于前計劃體制的轉(zhuǎn)型產(chǎn)生了極度的悲觀。一直到普京的出現(xiàn),俄羅斯的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峰回路轉(zhuǎn),似乎出現(xiàn)了國力的重新回升,但是圍繞著俄羅斯民主政治的取向,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nèi)社會都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有關(guān)俄羅斯民主問題的討論,不光是關(guān)乎從線性視角判斷,俄羅斯政治發(fā)展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而且,還關(guān)乎“普適性”和“多樣性”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①
俄羅斯的獨特政治邏輯
回顧最近二十多年來的蘇俄政治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獨特而又重復(fù)出現(xiàn)的邏輯。那就是,無論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還是普京擔任最高領(lǐng)導(dǎo)人期間的俄羅斯,都曾經(jīng)重復(fù)出現(xiàn)過每一任在上臺之初向西方開放和接近,但是到每一任的結(jié)尾時與西方疏遠乃至于抗衡的格局。
戈爾巴喬夫是以其弘揚全人類價值的“國際政治新思維”打開與西方關(guān)系的,但是,到他任期末了,在蘇聯(lián)面臨解體和深重危機的情狀之下,西方不愿出手相救。對此,俄羅斯人一反改革以來對于西方的好感,甚而以此見恨于西方。
1992年葉利欽上任時對西方一邊倒的政策獲得了西方的支持。但是到90年代末葉利欽下臺前夕,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已經(jīng)面臨著科索沃戰(zhàn)爭的危局。
新世紀初普京上任之時,高舉“重返歐洲”的大旗;同時,恰逢“9·11事件”發(fā)生,普京在中亞主動讓開兩廂,同意美國軍隊進入這個前蘇聯(lián)從未對西方開放過的勢力范圍。但是,到2008年普京第二個任期結(jié)束,由其搭檔梅德韋杰夫擔任總統(tǒng)期間,俄羅斯與西方關(guān)系的突出表征乃是俄羅斯與格魯吉亞之間的一場戰(zhàn)爭。
如果進一步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周期性變化之中,還幾乎同時出現(xiàn)了一個國內(nèi)政治取向的變遷,那就是每一位政治領(lǐng)導(dǎo)人的任期之內(nèi),都呈現(xiàn)先傾向于民主開放,后來又轉(zhuǎn)向政治保守化的趨勢。
在戈爾巴喬夫當政之初,積極推行民主化與“公開性”,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一時之美談和仿效對象。但是,到了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晚期,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曾經(jīng)主張民主與改革政策的領(lǐng)導(dǎo)人正在謀求由一個人獨自擔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總統(tǒng)的職務(wù),早年一起主張推行改革政策的政治精英也在此時從戈爾巴喬夫身邊逐個離去。
葉利欽執(zhí)政初期著力于打破蘇聯(lián)舊體制,建立市場經(jīng)濟,認同西方民主價值,目標是先民富而后國強,這當然就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但是葉利欽的激進冒險失敗,大國地位迅速隕落,休克轉(zhuǎn)型又使民眾備受煎熬,開放政治系統(tǒng)逐漸轉(zhuǎn)為“家族”、“寡頭政治”。民意由此迅速轉(zhuǎn)向平民主義,甚至開始懷念舊體制。
2000年, 普京上臺后,強調(diào)“人民團結(jié)”和強國路線,同時,也遵奉了自由主義的寬松和開放政策。此后,精英階層逐漸趨于分化,一方面是延續(xù)上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路線的右翼勢力;另一方面是圍繞普京中派主義政治的精英階層。轉(zhuǎn)折點發(fā)生在2003年,普京在三條線推進治理:懲處石油寡頭,開始收攏地方勢力,反對美國發(fā)起伊拉克戰(zhàn)爭。右翼精英對普京的抨擊由此開始,一直到2012年秋天以后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的出現(xiàn)。但是,與此同時,更主流的俄羅斯民意還是傾向于普京的保守主義政治路線。
可見,近二十多年蘇俄民主政治的演進是走過了三個圓圈。每一個圓圈都幾乎與每一位政治領(lǐng)袖人物的任期相伴始終:在外交上先親西方、后與之疏遠的同時,乃是國內(nèi)政治的先民主、而后又趨于保守化的這樣一種循環(huán),周而復(fù)始。
作為背景的俄國現(xiàn)代化進程
俄羅斯轉(zhuǎn)型進程中為什么出現(xiàn)了這樣奇特而又鮮明的政治循環(huán)過程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蘇俄式獨特的現(xiàn)代化進程可能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背景。從18世紀初到1991年這幾百年的俄國歷史,曾被稱為“世界歷史上的俄國瞬間”。
俄羅斯現(xiàn)代化的第一個高峰發(fā)生在18世紀初以后的彼得大帝至葉卡捷琳娜時期,在這兩位強人的光環(huán)之下,俄羅斯實行開明專制,面向歐洲,跨入現(xiàn)代化進程,俄國由此疆域擴大、國力增長,成為打敗瑞典等列強的歐洲大國。
第二個高峰發(fā)生在亞歷山大二世統(tǒng)治時期,1861年改革是當下受到高度關(guān)注的一次自由主義導(dǎo)向的改革,使俄國經(jīng)濟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走上迅速發(fā)展的道路,爾后的文化與政治也出現(xiàn)了創(chuàng)新和突破。但是,這一次改革的政治依托依然是政治集權(quán)的專制主義政體。
第三個高峰是蘇聯(lián)時期,以反西方的中央集權(quán)方式推動現(xiàn)代化,又一次打敗列強,取得二戰(zhàn)勝利,然后和美國平起平坐。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輝煌,從國家強大的角度,實現(xiàn)了一個民族的理想,但與此同時,國家的能量也趨于耗盡,社會的緊張度達到極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和生物體一樣,有它的生命周期。1991年的解體表明,它超出生命能量的限度,已經(jīng)用到極致,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樣通過強權(quán)聚集全社會的優(yōu)勢資源。②
概括地講,俄羅斯以前三個現(xiàn)代化周期盡管付出了沉重代價,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但畢竟使得原來的莫斯科公國成為雄踞一方的歐洲大國;到社會主義時期更曾經(jīng)讓世界耳目一新,以這樣一個反西方形象出現(xiàn),以一個反其道行之的獨特方式推動現(xiàn)代化,居然也成為世界數(shù)一數(shù)二的超級大國。這種歷史記憶在老百姓心目中難以泯滅,投射于普京身上,他就成為了強大國家的化身。
盡管蘇聯(lián)體制曾給百姓帶來相對穩(wěn)定、虛幻和真實并存的大國國民地位,但民眾對舊體制的缺乏活力和在東西方對抗中的落敗也非常清楚,知識精英對過時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有著巨大影響力。從政治繼承的角度而言,作為形式上繼承蘇共的俄共,觀念難有更新。雖然90年代晚期在一片凋敝的形勢之下,俄共甚至一度具有執(zhí)政前景,但是,在新世紀以后一個相對不那么意識形態(tài)化的政治文化氛圍下,較多民眾還是傾向于選擇具有威權(quán)主義色彩、但意識形態(tài)中性的普京。
在這二三十年中迅速形成的俄羅斯精英階層與中國的精英階層同中有異。相比之下,中國的新精英較多起于民間與草根,而俄國的新精英則較多來自前蘇聯(lián)的傳統(tǒng)精英,比如,共青團組織、國家強力部門、官僚系統(tǒng),包括知識精英。與一般人們所認為的中國的轉(zhuǎn)型相對比較穩(wěn)健,而俄羅斯的轉(zhuǎn)型相對較為激進的判斷可能有所不同,從邏輯上說,這一格局使得俄羅斯的社會轉(zhuǎn)型實際上有可能比中國保持更多的連續(xù)性,換言之,轉(zhuǎn)型之前蘇俄的社會保守方面可能更多地得以維持。另一方面,俄國精英在整個社會運作中起著關(guān)鍵作用,也比較傾向于民主自由主義,然而,這部分人始終是少數(shù)。大部分民眾仍然沒有從依賴國家支持的歷史記憶中走出,依然既傾向于主張各階層的平等,又仰仗于威權(quán)政治的統(tǒng)轄。這是俄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來自社會學(xué)的知識背景。
俄羅斯的威權(quán)主義:過渡形態(tài)還是長期趨勢?
從一般學(xué)理上講,威權(quán)主義有別于極權(quán)主義,也不是自由民主主義,當然,也有別于拉美民粹主義。筆者認為普京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威權(quán)主義”③,雖然他本人并不完全認同。
一般而言,西方學(xué)界認為威權(quán)主義政治的特點為:其一是非意識形態(tài)化;其二,威權(quán)體制一般具有一黨主導(dǎo)的多黨體制;其三,輿論有一定自由度,但一切都在調(diào)控之下;最后,是經(jīng)濟上的平民主義措施。
普京的“威權(quán)主義”特殊之處在于,第一,對歐洲價值觀的訴求,他曾經(jīng)多次表白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普京在2008年也說過自己是保守主義者,這是指對傳統(tǒng)價值、國家、宗教、家庭的信奉。第二,存有彈性的威權(quán)。雖然強調(diào)穩(wěn)定、安全、發(fā)展是第一要務(wù),但當2012年底出現(xiàn)民情波動,普京還是根據(jù)情況作出了調(diào)整。他最近強調(diào)了要實現(xiàn)中產(chǎn)階級的利益,要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茲羅平說,普京實際上既非自由主義、又非保守主義;既不左、又不右;普京就是普京,這就為他在一個國情異常復(fù)雜多樣大國的執(zhí)政留下了空間。
在筆者看來,除了歐美現(xiàn)代民主之路,對于多數(shù)國家來說,特別是就轉(zhuǎn)型階段的國家而言,契合于本國發(fā)展水平的開明柔性的“威權(quán)體制”相當普遍。亨廷頓說過,“西方”是唯一的,并非普世的,他意圖強調(diào)的就是“西方”道路不是可以被簡單復(fù)制的。非歐美國家在從前現(xiàn)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過程中,無論拉美、東亞,甚至二戰(zhàn)后初期出現(xiàn)過民主治理的國家,比如說韓國,到了20世紀60年代還是回到威權(quán)體制,中國臺灣、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都有這個威權(quán)主義的階段。因此不能把它簡單說成獨裁,要作區(qū)分。
區(qū)別于獨裁者,普京是個轉(zhuǎn)型期的過渡人物。有人推測,普京很可能再干一屆,但不會一做就是四十幾年。因為俄國雖然有崇尚強人政治的傳統(tǒng),但另一方面,四百年來深深浸染在歐洲自由價值觀的熏陶下,自由知識分子始終是它精英的主導(dǎo)方面。一定條件下,反對派聲音之強大,前一段也已經(jīng)看見。這是一種歷史性的制約,規(guī)定了當代條件下俄國政治發(fā)展的某種區(qū)間,也即既不可能太過于遵從西方民主,但是也不會過于回歸前蘇聯(lián)的舊制。
盡管人們把普京歸入“威權(quán)主義者”的類型,不光這一說法本身帶有濃重的西方學(xué)術(shù)界定的痕跡,似乎還有余地找出一個更能說明普京現(xiàn)象的合適范疇;而普京對于民主問題也有著自己的界定,他不太認同使用“威權(quán)主義”的說法來描畫他主政時期的俄羅斯政治。其一,他認為,我們不追求有俄國特色的民主,尊重世界自由民主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則,但是這些普遍規(guī)則在俄國如何實施,要根據(jù)具體條件而定。其二,普京經(jīng)常反駁道,俄羅斯怎么不民主?我作為總統(tǒng)是全民直選產(chǎn)生,美國總統(tǒng)還是間接選舉的。筆者本人還曾經(jīng)親耳聽過普京兩次當面反駁西方學(xué)者對自己和梅德韋杰夫之間政治“協(xié)商”的批評。他說,布萊爾和布朗不也是經(jīng)過協(xié)商而換馬的嗎?其三,有一次,普京談起他對于“主權(quán)民主”理論問題的理解。他認為,主權(quán)主外,而民主事內(nèi),兩者到底是何關(guān)系,還值得探討。這里反映出俄國威權(quán)主義并不急于成型,而是帶有很大的探索性。④
盡管普京對于民主有著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但是形勢往往比人強。所以,面對潮流變化,梅德韋杰夫作為普京參選的提名者,在與反對派對話中還是確認了要對第三次參加總統(tǒng)選舉作出憲政限制這一問題進行討論。問題在于,普京確實曾經(jīng)期望,“你們給我二十年,我還你們一個強大的俄羅斯”。這有其客觀邏輯:像俄羅斯這樣龐大經(jīng)濟轉(zhuǎn)型過程,特別要改變能源依附模式;包括普京最近特別強調(diào)的將對遠東、西伯利亞的重新開發(fā);還包括俄羅斯有可能在較長時期中不存在外來的嚴重安全威脅,使其有可能安心國內(nèi)建設(shè)等這些條件的出現(xiàn),意味著俄羅斯人比較傾向于通過一段較長時間的穩(wěn)定,來取得發(fā)展的機會。這些客觀需求和條件意味著一個有彈性的、比較理性取向的威權(quán)制度還可能會延續(xù)。如果普京能動員民眾,協(xié)調(diào)各方利益,專注于國內(nèi)事務(wù),俄國是有很大機會的。
俄羅斯民主政治的未來發(fā)展
筆者不認為俄國的民主在6到8年之內(nèi)馬上就能變成北歐或者西歐那樣。俄羅斯在這樣一個傳統(tǒng)包袱之下,要從一種政治力量獨大回歸到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多元開放、多黨競爭的局面還不太可能。但是,在上述發(fā)展預(yù)期的激勵之下,包括在二十多年轉(zhuǎn)型中艱難成長的中產(chǎn)階級推動之下,各種利益關(guān)系有可能得到調(diào)整,法律制度還是有可能會被改善,知識精英和年輕人對輿論空間的需求,都會使得普京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在普京還身強力壯,對自己的政治抱負還滿懷信心的前提之下,筆者認為這種心態(tài)也可能為普京提供理性決策的空間。但是,他會比較慎重。
從理論上說,發(fā)展與穩(wěn)定、民主和經(jīng)濟增長這些基本范疇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至少在中、短時段上,還是不那么確定的。也即,在某一些時段,經(jīng)濟發(fā)展依然有可能不催生民主,而民主反過來也不一定支持經(jīng)濟增長。但是,從較長時段看,在現(xiàn)代化進程的相互影響之下,對于先進制度的學(xué)習(xí)與選擇、改革與創(chuàng)新還是為民主政治的出現(xiàn)提供了廣大的空間。這是觀察俄國政治的一個理論背景。⑤
即使在西方,也不能將民主和強國路線截然對立,比如說,美國當然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大國和強國,但是美國的既強大又民主,的確是有著一些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條件的。至于非歐美世界,它能否實現(xiàn)既強國又民主這樣的抱負?如果都要以美國標準來衡量非歐美世界,在筆者看來,在可見的中短時期之內(nèi)很難做到。
對非歐美國家來說,民主的發(fā)展非常可能和強國不同步,某個階段強調(diào)國家的強大,等國家強大到一定水平,它給民主提供一個發(fā)展的空間;但到民主發(fā)展到一個臨界點了,又會追求強國目標,就這樣在強國和民主訴求之間循環(huán)往復(fù)。甚至,這還只是一種假設(shè)中的樂觀主義的邏輯,而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實際情況往往是以強國意識形態(tài)來動員和調(diào)度民眾,但是,在民眾的政治情緒高揚起來之后,所獲得的結(jié)果往往是既不民主、也不強國。在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發(fā)展進程中,人們看到了太多初創(chuàng)的體制根本無法包容被動員起來的民眾激情和訴求這樣的一類事實。
如果說,歐美在民主和強國之間相對均衡、較為同步發(fā)展的話,那么,在非歐美國家,民主和強國這兩個目標的實現(xiàn)可能不那么均衡和同步,但是,這兩者始終是緊密相關(guān)的。比如說,普京時代可能就是將強國這個目標放到較之民主更為優(yōu)先的地位之上。
政治強人與一般的現(xiàn)代民主進程
在丘吉爾、羅斯福等老一輩政治家離開歷史舞臺之后,西方世界已經(jīng)太多年沒有出現(xiàn)過政治強人的身影了,晚近的三、四十年中,出了撒切爾夫人,卻頗具爭議。敢問,沒有政治強人是現(xiàn)代民主之福嗎?
答案可能取決于在何種情況下來考察這一命題。正常狀態(tài)下,對于發(fā)達國家來說可能是肯定的。日本首相一年換一次,少了誰都沒關(guān)系,社會照樣運轉(zhuǎn)。所以,強人對這些穩(wěn)定的民主社會來說,不是一個必備的要素。但是,能否說歐美社會今后就再也不會出現(xiàn)政治強人了,這很難說。
在民主社會出現(xiàn)重大問題的時候,還是需要政治強人的。比如,撒切爾夫人。當遇見“英國病”挑戰(zhàn)之時,是她推動了私有化,才使得西方世界70年代晚期之后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她是一個引導(dǎo)潮流變化的強人。同時,她也下決心打馬島之戰(zhàn)。當時的外交大臣不愿意打,就被“鐵娘子”立即撤職。這在現(xiàn)代英國史上也是罕見現(xiàn)象,這就是鐵腕。鐵腕,是要經(jīng)過戰(zhàn)爭和改變潮流這兩項考驗才名副其實。
現(xiàn)在的世界性危機除了金融體制方面的弊病之外,根本上是一個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問題。比如,福山的觀念就是,民主自由當然是一個要堅定追求的目標。問題是民主制度形成之后,在每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如何執(zhí)行,碰到問題之后如何調(diào)整,即使在歐美歷史上,也是要通過各種歷史的偶然性而得以實現(xiàn)的。也就是說,不是民主自由的體制設(shè)定了以后就一了百了,而是通過每一歷史環(huán)節(jié)的偶然性機會使之得以完善。因為當年有華盛頓、杰斐遜、富蘭克林、羅斯福這些強人,才使得民主制度在危機時期能夠得到完善和調(diào)整。西方尚且如此,何況轉(zhuǎn)型國家。⑥
福山的觀念實際上是對現(xiàn)狀的一種批評。民主體制建立以后,它的調(diào)適過程中還會發(fā)生危機。民主的延續(xù)要靠人,不能過分迷信制度,制度還是外在的,否則歷史就真地終結(jié)了。目前這種情況下,要能夠超越利益集團的限制、兩黨的限制,闖出一條新路,使民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個意義上,“普京”這個符號不僅對俄國有意義。俄國現(xiàn)象之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非歐美社會的界面上,對西方最全面的學(xué)習(xí)而又反叛,同時,也體現(xiàn)了在非常時刻,受到過民主洗禮的民眾卻反過來表現(xiàn)出對于強力政治人物的期盼。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上的“俄國瞬間”已經(jīng)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俄羅斯瞬間”似乎又在涌動孕育之中。這并不是說,俄羅斯似乎就又會卷土重來,領(lǐng)導(dǎo)世界潮流,無論就其經(jīng)濟、政治的體量,以及文化的認同度來說,都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所謂的新的俄羅斯現(xiàn)象的要義在于,在一個多樣化、多元化社會進程之下,民主政治的推進,一定是有著更為豐富多彩的樣式與路徑,包括在一定條件之下還會要以所謂“有彈性的”威權(quán)政治作為載體。
本文想說明的是,在沒有亞里士多德式思辨?zhèn)鹘y(tǒng)的流風(fēng)余韻,沒有文藝復(fù)興和啟蒙運動的熏陶,也沒有工業(yè)革命和民族國家體系所帶來的規(guī)范設(shè)置,等等,這一系列獨特的歷史條件存在的情況之下,任何非西方社會的民主進程都會遭逢極其巨大的困境和挫折。但是,一個孕育著未來希望的東方或者半東方社會,難道不應(yīng)該以既是破解而又要善用自己歷史積累的創(chuàng)造性方式,為民主政治的發(fā)展作出自己更多的貢獻?
注釋
2013年4月20至21日全國俄羅斯哲學(xué)學(xué)會研討會上,本人在開幕致辭中表達了這一看法。
[俄]A.A.高爾斯基:“米洛夫關(guān)于俄國歷史發(fā)展問題的范疇”,《俄國歷史進程的特征:紀念米洛夫院士論文集》(俄文版),政治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56~61頁。
在俄羅斯,使用“威權(quán)主義”的范疇或者“柔性威權(quán)主義”的范疇描述普京政治現(xiàn)象的,可見于2011年瓦爾代論壇的年度報告。該報告主要是在俄羅斯學(xué)者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的主導(dǎo)下進行。
以上所引普京總統(tǒng)關(guān)于俄羅斯民主的提法,均采用作者本人在瓦爾代會議上聆聽普京本人發(fā)言的記錄。
有關(guān)2012年以來俄羅斯政治發(fā)展的當前進程的具體描述,可見《俄羅斯研究》雜志,2012年以來的相關(guān)各期中本人和同事們有關(guān)這一問題的具體闡述。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Part V: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Y, 2011, P.437-484.
責(zé) 編∕馬冰瑩
The Unique Logic of Authoritarianism in Context of a Political Strongman
--Debate over Putin and the Future of Russian Democracy
Feng Shaolei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approximately 20 years of Russian democratic politics shows a trajectory of initially adopting a pro-Western diplomatic policy and then alienating the West and of first promoting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n returning to conservatism. The historical restriction determin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democracy can not follow too closely the Western model and will never return to the former Soviet system, either. I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Russian people still tend to favor Putin,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trongman. They will creatively explore Russia's own road to democracy while try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ir country.
Keywords: Putin, Russia, democratic politics, political strongman
【作者簡介】
馮紹雷,華東師范大學(xué)終身教授、博導(dǎo),國際關(guān)系和地區(qū)發(fā)展研究院院長,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俄羅斯政治、外交、社會轉(zhuǎn)型、大國關(guān)系、國際政治理論等。
主要著作:《制度變遷與對外關(guān)系——1992年以來的俄羅斯》、《轉(zhuǎn)型時代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