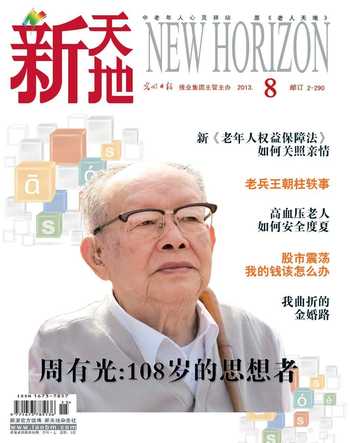大師魅力
何勒
仲夏時節,北京的雨水來得格外地稠密,似乎天公也在含淚送別學界相繼離去的三位大師:李文海、吳征鎰、張光斗。
這里我們擷取大師們生前生活中的幾個小片段,從中你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大師的風范與魅力。
李文海:一個真信馬克思主義的人
李文海, 1932年生人,江蘇無錫人,中共黨員,中國人民大學原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2013年6月7日16時30分,因突發心臟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李文海先生當過人大清史所的副所長,當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他篤信馬克思主義,在學界是有名的,也有人對他有不同看法。但他的同事和弟子這樣評價文海先生:他始終是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
李文海的一位同事說過這樣的話:“李老師是真信馬克思主義,不像有些人,假信!”
什么叫真信?怎樣做才不是假信呢?
他的學生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周育民,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真信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人們照樣敬重——記得1991年在武漢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我與李老師在一個小組討論。我提交的論文與李老師的觀點不同,李文海先生的文章影響很大,我報告的觀點難免使其他學者聯想起他的這篇文章,但李先生卻虛懷若谷地肯定了我的這篇文章史料十分扎實。”
后來,因上海修改歷史教科書的事情,周育民與李文海又有過爭論,周育民說,爭論過后兩人在清史工程的多次會議上碰過面,“他從來沒有對我這個有點‘忤逆的學生稍示慍色,差別只是以前叫我‘小周,改稱‘老周了。這種微妙變化,他和我之間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傳了。”
與李文海史觀未竟相同的人大政治系教授張鳴說自己是一個見了領導就遠遠躲開的人,和李校長并無交往;但是之前有出版社、雜志社的人找他,張鳴問原因,卻是因為李文海的推薦。“他當校長的時候比較平和,確實是個學者,擔任職務不是為了自己,不善經營,比較清廉。”
人大新聞學院畢業的湯涌介紹,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人民大學挖地基挖出一個大坑出了水,學一樓傾斜,鋼珠順桌子能掉到地下去。當時北京電視臺報道了此事,李文海校長找到新聞系主任何梓華教授,求校友公關。何教授說,我們教學生的時候,就要求他們頂住壓力做新聞。李校長想了想,再沒多說。
而人大的老師們記得,當時校園建設基建費用短缺,出了幾個缺口,李文海為此急病了,吐過血。
李文海是一個言行力爭實事求是的人,所以,他對馬克思主義是真信。
吳征鎰:一個不工作心就發慌的人
吳征鎰,1916年6月13日生于江西九江,中共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2013年6月20日1時31分,吳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昆明逝世,享年97歲。
1950年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成立,吳征鎰任副所長。1958年夏,已過而立之年的吳征鎰卻決定舉家遷往云南。許多人不理解當時在首都已有一番事業的他,為什么選擇去邊疆偏遠地區。吳征鎰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希望能專注于自己熱愛的植物學。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吳征鎰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燒鍋爐之余收集了各地中草藥手冊,訂正中草藥植物名稱,寫下四大本筆記,成為專著《新華本草綱要》之底本。
年逾花甲時,他還堅持赴湘西、青海、東北等地考察,兩次進藏、兩次入疆,重走祖國山川,審視全國植物區系分布,系統全面地回答了中國現有植物的種類和分布問題,摸清了中國植物資源的基本家底,提出被子植物“八綱系統”的新觀點。
他的弟子李德銖回憶說,1988年,71歲高齡的吳老還拄拐杖,帶領6個博士生一起在昆明西山考察。近幾年他自己的工作重心——建立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其具體實施工作就出自吳征鎰的建議。
在九十高齡前后,吳征鎰先生視力大幅下降,《吳征鎰文集》和《百兼雜感隨憶》兩部文集出版后,吳老設想以后可以過“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的日子。但當國家編纂《中華大典》的消息傳來時,主編任繼愈先生懇請吳老來擔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主編。家人擔心吳老九十高齡的身體無力擔當此任,呈請任老容準。任老說:“中國只有吳征鎰能擔此任”,又說:“讓我們兩個九十歲的老人一道來完成編典任務吧。”吳老欣然接下編纂《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任務,全心投入編典準備。
“吳老一輩子是一個不工作心就發慌的人,到80歲以后每天工作6個小時,90歲以后為《中華大典·生物學典》,每天工作2~3個小時,在世時基本把大典的框架搭好,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確實是我們永遠都學不完的。”吳征鎰的學生如是說。
張光斗: 一個給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師
張光斗,1912年5月出生于江蘇蘇州常熟市,水利水電工程結構專家和工程教育家。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13年6月21日13時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我不僅不是什么‘泰斗、‘大師,也不是科學家,我就是一個工程師,一個給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師。”他對采訪他的記者說,“有人以為我這是謙虛,說:‘你還不是科學家啊?我真搞不懂他們的想法。”
張光斗說,“我們過去一直就有個毛病,重科學,輕技術。現在很多人,你說他是工程師,他很不高興,你說他是科學家,他便很高興。甚至不少中國工程院院士,都希望人家叫他科學家,而不喜歡被稱為工程師。”
他真的是一個工程師嗎?從眾多媒體的報道中,我們看到——
2000年,已近90歲的他到三峽大壩工地檢查導流底孔施工質量。他不讓人攙扶,爬上四十多米高的腳手架,用手摸到表面有鋼筋露頭等凹凸不平的麻面,當即要求施工單位一定要按照設計標準返工修復。
2002年之前,作為國務院三峽樞紐工程質量檢查專家組副組長,他一連幾年每年都要去幾趟三峽工程現場。
……
作為“水利工程師”張光斗,愛水在清華校園是出了名的。看到哪個學生沒關好水龍頭,他就會跑過去,邊關水龍頭邊大聲訓斥:“你們這些小年輕的,早晚有一天會嘗到沒水喝的滋味。”
他的女兒張美怡說,在他們家,洗衣洗菜用過的水要留著沖馬桶、擦地板,晚上吃飯,只開一支15瓦的臺式日光燈,誰要是順手開了天花板上的大燈,就犯了老人的大忌。
晚年的張光斗,生活已離不開手杖和輪椅了,但他依然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拄著手杖在屋子里轉6圈,然后吃早飯,開始工作。上午,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瀏覽當天的報紙和信件。他一直沒有停止思考,就相關問題會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或者寫信,提出建議。如果覺得問題特別重要,他就會搜集資料,拿出論據,寫成文章投寄報刊,甚至上書中央。
張光斗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工程師,從黃河上游的龍羊峽、拉瓦西到長江中上游的葛洲壩、三峽,從雅礱江的二灘到紅水河的龍灘,哪里有水利工程,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里。
(責編:蕭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