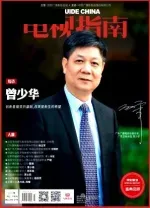格式!格式!
婁霄鵬

年輕的文藝青年們總是厭惡一切形式上的束縛,喜歡打碎所有的枷鎖和看上去有些像枷鎖的東西。年輕的電影編劇們通常碰到的第一個“枷鎖”,就是劇本的格式問題。我這里說的是英文劇本,不是我們中國的劇本。中國劇本的格式要復雜得多,在我做劇本審讀時讀過的有限的劇本中,就見過至少七八種自我研發的劇本格式,例如在描述性段落前面,有的加三角形,有的加方括號,有的退格,有的不退格;而人物對白有的加雙引號,有的不加;字體也有人大膽創新,有的用宋體,有的用楷體,如果不是怕引起閱讀障礙,我相信一定會有人選用大篆。我真為中國的劇作者們享有的自由而高興,相比之下,好萊塢的劇作者們就顯得循規蹈矩,很缺乏創造力。
多年前我剛剛開始學編劇時,對格式這個玩意也持不屑一顧的態度。我從前是學理工科的,美國的理科論文對格式的要求非常嚴格,比如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個標點符號也不能出錯。作為一個喜歡用“少許”、“大約”這些模糊定量概念來探索真理的中國人,我對這些吹毛求疵的要求深惡痛絕。后來好不容易換到了文科,居然立刻又碰上了這些死板的規定,剛要大松一口氣的我把剩下的半口氣又憋了回去,郁悶地沒有吃下晚飯。文學創作(假如大家慨然允許我把劇本寫作稱為文學創作的話)竟然還要受所謂格式的限制,我毅然認為這實在違背文學的本質。當老師在課堂上不厭其煩地向我們強調劇本格式的重要性時,不但是我,我熱愛自由的美國同學們也表示出了不耐煩,還有一個家伙干脆把老師嘮嘮叨叨的丑態寫進了劇本里加以嘲笑。在他的描述中,這位老師像個精神病患者一樣來回重復著一個詞:“格式!格式!……”大家不約而同地想起了《越戰啟示錄》中馬龍白蘭度絕望的囈語:“The horror!The horror!”(恐怖!恐怖!)
然而,不按格式寫作的劇本,會被判作不合格,一個更讓人沮喪的消息是,聽說好萊塢的劇本審讀者,只要看到一個不符合格式的劇本,他連一個字都懶得讀,就直接槍斃掉。所以我們都忍著怨氣,學習了英文劇本的格式,并在之后的寫作中,努力做到一個標點符號都不出錯。這種滿腹怨氣的狀態沒有持續太久,實際上,頂多持續到寫第二份作業的時候,大家就變得無所謂了,而到寫第三次作業時,我相信大家已經變得相當快活,不但不為在“枷鎖”中寫作感到痛苦,還享受到了一種剛剛學會開車時的快樂。至于現在,我不但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劇本格式是個好東西,而且還會把它和詩詞的格律、音樂的曲譜、繪畫的透視法則相提并論,這些“格式”并沒有限制住這些藝術形式的自由,反而逼迫出了更多的創造力。我甚至悔恨地想到,當初寫理科論文時,我本可以體會到更復雜的格式帶來的更多快樂。
英文劇本的格式其實很簡單,比起詩詞的格律來,簡直像四則運算和微積分的差別。我可以肯定,一個智力健全的人,只需要花上不超過十分鐘,就可以完全掌握所有的規定。英文劇本和中文劇本格式(如果有一個的話)最大的區別,就是對白的位置要放到中間,而且每行的長度只有頁面寬度的一半左右,這樣看起來非常醒目。英文比中文有一個方便之處,可以分大小寫,比如人物第一次出現時,名字要大寫,好讓制作者和演員容易找到,而中文除了加黑,很難實現這個功能。在需要強調一個特寫時(比如便條上的一行字),通常會單開一行來“插入”這個信息。英文劇本的字體也有規定,要用Courier New,字號是12(相當于中文字體“小四”的大小),如果一位缺乏同情心的劇本審讀者看到了一個對其他字體有所偏好的劇本,多半也會直接扔掉。劇本封面上的電影名稱,也約定俗成地采用12號字的大小,而不像中文劇本封面上的標題那樣恨不能鋪滿整頁紙。我猜這大概是一種工業化成熟之后的謙卑態度。此外,所有英文劇本的開頭第一行字通常是FADE IN(淡入),最后一行字是FADE OUT(淡出),這幾乎成了編劇們開始和完成劇本時的一個儀式。了解這些內容,十分鐘應該足夠了吧。其實,美國早就有了Movie Magic Screenwriter和Final Draft這些劇作軟件,編劇根本不用自己排版——寫到這兒,我感到這篇文章也有些多余。
如果你真的熱愛劇本寫作,我想注意一下格式這件小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忍受不了的痛苦,也根本耽誤不了你發揮奔放不羈的想象力,就算最天才的數學家,也沒有拒絕使用世界通行的加減乘除符號,而非要自己發明一套新的出來對么?我想是這樣。我不知道中文劇本在將來的某一天會不會紆尊降貴采用這種格式,或者至少有個統一的格式。這種格式有一個好處是,每頁劇本拍攝出來大約時長一分鐘,所以很容易根據劇本的頁數來判斷電影的長度,不過,確實比中文劇本耗費了更多紙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