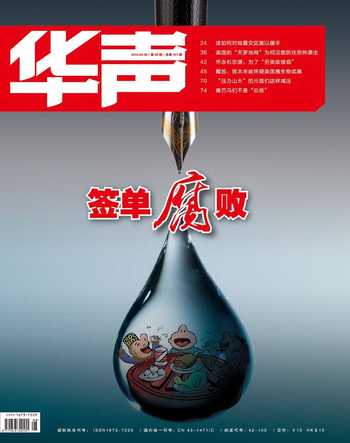該如何對地震災區施以援手
韓寒 左志堅



編者按:蘆山“4·20”7.0級強烈地震發生后,圍繞著媒體、志愿者要不要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如何更專業更高效,有哪些地方值得反思等等熱點問題,兩位熱心公益的“公共知識分子”——韓寒和左志堅(《21世紀經濟報道》新聞總監),近日分別撰文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韓寒:我的地震思考錄
5年前,汶川地震,我和老羅等朋友盡可能早的趕到了成都。不少網友捐了物資委托我們救災用。次日,又有幾個志愿來救災的朋友與我匯合。我們告別了牛博網的朋友,開始單獨行動。在那里停留了一周多,有些話,也許此刻說出來比較合適。
作為第一批去汶川的人,對于“志愿者”三個字有很多感受。有人對主動去救災的人頗有微辭。其實我部分贊同他們的苛責。在去往重災區的路上,的確看見過一些志愿者車拋錨了,身體出狀況了,搞不好救人不成反被救,也偶有志愿者的車輛堵路的情況發生。但總體來說,在512那樣大的災難前,志愿者帶去的幫助遠比他們造成的麻煩多得多。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謠言,比如“當年我們開著跑車什么物資都沒帶,卻到處玩,結果車壞了堵住了救援隊的路”,更有不少是針對其他志愿者的,我不知道編這種故事的人是什么樣的微妙心態。在巨大的災難面前,一定是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去救助的,在救助的過程中,定會有不周全。災難越大,越需要社會共力。有些人,對著這些因為熱心而造成的麻煩不愿理解,并且死纏爛打窮盡挖苦,反而對一些明顯的公權力失職監管缺失造成的悲劇坐視不管,甚至助紂為虐,我寧愿他在家里看跳水比賽。
但志愿者也有不少需要反思的地方,包括我也是。2008年,我和朋友一腔熱血,到了那里,發現其實我們能派上的用場并不大。網友們因為信任,把很多的帳篷和物資寄給我,我和幾個朋友一開始會選擇有目的的發放,后來發現這工作如果沒有專業對口的基金會,你干到奧運閉幕都完不成,而且容易一筆亂賬。后來我讓上海的朋友直接把物資給了壹基金。至于到四川的那些物資,我們兩臺車,白天拉滿,一趟趟去往不同的受災區,對于災民的幫助其實有限。更大的幫助,就是能最準確知道災區所需,發布給大家,以便于網友們在捐物資的時候更加有針對性。
在汶川時,我就收到了很多的贊美。其實根本就不配。很多冒死救助災民的真英雄被媒體忽視,我一個拉貨發物資和傳達消息的志愿者卻被人夸獎,其實羞愧。真正見識過巨大災難救援現場的人,都會覺得自己的渺小。越往后這種羞愧感越重,以至于我一直戴著口罩,一看見有媒體來就避開,也沒有發布什么我在災區的照片。說這些只是想告訴大家,專業救援和熱心救助之間的區別。好在我開車水平還行,沒添亂,也招募來一些物資,不至于完全是個廢人。而配得起贊美的是那些樂觀的災民,很多專業救援隊,志愿的救援者,一些專業基金會的志愿者,部分敬業卻不過度消費災民的記者,還有我平時所挖苦和批評的部隊及警察。
網絡雖然對救災幫助巨大,但網絡謠言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困擾。當時傳播信息靠博客和論壇,這種困擾還不算大,無非是一些網友夸大事實。我們在汶川地震期間,常常看到網上帖子,說某地已經不行了,斷糧缺水少藥,廣場滿地傷員,快救救我們。在我們飛奔去的一路上帖子還不斷更新,直播慘況。等我們到那發現該鎮受災很小,人們在廣場上歇息聊天,甚至旁邊餐館和商店還有不少開業著。很多志愿者都聞訊趕來了,物資堆積如山。一周內,我們被這樣的網絡帖子牽著到處走,很多次到了現場才發現與描述不符。災難面前,誰都不愿被遺忘,誰都想有更多的物資,但資訊傳播的偏差,往往讓由民間力量積蓄的重要的物資沒有能去到最急需的地方。最后我們的經驗是,往往寂靜無聲的地方,災情真的很嚴重,叫得此起彼伏的地方,也許可以先緩一緩。
如今有了微博,甚至有人借災難騙轉發關注甚至騙錢,捏造了不少信息。一些朋友無法分辨,一心急都轉發了,然后變成熱門,民間志愿者甚至專業救援隊都往那趕,等發現是假的已經浪費了大把時間。這也是為什么那些求助微博我都不敢轉發,因為在汶川的時候,我們得到了不少教訓。在災難面前,網站對于類似求助信息在被廣泛傳播之前最好有基本的核實。至少IP地址完全不對的第一人稱微博要格外注意。
我也建議在救援最重要的72小時內,名人明星暫時不要前往。不少人能認出你的臉,一旦排場比用場更大,再多的熱心和善良都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是在地震后的心理創傷恢復期,愿更多的明星可以去那里,哪怕就是宣傳,也是件好事。這點和我2008年的觀點恰恰是相反的,2008年汶川地震的后期,很多明星去往現場。在那里呆了一周多的我的那幾個朋友對此有所不屑,都言作秀,說,為什么你們在最危險的那一兩天不來幫忙。到了2009年我就覺得,其實他們的做法是對的。這72個小時,應該留給專業救援隊和有經驗的志愿者。
還有一個感觸。當災難來臨,最好的救援者其實是你自己和你身邊的人。自救和互救往往是災難發生后最有效的方法。建議學校能夠開設或者強化救援課,教授各種情況下的自救互救方法。
親歷過幾次災區,更知道所謂道德兩字,不能用來高掛。災難各種,人心萬千,境遇兩極,也許誰都是高尚者,誰也都是卑劣者。面對自我的苦難,他人的生死,很多時候,你和你以為的你并不一樣。我們都愿擁有一個更好的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行善修行的方式。善舉A和善舉B之間不該互相責難,也不要用動機論去解釋那些善舉,更不可道德綁架。我一個朋友,做了不少善事,很多不愿言說,飯桌上也不愿意談起,更不會網絡平臺上有所表示。早年玉樹地震時,不見他有動靜,結果有另外幾個朋友覺得他冷血。其實他的企業是第一批捐款捐物的,很多平時我們和媒體根本關心不到的慈善,他都會參與。人心肉做,有些苛責和綁架其實會傷害到行善者。對我所不理解的他人進行道德審判是我們內心隱藏的另一種災難。話退萬步,每個人的經濟狀況不同,就算不捐任何東西,甚至不關心災情,只要自我為善,不害他人,就是對世界做的慈善。
在對遠方苦難的萬千聲援熱血熱心之后,我反而會看見身邊有很多默然不顯的困苦需要幫忙。眾善夠重,諸惡才能被誅;重善夠重,困難才能不難。
祈福雅安!
左志堅:
① 關于地震和救災的常見誤區
2008年5月,我剛從國外出差歸來,立即上了去四川的飛機。那次我負責川震南線(映秀—汶川—茂縣)的采訪。我本行是商業報道,但沒想到那次巨災之后,竟成了災難記者。
一年之后,災區回訪,把北線(綿竹—北川—安縣)所有重災區走了一遍。2010年,又逢玉樹地震,再次帶隊去了青海。同年,四川災區完成重建,三赴災區,那次去了遙遠的青川。2011年,日本大地震,調派記者去東京,并在后方組織和協調專題報道。
是的,幾乎每年都在做地震報道。我的意思是,災難其實離我們很近。就在上周六,我剛剛到成都,做川震五周年的回訪,并在映秀住了一天。沒想到剛離開,又是七級強震撼動四川。
這一次,又是舉國沸騰,但一些認知誤區仍然存在。我想就這五年來的觀察,做一些簡單的總結。
一、震中是否就是受災最嚴重的地方?我的回答:不一定。
在2008年的災難中,當地震局監測到震中在映秀時,所有注意力都被吸引到那里。加上映秀道路中斷,天氣惡劣,直升機又無法抵達,這放大了外界的焦慮。又因為映秀離成都非常近,許多民間救援資源就都發往映秀。但另一方面,人們沒有意識到北川其實更慘烈,整個老縣城被埋。其實當時北川的交通條件比映秀好許多,如果有更多資源投放到北川,或許能救出更多人。
因此,我以為,你能看到的重災區,或許只是容易抵達的地方。你視線之外的地方,有可能更嚴重。
二、救災越快越好?我的回答:未必。
快和效率是兩碼事。比如說,你在第一時間把大量人員集結到映秀,結果人員傷亡最慘是在北川,那整體救援效率未必就高。我們要的是救援效率,這就要求指揮者必須很專業,而不是很熱血。
512那次因為氣候太惡劣,直升機無法獲取完整信息圖,這次就很好,無人機很快拿回了全景圖,這就對指揮者調配救災資源起到很大的作用。完整透明的信息是科學決策的基礎。
三、救人應該靠政府,老百姓不要添亂?我的回答:這話要一分為二看。
2008年我基本是和先頭部隊同時抵達映秀。部隊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等他們走整整一夜,抵達震中時,能做的事情實在是有限。而且山區道路不暢,意味著大型機械無法進入救人,徒手挖人的效率是很低的。我親眼看到兩位士兵花了很長時間去搬卡住的樓板,卻只能無奈的含淚放棄。
最有效的救援恰恰是災民自救。無論是時間還是地理位置,都比外來的部隊有優勢。這時候,防災教育就特別重要,平時的演習和組織,在災難真正來臨時,是能救命的。不知道2008年之后,四川各地的防災教育做的如何?
四、志愿者最好不要去災區?我的回答:這個要看是什么志愿者。
如果你連山區都沒去過,必要的沖鋒衣、睡袋什么都沒有,我也覺得沒必要去。但如果你在某些方面有一技之長,災區就可能很需要。比如說,我當時是和廣東的醫療志愿者隊伍同時進的映秀,醫療人員體力未必有多好,但災區很需要啊。
另外,一起同行有四川戶外俱樂部的朋友,他們背70升的包,全部是藥品,送到之后部隊非常感激,當時最基本的消炎藥都缺啊。這些志愿者也沒有停留,送到就離開,給我印象很深。
其實民間資源總歸是越多越好,問題不是志愿者要不要去,而是如何組織起來,如何讓救援更有效率——這方面政府應該統籌。
五、紅十字會不放心,我該給誰捐款?我的回答:前三天不需要考慮捐款的事。
玉樹地震那次有朋友給我電話,讓我在災區給災民幾千塊錢,回來她給報銷。我說現在有錢也沒地方用啊。其實但凡這種巨災,對人類文明是瞬間毀滅性的打擊,一下打回原始社會。停電停水停電話,錢沒用。真正需要的是物資。一般來說,前三天,最需要帳篷(防余震只能住戶外)、藥品(傷員太多)、電源(沒法住樓里或者干脆電廠損毀)、食品和水。
六、我們要給受災最嚴重的地方捐款?我的回答:不一定,因為受災最嚴重的地方,資金太多,其他地方可能更缺錢。
提到512地震,通常第一時間想起的是映秀、北川,或者還有漢旺。但以我之后回訪的經驗來看,這三個地方重建資金綽綽有余,因為他們知名度太高。而一些不出名,尤其是比較偏遠的地方,其實更缺錢。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青川,這個地方離成都太遠,坐車要大半天,山路長又彎,但慘烈一點不弱于映秀,有整個村子被全部埋掉的。問題在于,由于交通閉塞,記者、官員都很少去,曝光不足,捐款企業沒法獲得曝光的機會,腹黑的官員也撈不到政績,那自然不重視。這種地方往往經濟基礎偏弱,反而更應該救助。
恐怕政府、媒體都無法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專業的NGO才可以。當然企業也可以做得更專業,而不是更熱血。這次雅安地震,我就一直很關心那些尚未被報道的災區。
七、地震局沒有盡責,有人預測了地震,政府不重視?我的回答:這是誤解。
我很小時就在科普書上看到說地震是無法精準預測的,現在依然如此。現代的科學只能讓大家知道,自己是否在地震帶上,知道這一點,就已經足夠保命了。
所以應把主要精力放在防震減災上。只要地震時房屋主結構不垮,就有足夠時間跑路,小命就能保住。政府的重心應是組織演習、核查建筑質量、加強科普教育。
② 記者去災區不是“添亂”
我的上述文章發表后,在新浪微博轉發8萬多次,許多媒體轉載并約訪,傳播力超出我的預期。于是我就反思,為什么我以為是常識的東西,那么多人當新聞一樣拼命在轉?
這里面很大一個因素,還是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的原因,自然與記者的報道不充分有關。這就引申出另一個話題,當部隊在緊急救災時,記者是否應該去災區?為什么一些網友甚至“跪求記者不要去災區添亂”?
在我看來,“記者添亂說”也是一種典型誤區。不光普通網友,就是指揮員也會有這種觀念。2008年5月,我和救援部隊一起徒步進映秀時,正好遇到一位軍隊高級指揮員,他坦率地說,記者不應該這個時候過來,會擠占救災資源。
我說我背了三天的食物和水,而且還帶了睡袋和很多藥品。他又說,那你進出總歸要占了道路吧。這位高級指揮員是來考察路況,準備修路的,那時候大型器械無法進入映秀,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我們幾個記者,不可能影響到他的修路大計,因為那時漫山都是各種救援隊伍,交通全部靠走。
2010年,玉樹地震后,我和同事第一時間直奔高原。等我們熬完高原反應,快進城時就發現,已經堵車了。是的,有些擁堵本來就存在,跟記者去沒去沒有關系。
幾天前,《南方周末》的曹筠武也寫了一篇文章,他說到一點,“在權力差序格局制定的資源分配體系中,媒體和志愿者的排序往往處于末端。舉例來說,如果一個路口實行交通管制,絕大部分記者和志愿者的資格是最后通過”。
這點我也有親身經歷。2008年那次,我徒步進映秀之后,里面電力和信號全無,又要搶著發稿,只能徒步再走回去。徒步三個小時后還要搭一段沖鋒舟,得搖號,最后我同去倆同事沒搖上,就卷了衣服在陰冷的渡口睡了一夜。重傷員和醫療人員則飛機往返,絲毫不受影響。
是的,如果我不去現場,可能會有一個災民可以先出來;但我帶出來的信息及其為災區帶來的社會資源,我認為是遠遠超過前者的。光我帶進去的藥品,以及回程時交給災民的現金,也能抵消掉我對災區資源的擠壓。
到玉樹地震的時候我更有經驗一些。一出西寧機場,就采購了大量的食物和藥品,把越野車全部填滿,最后這些物資大部分給了災民。那次,我們帳篷邊上駐著《南方都市報》的隊伍,他們是自己帶了小型發電機上去的。這顯然也是汶川震后的報道經驗,盡量不擠占資源。
其實,就記者的職業角色而言,他帶回來的信息,就已經遠遠超過所謂的“擠占”。人們通常會更重視實物資源,卻忽視了信息這樣軟力量的價值。
此外,地震的前三天,重心在救人,這個時候,記者的角色就已經在起作用。
我寫上述“誤區”這篇文章,有一個重要的觀點:資源是隨著信息走的,沒有透明的信息,就沒有合理的資源分配和最優的救援效率。
當年如果沒有北川一線記者吶喊和呼救,當地的災情可能不會得到充分認知。那時候的視線都集中在兩個孤島——映秀和汶川縣城。也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受災極其嚴重的青川,未能在第一時間獲得與災情匹配的援助。這些都是旁觀者看不到的教訓,非一線親歷者不能感受其痛苦。
這次雅安地震,媒體吸取了教訓,許多記者迅速通過信息冗余的中心縣城,將有限的媒體人力分散到多個村落和孤島,核實并發布求救信息,為的是避免出現信息盲區。
有人會覺得微博時代,每個人都是自媒體,根本不需要記者前往。但信息的核實、發布、傳播,還是需要專業的媒體人來操作,才能提供對救援決策有價值的準確信息。
除了提供信息,媒體在中國的宣傳體制中,也有鼓勁和宣傳的作用。有沒有媒體在場,救援隊的工作激情是完全不一樣的。同樣,媒體的在場,也能起到輿論監督作用。許多人想當然的認為,只要一地震,所有人都會善心大發,其實災難后的丑惡也不少見,仍然需要監督。
只要是在一個文明社會,媒體的信息和監督價值,在災區中一樣存在,甚至只會更重要。記者擠占的那一丁點兒資源,實在是微不足道。
最有資格評判這個問題的,既不是網友也不是官員,而是受災的民眾。我在災區這么多次,沒有一個災民說厭惡記者的,他們會非常積極地為記者指路,他們很清楚,有沒有記者在場,救災資源的分配會完全不一樣。
即便是極少數之前不友好的宣傳官員,在那災難最初來臨的那幾天,對媒體也持較友好的態度,并盡力為媒體提供各種資源——他們早就把信息公開當作救災事業的一部分。
在日本大地震的時候,日本使領館更是在第一時間為中國記者開辟了綠色通道,迅速發出簽證,后來又盛贊中國記者在日本的報道。
認識信息的軟力量,就應該很容易理解記者的工作。真正的問題,不是記者要不要去現場,而是記者應當如何報道災難,以及災難報道時的倫理問題。這些也基本有共識了。
● 摘編自作者微博、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