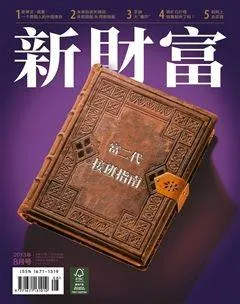公共消費類投資當成經(jīng)濟新增長點
當前,刺不刺激不是中國經(jīng)濟的核心問題,減速還是加速也不是核心問題,如何改革并通過改革引出新增長點才是關(guān)鍵。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導(dǎo)民間投資進入公共消費類投資領(lǐng)域,為此,要進行一系列的公共財政以及金融體系改革。
討論刺不刺激,
無助于尋找經(jīng)濟增長新思路
中國經(jīng)濟出現(xiàn)了明顯的增長速度的下滑,這一點沒有任何的爭議。歷史經(jīng)驗告訴我們,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完全反映經(jīng)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基本態(tài)勢。
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影響GDP增長最大的因素是固定資產(chǎn)投資,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固定資產(chǎn)投資完成額這一數(shù)據(jù)具有“經(jīng)濟穩(wěn)定器”作用,那就是:當經(jīng)濟增長放緩的時候,固定資產(chǎn)投資完成額是虛報的,因為地方政府有動力緩解甚至于掩蓋經(jīng)濟下滑的現(xiàn)實;相反,當經(jīng)濟增長過熱的時候,固定資產(chǎn)投資完成額這一數(shù)據(jù)是低報的,因為我們知道,統(tǒng)計局使用的固定資產(chǎn)投資完成額這一數(shù)據(jù),是根據(jù)工程項目完成額的目測法來進行的,這種目測法極其不精確,統(tǒng)計上更加嚴謹?shù)霓k法是實際的財政賬目工程款支出法。
與此密切相關(guān)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工業(yè)增加值的增長速度。這一增長速度實際上是從工業(yè)產(chǎn)值以及各個企業(yè)的銷售額中反推出來的,但問題在于,各個企業(yè)的銷售額與附加值之間,并沒有完全固定、一成不變的比例關(guān)系。因此,在整體經(jīng)濟放緩的時候,工業(yè)增加值的增速往往是高報的。這又是因為地方政府的主觀因素所致。
中國經(jīng)濟當前的種種數(shù)據(jù)—從出口到發(fā)電量到貨運量到大宗產(chǎn)品的價格,都反映了一個基本的情況,那就是中國經(jīng)濟當前放緩的態(tài)勢十分明顯。這一大背景下,該不該刺激中國經(jīng)濟的增長,自然成了當前社會各界所議論的重要話題。
中國經(jīng)濟該不該刺激?這不是問題。因為中國經(jīng)濟當前問題的實質(zhì)是還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點,而這個新的增長點必須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和調(diào)整措施釋放出來。
傳統(tǒng)的財政以及信貸刺激政策只能對傳統(tǒng)的、老的增長點發(fā)力,而這對中國經(jīng)濟的長遠增長并沒有好處。而不刺激又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所以,在刺激與不刺激之間討論話題,永遠找不到新的思路。
境外機構(gòu)編造“李克強經(jīng)濟學”,
大有游說不刺激政策之嫌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境外投資機構(gòu)編造出“李克強經(jīng)濟學”來總結(jié)他們所理解的新一屆政府的經(jīng)濟政策,其核心的一點就是不刺激。在我看來,這種以領(lǐng)導(dǎo)人冠名的經(jīng)濟學,在國外一般是根據(jù)領(lǐng)導(dǎo)人自己具體的施政理念來命名的,比如安倍經(jīng)濟學,明確提出他有“三枝箭”。而在中國,由境外機構(gòu)給中國領(lǐng)導(dǎo)人命名經(jīng)濟學,信誓旦旦地將經(jīng)濟學的內(nèi)容逐條描述出來,這種經(jīng)濟學大有政策游說的嫌疑,本質(zhì)上是把自己所理解的中國經(jīng)濟的政策取向強加在領(lǐng)導(dǎo)人的身上。
境外投資機構(gòu)的研究者比較關(guān)心的是自己是否預(yù)測得準確,自己的故事是否前后一致,而把自己對政策的理解、預(yù)測轉(zhuǎn)變?yōu)橛勺约好念I(lǐng)導(dǎo)人經(jīng)濟學,這恰恰是他們實現(xiàn)自己預(yù)測正確性的捷徑。因此,這種領(lǐng)導(dǎo)人經(jīng)濟學的游戲,恐怕不應(yīng)該過分地關(guān)注。
當前討論應(yīng)聚焦于
如何通過改革保增長
中國社會當前的最主要問題是緩解社會矛盾。種種的社會事件,從首都機場的爆炸案到城管暴力,都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社會矛盾正在不斷激化,而緩解這些矛盾的基本措施,就是要保持經(jīng)濟適當?shù)姆€(wěn)定。這好比穿越泥濘道路的自行車,必須要保持一個穩(wěn)定的速度,既不可盲目地加速,也不可過分地減速,加速固然有風險,減速也會使得自行車失去穩(wěn)定性。因此,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實現(xiàn)穩(wěn)定增長,這才是中國經(jīng)濟的當務(wù)之急。
但是,怎么樣保持穩(wěn)定的增長速度?當前的中國經(jīng)濟并不像1998、1999年的樣子,那時的中國經(jīng)濟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如國有企業(yè)嚴重虧損、國企職工大批下崗、國有商業(yè)銀行技術(shù)上破產(chǎn)、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今天的情況類似于1992年的中國經(jīng)濟,實體經(jīng)濟的增長點依然存在,但是缺乏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的增長點在舊的體制下不能發(fā)揮,因此經(jīng)濟進入低迷狀態(tài)。
根據(jù)這種形勢,中國經(jīng)濟當前要問的問題并不是要不要刺激,而是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如何通過改革來找到中國經(jīng)濟新的增長點,通過改革緩解經(jīng)濟下滑的頹勢。
公共消費類投資堪成新增長點
那么,中國經(jīng)濟的增長點在什么地方呢?
我自己在不同的場合也都堅持論述一個觀點:中國經(jīng)濟在當前階段最重要的增長點是一大批消費性的公共投資,其中主要包括各級政府應(yīng)對自然災(zāi)害的抗災(zāi)能力、城市內(nèi)部的地下管網(wǎng)建設(shè)、水和空氣質(zhì)量的治理。這一系列領(lǐng)域都是直接與百姓的生活質(zhì)量、生命財產(chǎn)安全緊密相關(guān)的,這一大批投資項目也是初步進入小康階段的今天,中國社會和百姓最需要的。
這些投資項目與傳統(tǒng)的產(chǎn)能擴張、工業(yè)化不同,這是一種消費性投資。問題的關(guān)鍵是目前為止,我們尚未找到一種機制,可以讓投資者從這些公共投資中獲得收益。換句話說,當前經(jīng)濟改革的一大挑戰(zhàn)是如何通過一系列制度創(chuàng)新,把民間資金引到這些公共消費類投資中去,從而找到新的增長動力。為此,國家必須放手允許地方政府試點,把一些準公共性投資轉(zhuǎn)變?yōu)楣竞匣锏耐顿Y方式。比如說污水處理,可以通過地方政府逐步收費,把這些收入轉(zhuǎn)讓給投資者,而投資者進行長期投資,從中獲得回報,最終通過BOT的方式轉(zhuǎn)給地方政府。再比如說,道路建設(shè)可以通過地方政府承包給企業(yè),由民間投資者經(jīng)營道路或道路周邊的廣告權(quán)、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來實現(xiàn)。
中國不缺資金,尤其是不缺民間資金。在過去幾年,民營經(jīng)濟投資量占到整個固定資產(chǎn)投資的70%左右。今天的問題是民間資金看不到方向,一旦我們能夠通過創(chuàng)新把民間資金引入到公共消費性投資中,那么不僅中國經(jīng)濟的增長速度能維持,中國經(jīng)濟的面貌也會得到改善,百姓的生活質(zhì)量同樣會得到提高。
配套進行公共財政及金融改革
與以上引導(dǎo)新增長點密切相關(guān)的是地方財政整頓。當前,不少地方政府欠下了巨額的銀行貸款,這些地方政府貸款將嚴重阻礙地方政府的持續(xù)發(fā)展。為此,中央政府必須找出辦法,發(fā)行一定的國債,將地方債務(wù)清理干凈。不僅要清理,而且要出臺相關(guān)改革措施,比如說允許地方政府征收一些資源類的稅收,如污染費;也允許地方政府逐步地推出房產(chǎn)稅,獲得土地出讓之外的穩(wěn)定財源。符合條件的、地方財政做得比較好的、比較透明的地區(qū),可以發(fā)行地方債和市政債,這事實上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讓地方政府得到資本市場的監(jiān)督。
為了順利引出新增長點,還需要在金融上進行整頓。當前金融體系中隱藏著一些呆賬壞賬,這些呆賬壞賬必須被清理,從而化解金融體系的風險。因此,筆者認為,金融改革刻不容緩。
總結(jié)說來,刺不刺激不是當前中國經(jīng)濟的核心問題,如何改革并通過改革引出新的增長點,這才是關(guān)鍵。而引導(dǎo)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導(dǎo)民間投資進入到一大批公共消費類投資中去,為此,要進行一系列的公共財政改革以及金融體系改革。
對于本文內(nèi)容您有任何評論或補充,
請發(fā)郵件至xincaifu@xcf.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