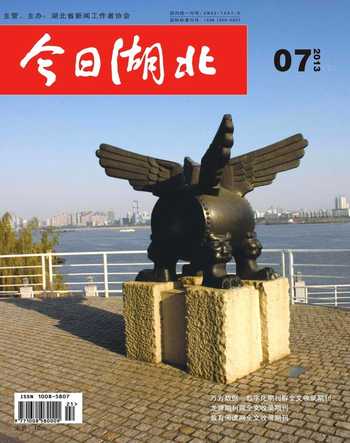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視角看詩歌中的愛情悲劇
張甜
摘 要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評是上世紀最重要的文學批評流派之一,它開拓了文學界的新視野,讓學者們從作品人物心理角度來解讀文本。本文以《孔雀東南飛》和《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為例,首先解析了詩歌中的愛情悲劇的普遍結構,隨后通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和“三重人格”的精神分析對愛情悲劇中人物進行探析,揭示了中外詩歌中愛情悲劇故事結構背后的普世的人物心理因素。
關鍵詞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 愛情悲劇 普遍結構 俄狄浦斯 三重人格。
一、引言
世界精神分析學之父,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近代歷史上對人類心靈有獨特貢獻的重要人物之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是20世紀最具有革命性的精神分析理論,是現代心理學的奠基石。運用這一精神分析法,我們可以從人物心理角度去分析文學作品,探析悲劇深層原因。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于《玉臺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該詩故事完整,結構緊湊,語言樸素自然,人物形象鮮明突出,為漢代樂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也我國古代民間文學史中的光輝詩篇之一。
西方著名詩歌集《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是英國民間流傳的口頭文學,故事非常生動,富于戲劇性,其中的愛情悲劇更是令人回味無窮。為統計數據的準確,筆者在文中引用的英國詩歌均出自1904年修頓·米弗林公司出版的選編本《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每首詩的A版本,筆者選取其中幾篇與《孔雀東南飛》進行對比,總結其敘事結構,試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探尋悲劇背后的人物心理因素。
二、愛情悲劇的普遍結構
比較品讀《孔雀東南飛》和英格蘭詩歌中的愛情悲劇詩歌,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愛情悲劇故事發展存在一個普世的故事結構,即愛情中男女雙方的真愛;愛人一方處境惡劣;愛人一方死亡或不幸;愛人另一方死亡或生不如此。
在《孔雀東南飛》中,以上愛情悲劇的四個階段有很明顯地體現。首先,雖然劉蘭芝和焦仲卿的深情在詩歌一開始并未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我們可以看到,接下來在焦仲卿送劉蘭芝回娘家的路上,兩人的海誓山盟,深情款款。焦: “誓天不相負!”。隨后兩人定下了:“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 的千古誓言。劉蘭芝首先遭到婆婆的驅趕,被迫回到娘家;隨后,其兄逼其改嫁。此時,在劉焦二人的感情世界理,劉蘭芝面臨著被迫違背和丈夫的誓言,感情處于危機時刻。但為了不違背與丈夫的誓約,劉在新婚的逼迫下以身殉情。聽聞妻子已逝,焦仲卿悲痛不已,隨即“自掛東南枝”,隨妻而去,其情令人潸然落淚,其舉使人扼腕嘆息。
無獨有偶,西方詩歌集《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有不少愛情詩歌的敘事模式和《孔雀東南飛》極為相似。例如第76篇The Lass of Roch Royal和第73篇Lord Thomas And Fair Annet,愛情均因男方母親的強制阻撓而以悲劇結束。在The Lass of Roch Royal 中,伊莎貝拉夢見了她的愛人格雷戈里并且獨自出海尋找他,后來兩人相遇,情愫暗生。當她再次來尋找格雷戈里時,不巧他在屋內熟睡,伊莎貝拉被他的母親堵在門外,并且告訴她格不在家。可憐的伊莎貝拉還懷著孩子,就這樣被拒之門外,飄無定所。格雷戈里醒來后找到了伊莎貝拉,但心愛的人已經香消玉損,在悲慟的煎熬中,格雷戈里自殺殉情。
在Lord Thomas And Fair Annet中,Lord Thomas(以下翻譯為托馬斯勛爵) 與Fair Annet(以下翻譯為安妮特)兩人感情頗深,后來因為誤解而懷疑對方。托馬斯勛爵在母親反復勸說下迎娶富裕的栗膚色新娘,放棄安妮特。托馬斯勛爵沒考慮清楚就決定娶一位家境寬裕的栗膚色的新娘,安妮特面臨著失去愛人情感危機。豈料那位栗膚色的新娘因妒生恨,將安妮特殺害。在痛苦與憤怒的煎熬中,托馬斯勛爵刺死了栗膚色的新娘。面對愛人冰冷的尸體,托馬斯勛爵痛徹心扉,以身殉情。
在詩歌集《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也有不少愛情悲劇是女方父兄干涉所致,例如第69篇Clerk Saunders和第72篇The Clerks Twa Sons O Owford。稍作總結可以發現這兩個故事也是按照以上愛情悲劇的普世情節展開的。第69篇中,Clerk Sauders 和May Margret深情款款,當二人欲廝相纏綿時,May Margret的兄弟們沖進來將Clerk Saudersa殺害。May Margret痛不欲生, 她將因為愛人的死無法走出痛苦的陰影。
第72篇The Clerks Twa Sons O Owford中,教士的兩個兒子深深愛上了市長的兩個女兒。與他們來說,一日不見如隔一年。不料他們的愛情遭到市長的反對,兩個小伙子被關押。無論兩個女兒如何懇求,教士甚至拿錢想去贖回兒子,都遭到拒絕。最后兩個可憐的小伙被吊死在樹上。失去愛人的女孩無法面對殘忍的事實,痛不欲生。以上兩篇詩歌中的悲劇均是女方父兄的暴力干涉所致,那么他們的行為背后隱藏著什么心理因素呢?
三、戀子情節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在兒童時期,男孩愛戀的第一個對象是自己的母親,他想獨占母親而仇視父親,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節”也就是“戀母情結”。而小女孩則深情于父親,想取代母親的位置,這就形成了“伊賴克輟情節”,即“戀父情節”。 同樣,父母對兒女也會表現出類似的愛戀,尤其是在單親家庭,父親或母親會不自覺中在情感上過度依賴兒女,兒女成為了他們唯一的感情寄托,這就難免產生“戀母情節”與“戀父情節”的倒置—“戀子情節”或“戀女情節”。
在《孔雀東南飛》中,焦母多年守寡,與兒子焦仲卿相依為命,兒子成了她唯一的情感慰藉和精神支柱。而眼前的一對小夫妻情深似海,卿卿我我,焦更是視劉為掌上明珠。因此焦母認為劉蘭芝奪去了原本屬于自己的那份愛,往日兒子圍著自己轉的情景已不復存在。為了奪回兒子的愛,焦母對兒媳百般刁難,狠心將賢良淑德的兒媳趕走。焦仲卿雖然一千個一萬個不愿意,但是在封建禮教的壓力下,還是忍痛選擇了順從母親,委屈自己的愛情。同樣,在英國詩歌Lord Thomas And Fair Annet和The Lass of Roch Royal,愛人均是因為男方母親的強制阻撓而分開,最終造成無法挽救的悲劇后果。
實際上,母親對兒媳或兒子女伴的厭惡正是她們潛意識中的“戀子情節”在作祟。雖然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 ,而且加入焦家后,“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可謂勤勞能干,秀外慧中。如此賢德的兒媳在焦母看來變成了奪去兒子的“第三者”,因此以種種理由將其趕走而恢復之前母子相依的“平和”景象。《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第69篇Clerk Saunders和第72篇The Clerks Twa Sons O Owford,悲劇均是由于女方父兄暴力干涉所致。他們將處女的妹妹或女兒視為自己的私有物,禁止其他男性的侵犯,顯示了父兄對異性孩子的依戀和占有。Clerk Saunders因為與May Margret同床共枕被后者的兄弟發現而被殺,表面看起來是May Margret兄弟對她的一種保護,實為因愛戀妹妹而對追求者的敵對,最終導致妹妹抱憾終生。
”Comfort well your seven sons, for comforted will I never bee.”
在The Clerks Twa Sons O Owford中,市長吊死愛慕自己女兒的教士的兒子,也是心理上對女兒愛戀與占有的一種表現。綜上所述,母親反對兒子幸福的婚姻,迫害兒媳和父兄怒殺女兒或妹妹的愛侶體現了父母長輩對異性孩子不正常的愛戀,即“戀子情節”這一愛情悲劇背后的人物心理因素。
四、本我,自我和超我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內心世界可以分為意識與無意識。“本我”總是處于無意識領域。“本我”遵循快樂原則,使人們設法滿足它追求快感的種種要求,而這些觀點往往是違背道德習俗的。所以,在“本我”與社會現實之間出現了一個調節者—“自我”。“自我”的任務是尊重現實原則,并且在此基礎上幫助“本我”實現本能要求。人格結構里面最高一層是“超我”,它是代表社會利益的心理機制。“超我”總是根據道德原則,將社會習俗不能忍受的“本我”壓抑在無意識領域。總之,“本我”是放縱的情欲,“自我”是理智與審慎,“超我”則是道德感,榮譽感和良心。因此,人的本我和超我經常處于矛盾斗爭中。
《孔雀東南飛》中,焦母對兒媳的迫害和驅趕就是其“本我”的體現。“本我”是無意識的,它追求快樂原則。焦母想要恢復以前與兒子的親密無間,這一“本我”思想促使她趕走兒媳,怒斥兒子為兒媳求情。焦母作為劉蘭芝的婆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體現出長輩的慈愛和風度,這些是焦母“超我”的體現,可惜她對兒媳沒有一點疼愛之心,殘忍地將愛侶拆開,最終導致兒子兒媳雙雙殉情的悲慘結局。《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Lord Thomas And Fair Annet和The Lass of Roch Royal這兩首詩歌中男方的母親亦是無法駕馭心中“本我”,使其控制了自己,任憑本我意愿破壞兒子的感情。托馬斯勛爵見愛人已逝,遂自殺殉情。
”Now stay for me, dear Annet, he sed, Now stay, my dear, he cryd; Then strake the dagger until his heart, And fell died by her side.”
托馬斯勛爵的母親因為一味追求“本我”而失去了愛子,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第69篇Clerk Saunders和第72篇The Clerks Twa Sons O Owford中女方父兄的表現也顯示了其“本我”的訴求。他們對女兒或妹妹的依戀和占有導致了對后者男性伴侶的憎惡,在本我意愿的驅使下,女方男性家長將女方男伴殘忍掠殺。
”O sorrow, sorrow come mak my bed, an dool come lay me doon! For Ill neither eat or drink, nor set a fit on ground”.
這些悲劇的發生顯示了“本我”在沒有監督或戰勝“超我”后的可怕結局,而施暴者本身也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過錯,“本我”思想一旦凌駕于“超我”之上,“劊子手”都認為自己是在履行鏟除敗類的神圣職責。
五、結語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使文學評述不再停留在文本表面,而是深入到作品人物的心理,開拓了文學批評的研究視角。本文探析了《孔雀東南飛》和《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愛情悲劇的普遍結構,并且運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俄狄浦斯”情節與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關系比較分析《孔雀東南飛》和《英格蘭與蘇格蘭民謠》中的愛情悲劇,向讀者揭露了東西方詩歌愛情故事相似的敘事結構和悲劇背后人物心理的普世情懷。
參考文獻:
[1]葛亮. 本我·自我·超我. 國外文學(季刊), 1999(4).
[2]胡庭樹. 從精神分析的視角看<孔雀東南飛>中主人公的愛情悲劇. 安徽文學, 2009,210095.
[3]Sargent, Helen Child & Kittredge, George Lyman. 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 [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4, p.153, p.143, p.152.
[6][奧] 西格蒙·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談本能與成功 [M]. 梁鳳雁,編譯. 石磊,主編. 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
[7][奧] 西格蒙·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論 [M]. 人民日報出版社,2005.
[8]謝艷明. 詩歌的敘述模式和程式 [M].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9]張葆全. 玉臺新詠譯注 [M].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37,39.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