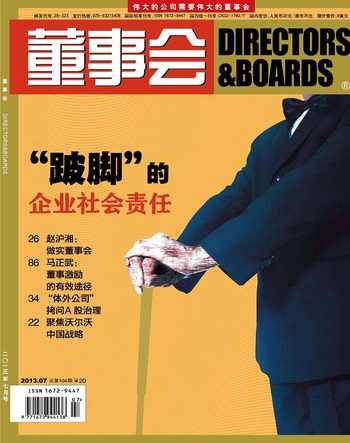“體外公司”面臨失控
崔自力
近期對于“體外公司”的各種討論日趨激烈,尤其是對于上市公司和擬上市公司:由于“體外公司”的存在,股東的利益被綁架或者掏空,直接影響到大量公眾投資者的利益;再加上證監會希望以嚴厲的審核手段把一部分排隊上市企業堵在堰塞湖之外,因此與此相關的“體外公司”問題才會引起如此廣泛地關注。非常有意思的是,對于內部人控制和上市公司誠信問題,國內開始關注的時點是在2012年,而美國是在2002年。與之相比,我們整整落后了十年!
“體外公司”百變財技
要想把“體外公司”的問題搞清楚,必須搞清楚“體外公司”究竟是什么,以及“體外公司”是如何運行的?
所謂的“體外公司”,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描述它:在形式上,“體外公司”往往具備獨立的法人地位,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而在實質上,“體外公司”的成立和運營往往以和某家公司(目標公司)特定的聯系為前提,通過設定好的機制,可以實現兩家公司之間利益和風險的輸送,從而兌現“體外公司”的特定目的。
實踐中,“體外公司”與“目標公司”可能具有某種產權上的聯系,也可能完全沒有關系。一般意義上講,“體外公司”應該是“目標公司”里的某些人員(可能是某個股東,也可能是某個核心管理人員)在體外另行設立的獨立公司。但在實踐中,這些“體外公司”既有可能是某個內部人擔任法人或者股東,也完全有可能只是農村的一群老太太擔任其股東。但是“體外公司”一定會在實際控制權和收益權上,存在高度的指向性。探究兩家企業是否存在關聯關系,目前只能通過公司名稱或者股東名錄查找線索:一般兩家關聯企業在名稱上或有相同的元素,或者股東名錄上有交叉關系等。例如,此前曝出的上海家化體外公司事件中,上海家化和上海家化生物科技、上海家化露美商貿就具備相同的元素;或者兩家關聯企業在股東名錄上存在交叉,在“易事特公司體外公司”案例中,就是發現存在多家同樣從事電源銷售,且法定代表人(或聯系人)與易事特員工“同名同姓”的身份不明公司。難點在于,同名同姓的關聯關系還好追索,而對于完全實行股權代持的關聯關系,目前還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
“體外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可能傳輸的是某種利益,也可能是某種風險,最終“體外公司”通過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等獲益。以傳輸風險為例,一般是“目標公司”通過對“體外公司”的風險承擔,使得“體外公司”可以獲得無風險收益。比如,“目標公司”進行初始投資,把已確定收益的追加投資機會讓渡給“體外公司”,此外還有委托擔保等。
在利益與風險傳輸實現方式上,可能通過直接的關聯交易,也可能是通過間接的方式。尤其是兩家公司不能明確為同一控制人,通過第三方實現,將增加監管的難度。例如,“目標公司”可以授意其供應商溢價采購“體外公司”的產品與服務,從而提升“體外公司”的收益。體外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的利益輸送,也可能只是通過某種默契,例如某些行業的招標,往往只有通過特定的中介進行投標才有可能中標。
對上市公司來說,還有一種重要的利益輸送方式,那就是利用內幕信息,采用“體外公司”進行提前操作,實現在“體外公司”的不正當得利。例如在“寧波聯合事件”中,盛泰聯屬于寧波聯合的高管體外公司,寧波聯合從未對外公開披露過兩者之間的關聯關系。盛泰聯通過利空吃貨,提前囤積了寧波聯合的股票,為其以后套現做了最好的準備。
除弊興利當用重典
“體外公司”的突出特點,決定其廣泛存在和普遍運行具有危害性大、隱蔽性強、監管難度大等問題。
“體外公司”最直接的危害是損害了“目標公司”股東的利益,也損害了相關利益者,其廣泛存在還必將損害資本市場的整體利益。至關重要的是,“體外公司”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和正義。“目標公司”與“體外公司”的利益輸送并非零和的游戲,往往“目標公司”失去的利益要遠遠高于“體外公司”的獲益。例如,去年網絡媒體曝光的某鐵路項目招標中,某招標中介公司(體外公司)因為可以影響招標結果,于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拿到中標金額的一半還多。 “體外公司”既壟斷內部信息,又壟斷了特定的交易權,極大地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正義,是市場經濟下的害群之馬和蟻穴蛀蟲。
由此,對于“體外公司”的監管,一定要嚴格責任追究制度,治亂世當用重典。中國當前的“體外公司”和內部人控制現象已經甚囂塵上,必須從制度層面予以高度關注,避免局勢的日漸惡化!2008年出臺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明確了對于內部人控制的監管機制,但是并未明確相關的刑事和民事責任。于是,在執行中就出現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現象,從來沒有形成制度的威懾力!
治理“體外公司”需要在立法上體現“揭開公司的面紗”,注重實際控制權而非產權關系,從實際控制角度界定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聯關系,把“體外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的體外交易,納入到關聯交易監管的范疇。事實上,美國當代在立法實踐中,已經非常關注以實際控制權而不是產權,來界定企業的責任。
此外,應把反不正當競爭引入“體外公司”的治理中來,無論是“體外公司”侵害“目標公司”的利益,還是集團公司侵害下屬子公司的利益,損害的都是市場經濟的公平和正義,必須當作不正當競爭予以嚴控。
如果一個企業爛了,就打碎這家公司;如果一個市場爛了,就重構這個市場。中國資本市場也許已經到了重構底層建設的十字路口,沒有從根本上的興利除弊,等來的只能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形勢下的不斷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