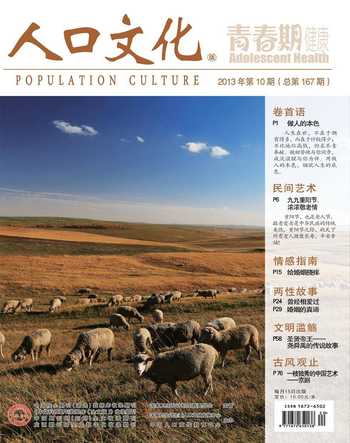水墨間的行吟
冉偉嚴(yán)



畫家介紹:蔡寶會(huì),河北省霸州市人,畢業(yè)于河北大學(xué)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師從許鴻賓先生,省美術(shù)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現(xiàn)任霸州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長(zhǎng),霸州市書法家協(xié)會(huì)主席,霸州市書法、國(guó)畫藝術(shù)研究會(huì)主席,霸州市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曾兼任市美協(xié)主席。現(xiàn)就讀于中國(guó)國(guó)家畫院吳悅石導(dǎo)師工作室。
好的中國(guó)水墨畫總有一種“穿越”的力量。這穿越,是透過(guò)形色穿越了心;是透過(guò)時(shí)間與空間,將此間的你,穿越到彼岸。所謂“心飛揚(yáng)、思浩蕩”, 所謂“澄懷觀道”,大抵若此。
所以,蔡寶會(huì)的工作室設(shè)在一個(gè)四合院里,會(huì)讓人覺(jué)得合適,典型的北方平原上的四合院落,過(guò)門洞的墻壁上掛的不是農(nóng)具,不是金山銀水,而是一幅中國(guó)水墨,一腳踏進(jìn)這個(gè)院子,心隨之放了下來(lái)。
水墨畫是讓人“放心”的。人心的變化是一個(gè)玄機(jī),它的陰晴冷暖、跌宕起伏,比天空和海洋還要敏感更多、細(xì)致更多、豐富更多。梵高的《星空》可以讓心狂熱,修拉《大碗島的星期日下午》可以讓心在細(xì)膩的沙線間變得冷靜,雷諾阿《紅磨坊街的舞會(huì)》又讓心變得嫵媚。所有這些感知,都是那么美好,而能有一種超然安詳?shù)拿篮茫瑓s非中國(guó)水墨不能使之然——那叫“放心”。
內(nèi)心惶惶不放心是常態(tài),所以,孔子論修為的目的在于“修己以安人”, 以個(gè)人言,修為自己是為了讓擔(dān)心你的父母、兄弟、朋友放下心來(lái);以社會(huì)語(yǔ),修為自己是為了讓百姓安居樂(lè)業(yè),社會(huì)安定祥和。修己與安人,正是天平的兩端,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教給我們的生存智慧,就在于把握這兩端的平衡。把握住一種平衡狀態(tài),則“風(fēng)也不動(dòng)幡也不動(dòng)”,內(nèi)心充盈安然的喜悅。
蔡寶會(huì)是一位孜孜不倦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并不厭其煩地以中華傳統(tǒng)熏染自己的畫家。他說(shuō):“假如荷花荷葉是中國(guó)的繪畫,那支撐她的支桿,不就是中國(guó)的書法么?而下面的漫漫池水,不就是泱泱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嗎?沒(méi)有深厚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作底蘊(yùn),何談書?又何談畫?”他把修己安人的人生哲學(xué)幻化于水墨,墨的黑與宣紙的白是兩端,用這兩端把五彩世界“化”入水墨天地,而他,在水墨間行吟。中國(guó)特有的宣紙,有著奇妙的滲化功能,就在這奇妙的滲化之間,水與墨交融,墨與白達(dá)到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干、濕、濃、淡、焦——不斷調(diào)和,從絕深的焦黑,到一無(wú)所有的白,變幻出數(shù)個(gè)層次和過(guò)渡,這種黑與白的組合就有了玄妙的不確定性。墨演繹出無(wú)窮奧妙,充滿神秘與遐想,又可遇而不可求,這樣的筆情墨韻帶給人一種出其不意的愉悅。
見(jiàn)他剛剛完成的一幅八尺作品《荷香入夢(mèng)》,一池濃碧的荷葉,一曲節(jié)奏分明的墨之交響,或鏗鏘落墨如墜,或恬淡墨淺似云;幾株亭亭荷梗,一點(diǎn)“紅顏”,巧妙的留白,是天空,也是池水,更是可以無(wú)限想象的空間。水與墨之運(yùn)用,光與色以及陰陽(yáng)向背,盡在其中。
又見(jiàn)工作室的一面墻壁上掛著四幅寫意“荷花”系列,皆四尺。我沒(méi)有問(wèn)這些畫是什么時(shí)間畫的?畫家也沒(méi)有更多的解釋。其實(shí)很多時(shí)候,我們?cè)谝环鶎懸馑埃遣恍枰嫾易约焊嗟慕忉尩模皇菃幔匡h逸之姿,雋秀之氣,沖淡之趣,高古之雅,全在那幾筆墨痕里。寫意,看似“不經(jīng)意”,實(shí)是“經(jīng)意之極”,是積累之后的釋放,是沉淀之后的凈化,是一個(gè)畫家經(jīng)過(guò)歲月的錘煉表現(xiàn)出的對(duì)人生獨(dú)到的體味和把握。透過(guò)畫面品味一種“氣息”是中國(guó)畫的審美享受。古人謂畫分四品:逸、神、妙、能——但怎么能將作品斷然分成這是逸品那是神品呢?一幅上乘寫意水墨,是將逸品的意境、神品的學(xué)養(yǎng)、妙品的空靈、能品的情趣呈現(xiàn)給了觀者,這些,是中國(guó)筆墨的內(nèi)在血肉和情感的文化屬性。本來(lái),墨寫之形,很有限,像葉、像花、也可以像石頭,但無(wú)論像什么,有了筆墨就有了形,有形就是有限。而寫意的玄妙就在于它不讓你停留在這“有限”里,就是要介于似與不似之間,實(shí)現(xiàn)“舍形而悅影”,讓荷有盛放于天地之間的無(wú)限。與荷相對(duì)應(yīng)的,是一只自在安閑的水鳥,一只飛來(lái)飛去的蜻蜓。而這樣的對(duì)應(yīng),不正是生命追逐的美好無(wú)限而自由的狀態(tài)嗎?
寫意水墨是抽象的,畫家讓抽象性的線條,入了心象,由此構(gòu)成寫意水墨的永恒魅力。“萬(wàn)物皆吾也”,所以,一枝一葉,一花一鳥,都帶有一份只屬于自己的獨(dú)特情感,是“這一位”畫家的理解和表達(dá),而不是別人的,就是這份帶有畫家個(gè)人情感色彩的創(chuàng)作,讓我們內(nèi)心悅?cè)弧>驮诓虒殨?huì)的工作室里,看到一幅又一幅寫意花鳥,是一段又一段放心的喜悅。荷花,是清秀、飄逸的荷花;滿筐的櫻桃、兩只螃蟹,是清奇、恬淡、意趣橫生;藤蘿掛果,是勁健、疏野的筆情縱恣;即使一把壺一朵野花,也是簡(jiǎn)遠(yuǎn)而不失雋永……一種格調(diào)、一種氣韻、一種意境,就是這樣一種中國(guó)畫藝術(shù)中特有的文化氣息熏染你、凈化你,而且,一位畫家對(duì)事物感知的深厚亦或淺薄,對(duì)生命感知的廣博亦或狹隘,全在這筆情筆性。
懂得筆情筆性的畫家,怎么可能只是一個(gè)畫家?準(zhǔn)確一點(diǎn)說(shuō),蔡寶會(huì)又是一位藝術(shù)教育家。跟隨他學(xué)書法繪畫的孩子,從6歲到26歲,20多年間,大約也有幾百個(gè)了吧。現(xiàn)如今,這些孩子當(dāng)中,考進(jìn)清華美院、中央美院等美術(shù)專業(yè)大學(xué),畢業(yè)成為專業(yè)畫家的亦不在少數(shù)。一直到現(xiàn)在,依然有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家長(zhǎng)慕名而來(lái)求教于蔡寶會(huì)老師。這慕名,源于多年來(lái)霸州這個(gè)區(qū)域的人們對(duì)蔡老師為人與學(xué)識(shí)的認(rèn)可。他告訴學(xué)生:立品可醫(yī)俗,讀書可醫(yī)俗!而且,他對(duì)此身體力行,歷練多年的堅(jiān)持,成就了自己的繪畫和書法創(chuàng)作,更寫下許多美麗的詩(shī)行和美好的文章。
看到他多年以前畫的一幅用于教學(xué)的素描作品——細(xì)膩的線條描繪出的明暗深淺塑造了一個(gè)幾近完美的人像——才知道,蔡寶會(huì)早年就學(xué)于工藝美術(shù);才知道,通過(guò)他的中國(guó)水墨畫,除了感知到筆墨的含量,為什么可以有一種奇妙的構(gòu)成或者說(shuō)布局給人強(qiáng)烈的沖擊感。就是那些“荷花”,一枝荷,可以從一角曲折地行過(guò)半個(gè)畫面垂向相對(duì)的一角,有一點(diǎn)不可思議的美感,有一點(diǎn)陡峭。這陡峭,是畫家視角的凌厲,是“遷想妙得”,最終形成妙的留白,佳的布局,形成中國(guó)寫意的美。
其實(shí),畫家所要表達(dá)的生命感悟,就集中在這一支或者幾支線條、幾許墨色里,就是這幾支荷、幾條藤,卻負(fù)荷了無(wú)限深意,讓你覺(jué)得留白處的宣紙都不再是紙,而是通透,是有了生命的東西。杜牧寫“碧松梢外掛青天”,這是一種充滿空間感和想象的張力,蔡寶會(huì)在水墨間行吟的也是這樣一份張力,不穩(wěn)而穩(wěn),充滿動(dòng)感,于有限中見(jiàn)到無(wú)限,又于無(wú)限中回歸有限,讓水墨畫優(yōu)雅的意趣回旋往復(fù)。
(編輯 劉小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