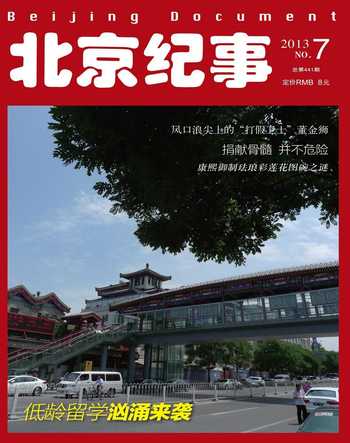什么是“最可靠的社會保障”
易明
歷史學者說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個時期非常好,看當時的大都市,開封有《清明上河圖》為證,杭州就不用說了,到了今天也是世界公認的好地方。但是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力強盛似乎不是一碼事,北宋從開國就面臨北方的問題,南宋被沒文化又強悍無比的金元壓得要死要活,最后連半壁江山也失去了。國將不國的刻骨銘心之痛,永遠留在宋詞大家辛棄疾、李清照的字里行間。
近來談中國夢的文章很多,從《中國文化報》看到周篤文的《詩詞中的“中國夢”》一文,又有了一些收獲,特抄它兩三段:
700多年以前,在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的杭州,在元兵壓境,危亡在即的時候,愛國詩人鄭思肖寫了《德祐二年歲旦二首》。其一曰:
力不勝于膽,逢人雙淚垂。
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
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
朝朝向南拜,愿睹漢軍旗。
這是我讀到的詩中最早提到“中國夢”的記錄。詩寫得很悲愴,大意是說,在這無力挽救亡國命運的時候,只有垂淚向人。心里縈懷著強國之夢,腦子里叨念著《詩經》中的下泉之詩。離人較近的太陽還看得見,遙不可及的高天就無法去打聽了。我天天朝著南方抗元的義軍跪拜,希望他們能凱旋。《下泉詩》是《詩經·曹風》的篇名,主要表現對太平盛世的向往。
鄭思肖(1241年~1318年)字憶翁,號所南,福建連江人,宋末愛國詩人、畫家,尤工墨蘭。名與字號皆宋亡后所取。“思肖”,即思念趙宋之意;字“憶翁”,意取永紀宋朝帝君;號“所南”,意取決不面北事臣于元。
所南先生是筆者敬仰的鄉賢,據說他終身未娶,以蘭為妻。少兒時家里蘭花品種多,花開得好,他揮毫寫生,靜觀默察,爛熟于心,凝思細想,下筆如有神。有一天晚上,他夢見蘭花仙女駕臨畫室,隱入筆管中,從此畫技突飛猛進。所謂的夢,就是白天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在睡夢中有了靈感,所南先生能在夢中得到啟發,是平時冥思苦想的結果,當然也離不開勤學苦練。歷史中都有傳奇,比如他家有好蘭是因為有一口好井(這井前十幾年還在,井深水甜)。當年曾經有一個遠來的道人,口渴向他的祖母討水喝,老人泡了一杯香茶送上,道人喝了很感激,指著園中說:“此處地下有一眼好泉。”說完就消失了。
其實說半天,是一個被人重復多次的道理,在中國,個人命運永遠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國家命運又離不開這生存了億萬年的江山。雖然社會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世道輪回,老思想仍然具有“啟示錄”的價值。
前幾天,去東三環麗澤橋附近的4S店保養車,這地方已經走過10年了,熟門熟路。可笑的是那天一出門就鬼使神差,沿著南四環奔西四環就去了,一路還在找過去記憶里的標志物,快開到西長安街才發現犯了“重大路線錯誤”。后來,聽交通臺知道,那天北京延慶、順義一帶,白天烏云密布如暗夜一般,街燈、車燈全開,瞬間下起大暴雨。京南這邊要下沒下,氣壓低,足以讓人的思維“短路”,好在及時走回頭路,向左向右,走到廣安門外的小井,自己先樂了。跟夫人說這是咱小學四五年級時,下農村勞動的地方,那時叫小井生產隊,冬天收大白菜,夏天還要插秧來一季水稻。
現在說這個跟做夢差不多,小井村附近還有一個大井村。當年沒有自來水,都是村民自己打井裝上手動壓水機,我們渴了就對著鐵嘴壓水喝。70年代初,學校組織我們去勞動,生產隊會用幾輛馬拉大車來接,從虎坊橋菜市口廣安門出關廂,兩邊都是田地。那時坐馬車是一道風景,車把式屬于技術工種,都有點脾氣。馬屁股后面的座位是我們最羨慕的地方,一般都上不去,馬鞭一般也不能碰。每個車上還有馬糞兜,馬一撅屁股車把式就停下來,忙不迭地撿糞,唯恐被人家收走了。現在想想那是最好的有機肥,馬吃的東西都干凈,高檔的精飼料豆餅是古法榨油的副產品,人吃也沒事,黑豆擱在中醫就是一味藥材。
其實,有適量沒污染的好東西吃,有干凈的水喝,有清新的空氣呼吸,就是“最可靠的社會保障”,足矣!錢財的索取和純物質的消費都該有度,人類的欲望必須節制。想想中國幾千年的飲用水和空氣,從未給人身體帶來致命的傷害,國家強大了和平了,祖國大好河山最不應出現的這些隱憂,讓人無法釋懷。
路透社的報道《農田污染威脅中國糧食自給》中提到:
中國南方城市廣州近日查出在售的大米鎘超標,這是中國一系列食品安全丑聞中最新的一起。毒大米事件為中國整頓食品鏈帶來更大的壓力,甚至可能影響到毛澤東所看重的糧食自給自足。雖然國內需求不斷增加,同時史上最快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吞噬了大量耕地。
這就造成了糧食供應追求數量而非質量,即便這些糧食是產自被工業廢水和不適宜人類飲用的水源嚴重污染的農田……雖然中國政府誓言要在主要的糧食供應鏈上實現自給自足,但根據美國農業部的預測,今年中國大米和玉米進口將再創新高,小麥進口也逼近歷史最高紀錄。
地方政府在上周晚些時候表示,廣州的質檢人員在抽檢中發現18個批次米及米制品中有8個批次鎘超標。廣州最后被迫公布鎘超標大米來自中國最大的稻米產區——湖南。
(摘自2013年5月24日《參考消息》)
吃飯的人多,勞動的人少,在過去就意味著坐吃山空。2012年,中國15歲~59歲的適齡勞動人口比上一年減少350萬。2011年底,60歲以上的老人達到1.85億,而到我們老齡化高峰時將會有4億老人,有8億勞動力。養老和就業將同時成為社會最復雜的問題,因此實現習總書記強調的“最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需要中華民族的大智慧。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唐鈞認為:我們養老保險的“雙軌制”是不公平的,但簡單地講“并軌”,這個思路可能并不能解決問題。因為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并不只是“雙軌”,我算了一下,大約有“七軌”。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軍人、企業職工、農民、城市居民,還有農民工。雖然農民工從理論上講,可以包含在城市職工這個范疇,但實質是不同的,所以總共是7種制度。大家呼吁要解決養老金“雙軌制”,沿著這個思路,似乎可以把城市職工和國家工作人員搞定了。但是,農民會不會出來說話,你們城里人自己捏巴捏巴就算數了?你們一個月拿好幾千塊,我才拿幾十塊錢,這不公平。
最近,著名的油畫《父親》正在國家美術館展出,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楊衛說:1975年除夕之夜,在遠離北京的山城重慶,一位過路知青被一個在茅坑旁邊收糞的老人形象深深觸動。透過節日的喧囂,這位知青與孤獨地瑟縮于寒風中的收糞老農迎面相對,突然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戰栗,產生了莫名的創作沖動。這種不可名狀的創作沖動,驅使這位知青日后創作完成了一幅著名的油畫作品,這便是羅中立和他的油畫《父親》。
油畫《父親》初次亮相是1980年,剛剛問世,便引來一片嘩然,成了社會各界談論的焦點。羅中立的油畫《父親》之所以能夠打動千千萬萬中國觀眾的心靈,就在于1980年左右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大時代的轉折點上,而羅中立的這幅油畫作品《父親》,將父輩的苦難與悲愴,凝結在情感的畫面上。如同20世紀20年代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一樣,都是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深情回眸,以人性中最感動的因素,賦予了幾代中國人對衰老背影的精神憑吊。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