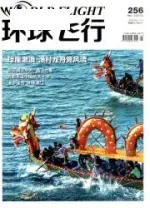朱知壽:中國朝陽鈦空追夢者
武晨



鈦,一種神奇的金屬,其比重接近鋼的一半,卻像銅一樣經得起錘擊和延展,在超低溫條件下也具有良好性能,并具有超導性。鈦合金還具有的高比強度、高熔點、抗高溫、耐腐蝕等特性使之成為制造業中的重要材料,更是理想的航空航天材料。
鈦在1791年就已經被發現,但由于鈦在高溫下具有很高的化學活性導致提煉工藝要求十分苛刻,直到1910年才首次獲得成功提煉。純鈦的強度很低(抗拉強度只有250MPa~300MPa),一般不宜做成工業實用價值的結構材料,只有通過在純鈦中加入一種或幾種合金元素、經真空熔煉,并再經熱機械處理、粉末冶金、焊接和鑄造等工藝方法制造成各種合金,才能真正可以用于工業領域。獲得這一突破的成功標志就是在20世紀50年代發明了Ti6Al4V等鈦合金開始的。相比銅誕生6000年、鐵誕生4000年、鋁誕生100年來說,鈦還是一種非常“年輕的”金屬,鈦產業也被譽為很有應用前景的“朝陽產業”,目前世界上也僅有美國、俄羅斯、日本和中國等幾個國家掌握了完整的鈦工業生產與應用技術。
先進鈦合金材料的大量采用是新一代飛機和航空發動機先進性的顯著標志之一,可大幅度提高結構減重效果和安全可靠性。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的航空用鈦量占鈦產量的50%以上,獨聯體和歐洲等國家的鈦產品也主要用于飛機和航空發動機,這充分說明鈦合金在飛機結構中的重要戰略地位與作用。
中國鈦材產業在最近的10年來得到了快速發展,我國海綿鈦年產量已突破5萬噸、鈦加工材已達到4萬噸的規模,產量分別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但相比世界發達國家,我國鈦加工材在航空航天的高端用量偏低,只占產量的不到10%,非航空用量卻占50%以上,產品結構比例嚴重失調,難以發揮出鈦合金作為寶貴資源和高綜合性能的應有作用。所以,如何進一步提升我國鈦合金在航空工業領域的用量和應用水平、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技術水平,是鈦合金研發和應用工作者面臨的當務之急。
中航工業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員、中航工業鈦合金材料技術首席專家朱知壽便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實踐者。朱知壽介紹說,我國自“九五”以來,加強了新型高性能鈦合金材料研制和應用研究的力度,強調自足國內、按系列化發展的研發思路,通過科技創新,縮短了鈦合金應用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此基礎上,既提高了我國鈦合金在航空工業領域的用量,又促進了我國民用鈦材深加工能力的發展,從而調整了鈦產業結構的良性發展方向,逐漸擺脫了“雜”、“亂”、“散”的被動局面。朱知壽同時指出,在我國傳統加工方式為主導的背景下,我國鈦合金在航空工業領域的材料利用率一直偏低,一般只有10%左右,而復雜鈦結構件的材料利用率就更低了,所以如何通過技術創新,發展并采用諸如粉末冶金、精密鑄造、超塑成形、先進連接、激光快速成形等先進加工技術,提高鈦合金構件的材料利用率,進一步降低成本,是提高鈦合金在航空工業用量的另一個技術關鍵。
朱知壽自從1991年投身航空用鈦合金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工作以來,已經主持完成多項國家重點科技項目和型號技術攻關項目,目前所帶領的“新型高性能損傷容限鈦合金創新團隊”涉及了十幾個項目,旨在推進我國航空用鈦合金材料系列化研究,提升航空鈦合金的應用水平和技術成熟度,發展新型高性能鈦合金材料系列技術,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研究團隊針對飛機用量最大的中強高韌和高強高韌損傷容限型鈦合金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工藝創新和材料創新,實現了中強高韌TC4-DT和高強高韌TC-21損傷容限型鈦合金在我國飛機關鍵承力部件上的裝機應用,這也標志著我國損傷容限型鈦合金在飛機關鍵承力部件上得到批量應用“零”的突破,從而也奠定了我國飛機結構鈦合金材料形成了“強度高低搭配、綜合性能優勢互補”的基本格局,滿足了飛機高可靠性和高減重的設計與應用目標,從而提升了我國飛機鈦合金用量及應用水平,并實現了從科技成果到產業化的轉化,產生了顯著的技術與經濟效益。
在此基礎上,研究團隊進一步開拓低強度高塑性鈦合金(Ti45Nb絲材)和超高強度抗氧化鈦合金(TB8板材、鍛件、絲材)的材料系列化研究領域,并已經在重點型號的鉚釘標準件國產化、鈑金零件和焊接構件中得到了大量應用。目前,研究團隊沒有停止創新的步伐,繼續拓展航空鈦合金系列化研究領域,堅持源頭科技創新,開展超高強韌和極限環境下新型高性能鈦合金的研究,繪制了一幅航空鈦合金從“低強、中強、高強、超高強和極限強度”系列化技術發展藍圖,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航空鈦合金材料體系、擺脫國外長期依賴,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朱知壽帶領的高性能損傷容限型鈦合金研究團隊,一步一個腳印,一步一個臺階,用自己聰明的智慧、赤誠的愛國心,在鈦合金材料這一“朝陽產業”中,不斷挑戰新的創新目標和材料極限,不斷向更高強度、更高韌性、更高使用環境極限和更高綜合性能挑戰,滿足未來航空飛行器對高性能材料和極端材料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