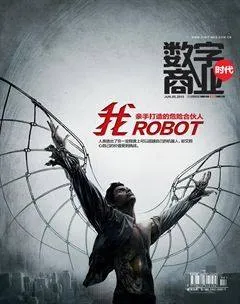阿里「選擇」了杭州
向坤
一場黃龍體育館的盛大演唱會過后,馬云引退了。不管怎么說,互聯網的江湖不會因為馬云的離開而寂寞,而江湖上雖然沒有馬云,但是關于馬云的故事還在流傳。
最近網絡上有這么一段視頻:年輕的馬云在北京跑國家體育總局時,被體育總局的干部冷眼相對的畫面,彼時是差不多近20年前的事了。事實是馬云在北京度過了幾年不得志的日子,最終移師杭州才完成了阿里巴巴大業。
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為何沒有留住阿里巴巴?作為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之一的阿里巴巴,為什么落腳杭州?這確實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經濟學上有所謂的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的說法。一個地方如果說優勢的產業要素比較集中,那么依托這種產業要素為發展基礎的企業就會集中在這一塊發展。回望阿里巴巴的成長歷史就會發現,相對于新浪、搜狐、百度早早依靠美國資本市場實現了財富急劇效應相比,阿里巴巴對資本市場的依托是最少的,阿里巴巴并沒有通過對資本市場畫出一個美好未來畫餅的方式來實現迅速成長。相對于新浪、百度都曾經有過很長時間找不到盈利模式的艱難日子,阿里巴巴的成長路徑和盈利模式顯得很清楚,在淘寶支付寶一個個阿里體系內的新招財樹生根發芽之時,給人們的感覺也是水到渠成而沒有生硬之感。這是由于電子商務是最為依托現實經濟的互聯網商業模式。杭州周邊的江浙有著中國最為龐大的產業鏈分工體系,溫州、常州有著無數個小型的加工企業和制造企業,這使得阿里巴巴一開始就擁有了發達的企業資源網絡。而發達的民間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使得這里的消費者信用意識比較強,更加能夠接受互聯網交易這種依賴人的信用意識的商業模式。馬云在告別演講中反復強調了信任,正說明了阿里巴巴對信任作為一個經濟要素的認識。反觀北京沒有這么發達的民營經濟體系,商業氣氛的相對薄弱使得阿里巴巴缺乏土壤。正因為杭州擁有信任、民營企業網絡等資源,交通物流體系相對較發達,使得集聚效應凸顯,綜合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另外,兩地的經濟模式和政府意識也決定了阿里巴巴沒有在北京生根發芽。北京是政治中心,政治資源的積聚使得北京多是大型國有企業的總部,集中了最為重要的資源。同時北京的金融機構也更專注于傳統的融資模式,融資擔保看重有形資源,融資客戶集中于大型企業。再加上政府的服務意識相對更加重視自上而下的管制。相反,杭州集中了大批的民營企業,江浙政府由于很早就意識到江浙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因此對民營經濟和新經濟模式的態度比較開明。政府的服務意識比較強,金融機構相對來說更加能夠接受獨特的商業模式和支持小企業的發展。這么多年來阿里巴巴得到的政府支持也是十分明顯的。
這么多年來,馬云特立獨行的性格一方面引來了人們的贊譽,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責和批駁。如果沒有江浙政府主管機構相對寬容的態度和江浙人務實重商的性格特征,馬云也不可能得到肥沃的土壤得以成長。而北京人由于歷史原因,各種限制比較多,天馬行空的思維模式比較難以得到人們的共鳴,四處碰壁也就不奇怪了。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互聯網行業中也仍然是這么一個規律。中國的互聯網三巨頭總部分居于北、深、杭三個城市,其實是有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和文化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