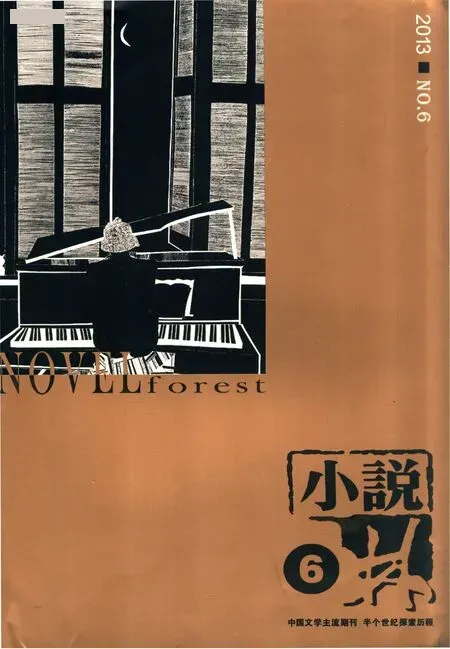力工
村里沒一個人不知道小金子愛美,別說只村子里,就是全世界男人紋眼線的也找不出幾個。他的父親氣得快瘋了,拎著鎬把一直追他到房東頭的包米地里,裂痕斑斑的鎬把當然是打折了。金子在炕上躺了近一個月,整個最忙的秋收他卻因此閑了下來,幾十畝的包米從收割到賣出,全由他父親和大哥干了。
金子有的是力氣,自從跟堂兄去縣里卡拉OK一次后,再不愿意干農活了。父親沒辦法,用賣包米的錢給他買了一輛摩托。村子到縣里路不好走,出租車很少跑這里,年兒節的村里人串門走親戚的甚多,都能用上他的摩托,一年下來金子掙得不比累死累活的父親和大哥少哪兒去。
金子不抽煙也不喝酒,錢卻沒給家交過一分,最近還經常夜不歸宿,摩托車倒是擦得锃亮,還學會哼哼葉凡的《相思》了。父親納悶,想兒子一定是被卡拉OK的哪個狐貍精給迷住了。決定給金子張羅婚事,鄰居家的狗兒跟金子一般大,孩子都三歲了。
金子長得很好看,他的眼睛即使不紋眼線,也少見的漂亮,因個子太矮,認識他的人都叫他小金子,他的全名叫金子龍。他父親常跟村里熟人說,我兒子就是個兒太矮,否則怕這個窮村子還真留不住他呢。相親那天,金子看過那女人一眼后,目光就再也沒離開過自己的腳尖。他整整三天沒跟父親說一句話。父親告訴他,丑妻進室家中寶,再說人家不嫌咱窮,相中的是你這個人,那個卡拉OK的狐貍精怕靠不住。見強壯的兒子幾天下來瘦了整一圈兒,父親妥協了,你去找那個相好問問,她要是不嫌咱家窮,又是農村,你就把她領回來,我認了。
初冬的第一場雪站不住,坑坑洼洼的路泥濘冰滑,金子的摩托摔了兩次,他媽媽給他洗得干干凈凈的米色夾克服沾滿了泥漿,來到縣里的星光大道歌廳時,服務生不讓他進去。金子等了半個多小時,紅兒才出來見他,她喝了酒,蓬松的短發亂糟糟的,身上該露不該露的地方都裸露著,紅色的長指甲間還夾著抽剩的半截香煙。
怎么,有錢了?紅兒乜斜著眼睛,也不管金子的衣服有多臟,急不可耐地就來扒金子的上衣。
金子一把拽住紅兒的手,別急,我有事兒跟你說。
紅兒的酒還沒醒,怎么能不急?你都多久沒來看我了,想死我了。
金子說,我爸給我找媳婦了,我要結婚了。
那你就結婚唄,金子的臟夾克已經被紅兒扯了下來,扔到了墻腳。
金子費了好大勁兒才推開紅兒,我這次是跟你商量正事兒。
你能有什么正事兒?紅兒不高興了,她還是第一次被這個農村傻小子拒絕。
金子說,我不想跟她,我想跟你過一輩子。
紅兒的酒一下子醒了,什么?你想讓我跟你結婚?別做夢了。
金子愣怔了,你不是說我好嗎?
紅兒叫道,我是說你床上的功夫好,不是說你的破摩托好、你家的破大坯房子好,我可不想跟你種一輩子包米去。
金子有些失望,你不喜歡我,為什么每次只要我五十元?
紅兒撇了撇抹得紫紅的大嘴說,我跟你在一起比跟所有別的男人都爽,少給點可以,沒錢可不行。
我也不愿意種包米,我可以干別的養你,我有的是力氣,金子還不死心。
開你的摩托養我,還是去站大崗?紅兒一臉的不屑。
金子也生氣了,除了那點好處,我就沒有別的一點兒好?我辛辛苦苦兩年掙的出租錢都給你了,我連一雙襪子都沒給自己買過,也沒給爸爸打過一斤酒,媽媽更是一分錢沒要過我的。
那不是你愿意的嗎?紅兒也沒好氣地說。
金子問,咱們每次見面你都給我唱《相思》,我還以為你總想我呢?
紅兒說,如果黑狗給我錢,我也給它唱。
金子回來后把自己關在屋里哭了三天,漂亮的眼睛從此蒙上了一層灰白的薄膜,夜晚看東西模模糊糊的,他比以前更不愛說話了。
第二年的春天,金子把全家的三十畝地抵壓給村里信用社,貸款蓋了三間磚瓦水泥的大房子,墻面貼了白瓷磚,房頂還扣了粉紅色的蓋板,絕對是全村子里最漂亮的房子。秋收過后,這個村子里最漂亮的男人和村子里最丑的女人結婚了。村子里有個習俗,結婚的當天晚上不能關燈,預示著往后的日子亮堂紅火,但金子還是把燈關上了。
妻子鳳兒比他高得多,力氣也大,三百多斤的公豬她一個人就能捆上,種地扛活樣樣不比金子差,就是拴不住金子的心。金子可不是頭公豬,他沒有精神生活可不行,結婚那天晚上他問鳳兒,你會唱《相思》嗎?
鳳兒說,我從不唱歌。
呵呵,金子的聲音透著失望。
結婚的第四天,金子就離開了村子。他跟父親說,他得去省城干活,還信用社的五萬元貸款。
父親金大海同意,知道僅靠種包米也確實還不上銀行的錢,也知兒子想離開媳婦兒。看著兒子灰蒙憂郁的眼睛,金大海想這門親事他可能錯了。
金子家離省城只有兩百多公里的路程,不到三個小時的火車,金子就到了省城,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金子有點發蒙。
金子的三姨在省城的一個小區經營一家小型超市,來之前通過電話,讓他在長途客運站的對面乘十四路公交,一直坐到終點下車。金子問路邊的出租車司機,大哥,十四路公交車站在哪兒?
司機說,在江橋的邊上。
金子問,我得走多遠?
司機說,那可遠了,如果你打我的車,也要二十多分鐘。
金子問,多少錢?
司機說,打表,估計沒多少。
金子把行李卷扔進了出租車的后備箱,坐在了副駕駛的位子上,發現后排座位上坐著一個膀大腰圓、一臉橫肉的中年漢子,脖子上掛著一條粗粗圓滾的金項鏈,看金子的眼神就像一條黑狗突然瞧見了一塊骨頭。
金子說,我不坐了,我還是找公交車吧。
司機說,小兄弟,你也太不講究了。司機說著話,車已經啟動了。
車行駛了將近三十多分鐘,計價器的數字每跳一下,金子的心就要急速地蹦三下,停到江邊的十四路公交車站時,計價器顯示是四十三塊錢。
大哥,要這么多錢啊。司機說,你第一次來省城吧,以后就習慣了。
后面的漢子兇巴巴地說,跟他費什么話,你他媽的快給錢,別耽誤老子的活兒。
這是十四路公交的起點站,金子很容易就找到了座位。車行了也就十幾分鐘吧,金子聽車內的播報提示:火車站就要到了,上下車的人多,請大家給下車的人讓讓。
金子愣住了,火車站?他問身邊的乘客,這是省城的火車站嗎?
那人答道,是啊。
金子問,那長途客運站在哪兒?
那人說,就在火車站的右側。
金子知道上當了,他又回到了剛才下車的火車站。
金子的三姨家在省城已經住了幾年,用金子媽的話說,她妹妹在省城是落穩了腳的。所謂的“超市”是一個能裝兩輛轎車的食雜店,前面用來賣貨,后面用軟間隔騰出一個上下兩層住的地方,金子的三姨和姨夫住下層,金子和他的表弟住上層,表弟在一家發廊學徒,每月也只有三百元的工資。金子的三姨真是個能人,第三天就給金子找到了活兒,在一家純凈水廠當裝卸工,沒休息日,每月九百元。
金子在村子里是有名的車軸漢子,這個活兒對他來說跟女人繡花差不多少。才工作不到一個月,金子就不想干了,也不想在他姨家住了。姨夫是個閑不住的人,夜闌人靜的時候,突然嘎吱嘎吱的聲音讓心事重重的金子睡不著。或許表弟比他小幾歲的緣故,或許他已經習以為常,金子可是過來人,他跟紅兒那陣子可比姨夫猛多了。金子算了一筆賬,中午在廠子里吃,每月得給三姨家交二百元,一個月再省也就能存下五百元,他得十年才能還上銀行的貸款。姨夫告訴他,省城里只要肯出力氣,活兒有的是,掙得多。
金子問,干啥?
姨夫說,力工。
水廠對面的不遠處有幾棟兩層高的裸樓,里面沒下水,沒取暖,也沒有廁所,上二樓要走鐵板搭的簡易樓梯,廁所就在房子的前面不遠處,兩邊的垃圾堆得小山丘一樣高,冬天還好,夏天路過的人都要捂著嘴鼻匆匆走過。這幾棟房子聽說是當地一個特別有錢的人投資的,他看好農民工租房這個市場,他顯然是成功的,幾年來房子幾乎就沒有空閑過。金子挺幸運,在一棟房的二樓租到了一間,中間有隔斷,有上水,有爐子,能燒火。鄰居是一個安徽人,快七十歲的獨身老頭,在省城收廢品二十多年了。他告訴金子,冬天也不用愁,撿的柴禾都用不完,碰到開博覽會什么的,閉幕時要拆除搭建的展臺或架子,燒不完還能賣呢。跟金子的三姨一樣,這個收廢品的老人也是個能人,二十年來不僅給兒子娶了媳婦,還給兩個弟弟娶了媳婦。老人是個慷慨的人,不怕金子搶了他的飯碗,極力勸說金子也干這個活兒。老人說,這個城市的人愛面子,寧可掙得少也不愿干這個活兒,別看他們穿得好,活要面子死受罪,當然真碰到有錢的主兒,那就發了,送你個彩電或冰箱就是個玩兒。
金子說,不干。我有的是力氣,你幫我找個力氣活,累點不怕,俺媽說了,沒有累死的,能多掙幾個子兒就行。
老頭說,那容易,明天我跟永紅建材商店老板說,讓你上那干活兒去。
永紅建材的老板娘胖胖的,不是金子喜歡的那種女人。她問過金子之后,就明白了,眼前這個敦實的小伙子除了種過地,開過摩托,看來什么也不會干。她說,瓦工、電工、水暖、油工你都不行,你就干力工吧。
金子問,都啥活兒?
老板娘說,扛水泥,扛沙包,砸墻,抬家具,拆架子,卸貨。
金子說,行。
沒過一個月,和金子一起干活的幾個工人就離不開他了。人家一次扛一袋水泥就氣喘吁吁,他一次扛兩袋,連上五層樓,腦門兒連個汗珠兒都不見,分錢時卻和大家一樣平均。哥們兒幾個發現他不太合群,大家累了幾天,找家小酒館整兩瓶啤酒的事兒,他從不參與。
時間也過得真快,不到四年的時間,金子就攢了整整五萬元。十年的貸款,金子只用四年就全部還清了。
金子的媳婦鳳兒也是真爭氣,只結婚晚上那一次她就懷上了,生了個鬼精靈的丫頭。這幾年金子每年春節都回家幾天,對妻子的要求也不拒絕,反正關了燈就把她當作紅兒吧。他還是想紅兒,他去縣里的星光大道問過,老板說紅兒早就走了,哪去了,不知道。
父親金大海發現省城是真掙錢,就跟金子說,咱家的地你大哥一人種就行,我和你媳婦也都去省城干活,你在那兒也有了根基,你跟別人干也是干,咱倆干那錢不就都成咱家的了嗎?給你媳婦也找個活,我看你小子現在也有這個能耐。孩子讓她奶奶先看著,明年也到省城去上學。
金子問,爸,你成嗎?那不是人干的活兒。你都快六十歲了。
金大海說,成,我比你還能干呢。
金大海也真不賴,父子兩人每月都能凈剩個五六千元。金子有錢之后,鳥槍換了“洋炮”,買了電鉆,砸墻再不用釬子和錘子了,他剛干活的時候生疏,錘子不小心常誤砸握釬子的手,左手背上的傷疤就像是一張中國地圖。他給妻子鳳兒找了個打掃公寓的工作,每月五百元,現在都漲到九百元了。金子可不是個安分的人,他還想攢錢去找紅兒,如果紅兒看他現在扛水泥、沙子的樣子肯定還是不成。昨天他給人抬家具,兩三個人才能抬上去的沙發,他硬是一個人背了上去,七樓啊,他以為最少能給他三十塊。屋里有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在喝酒,沙發放好后,金子問,大哥,你給多少啊?
一個戴墨鏡的男人,敞開的襯衣露著黑色的胸毛,你要多少啊?
金子小聲咕嚕了一句,三十塊。
那人說,我沒聽清,多少?
金子鼓了鼓勇氣說,三十塊。
你看你哪兒值三十塊,哈哈。金子被那個戴墨鏡的人一腳踹倒,又一腳把他踢得滾下了樓梯。金子在滾動中想起一個同行告誡他的話,如果碰到不給錢的人,千萬別要,一定不是好人,可別吃虧。
就像當年金子不愿再干農活兒一樣,他決定不再當力工了,他要找個體面的工作。永紅建材的胖老板娘很喜歡金子,幫他在一家藥店找了份賣藥的工作,底薪八百元,加上千分之三十的提成,一個月下來也一千五百多元。金子的女兒金春兒也接到省城上學來了,雖然掙得少些,也有了城里人的感覺。金子的父親金大海最近發現金子變化太大,晚上常回來得晚,還喝得醉醺醺的,問他,他說是老板請員工們喝酒。
其實這幾天金子都是一個人在喝酒,他太想紅兒了,他實在喜歡不起來自己的妻子,不會說話,不會唱歌,也不會打扮,長得跟家里后院剛從地里起出的土豆似的。前不久他接待了一個女人,活脫脫地就像從紅兒臉上扒下來的,年齡雖然快四十歲的樣子,風騷的勁兒比紅兒還更勝一籌。她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買那種男人吃的藥,金子知道,她對他也有意思,每次接藥時都要順便摸一下他的手。金子很苦惱,他不太敢相信這個穿著時髦的女人會看上他。金子是個寡言的人,什么事兒都放在心里不說出來。她每個星期都要來買藥,可這個星期到現在還沒來,金子特別喜歡她摸他手的那一瞬間,像過了電一樣,酥酥的、癢癢的,腿都軟了。
想什么呢?愣愣的,給我拿兩盒六味地黃丸。金子朝思夜想的女人突然來到了面前。
金子掩蓋住興奮,聲音有點顫抖,你怎么不買經常用的那個西藥了。
那個女人說,這個是我用的。
金子說,還是吃中藥好。
女人說,一直沒問你的名字。
我叫金子龍。
噢,挺好聽的。她接藥的時候仿佛無意間摸了一下金子的手,金子整個的身子倏地顫動了一下。那女人好像感覺到了似的,低頭輕輕一笑。她問,你帶手機了嗎?
金子說,帶了。
我著急打個電話,我手機沒電了,能借用一下嗎?
金子巴不得有這種搭訕的事兒,當然當然。
那女人用金子的手機撥了一個號碼,聽了一會兒,說,沒人接,算了,過后再打給他吧。
快下班的時候,金子的電話突然響起。金子一看,是一個陌生的號碼。誰啊?
上午去你那兒買藥的,一個女人邊說邊呵呵地樂著。
金子聽出是誰了,也知道今天借他的手機是為了盜他的號碼,心怦怦急速跳了起來。
我聽說你原先是力工,你現在還干嗎?
金子忙答道,掙錢誰不干。
那女人說,我這兒有點活,我自己干不了,你能幫我嗎?
金子急忙答應,行啊。
那女人說,那你來吧,我給你馇粥喝,我叫馬麗,你以后叫我馬姐就行。
馬麗好像剛洗過澡,波浪的頭發披散著,穿一件軟塌塌的睡衣,赤著腳,趿拉著一雙膠拖鞋,腳的指甲涂著鮮艷的紅色。金子在村子里哪見過這陣勢,跟紅兒干那事兒的時候是在她的宿舍。屋子里的家具很簡單,一室一廳的房子,沒有廚房,是一間單身公寓。
金子問,啥活兒?
馬姐說,也是力氣活兒。
金子說,我沒回家,沒帶工具,得看啥活兒,技術性太強的我干不了,我是力工。
馬姐癡癡地笑著,這活你肯定能干,工具你隨身帶著呢。
金子愣怔怔的,還是沒明白。
馬麗過來拉著他的手,來,到里屋來。
臥室很小,一張雙人床上鋪著土黃色的床單,旁邊是一個立式的鋁合金衣架。馬麗半坐半仰在床上,乜斜著眼睛,神情像極了當年的紅兒。金子覺得血液突然在體內爆躥起來,明白這個女人要他來干什么活兒了。金子曾跟村子里唯一的好朋友狗兒說過,他就是喜歡城里的女人,他就是喜歡漂亮的女人。他問狗兒,我錯了嗎?
狗兒說,沒錯,可你太矮,家又太窮,人家未必真喜歡你。
金子說,我不管她喜不喜歡我,我喜歡她就成。現在有個漂亮女人主動喜歡他,這可是金子做夢都沒想到的美事。
馬麗把金子拖到床上,一點一點地解開金子的衣服,古銅色的繃緊結實的肌肉,在昏暗的燈光下性感撩人,他常年干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舉重運動員的肌肉還健美,沒有一點多余的脂肪,如果金子有一米八零的個頭兒,如他父親所說的,村子里還真留不下他,可惜他身高還不到一米六零。金子這幾年除了干活,攢錢還銀行的貸款,夫妻那事兒只過年回家做過,做也是潦潦草草,應付了事,盡一個丈夫的責任罷了。這堆干柴一旦燃起,必烈焰熾熾。金子像頭公牛一樣把馬麗撲在床上。
馬麗喊道,你去把燈關上。
金子說,不,我要開著燈,我要看著你。他呼哧呼哧地喘息著……
門突然間咣當一聲撞開了,別動,警察。金子嚇得像堆爛泥癱在了床上。
馬麗已經穿上了睡衣。警察對金子說,穿上衣服,跟我走。
金子清醒些了,大哥,別這樣,她讓我來的。
警察說,我知道是她讓你來的,否則你怎么能找到?說吧,一次多少錢?
金子說,她還沒跟我談錢的事呢。
警察又問馬麗,他給你多少錢?
馬麗說,五十元。
警察說,你可真賤,五十元就讓他上了,真便宜了他。
金子說,她沒要錢。
警察說,她是我們那掛了號的,就靠這個生活的,怎么會不要錢?你是要拘留十五天,還是要罰款?
金子說,可別拘我,家里和藥店知道了,多丟人,我認罰。
警察說,還知道丟人?念你初犯,三千元吧。
金子也老實,我今天剛開工資,就一千五百元。
警察問,真的?我搜搜你的衣服。金子今天剛開工資,正好是一千五百元。警察數了數錢后,說,便宜你了。拿著衣服快滾。
金子灰溜溜地下了樓,下意識地看了看馬麗住的窗子,燈突然滅了。金子在樓下待了有半個小時,那個抓現行的警察也沒有下來。金子恍然明白,他們是一伙的,他上當了。金子甚至懷疑剛才那個人不是警察,是冒充的,可那銀色的警徽一點不像假的,還有胳膊上的臂徽也不像假的。金子蒙了,又羞又悔,揮手給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
到家的時候,已經夜半了。金春兒還沒有睡,她在等爸爸回來,爸爸,明天要交今年的借讀費一千五百元。
金子說,管你媽媽要去。外地孩子在省城上學,小學每年都要交三千元的借讀費,由于農民工集體上訪,今年外地農村的孩子,借讀費減半兒。
金春兒又說,老師要我們添家庭成員表,你的職業一欄怎么添?金子說,農民,噢,不,是力工。
金子是個寬容大度的人,馬麗給她打電話解釋那天的事兒,金子說別說了,那天即使不發生那件事兒,他也會給她錢的,因為他是男人,但不會那么多。
馬麗好感動,說,你以后有錢沒錢都可以來看我,我的小門永遠是朝你敞開的。
金子說,還小門呢,你這個年齡都是大門了,誰都可以進,我就不去了。說歸說,金子還是經常去看馬麗,他喜歡漂亮的女人,喜歡馬麗的巧嘴,馬麗也真的開始給這個傻小子馇粥喝了。
妻子鳳兒最近覺得不對勁兒,金子跟她已經完全沒了那夫妻的事兒,晚飯也常不回來吃。問他怎么回事,他總說藥店老板請他們吃飯。父親金大海也覺得有問題,但一想起兒子的眼睛,心就疼,也不愿深究。鳳兒是個孝順的好兒媳,見公公不管不問,也只好忍氣吞聲。
被馬麗坑騙過和接待過的客人,少說也有一公交車了,她真是打心眼里喜歡這個三十歲的農村傻小子,從第一次做那事兒到現在為止,還沒一個男人和金子能比。他經常聯系的老客戶,因為金子總來的原因,和她也淡薄多了。金大海對金子的要求是,每月最少要上交一千元錢。金子覺得這個要求也不過分,一家四口,也不能太不顧家了。那面又怕對不住馬麗,金子是徹徹底底被馬麗俘獲了,他曾向馬麗發過誓言,為她死都行。金子為了多掙幾個子兒,放棄了藥店的工作,又開始了他的力工生涯。
轉眼到了春節,金子的大哥來電話說,今年的包米漲價了,收成也好,家里殺了一口豬,還弄了很多別的年貨,希望他們早點回來。
金子跟父親說,我今年不回去了,初三過去,就有活了。春節別的力工都回家,活就都是我的了。
金大海想也是,兒子今年拿回的錢太少,明兒開春金春兒還得交借讀費、書費和什么其他的他也弄不懂的亂七八糟的費用,房子租賃費也漲了不少,兒子在省城前幾年不都是一個人過的嗎?叮囑他如果有大活兒一定通知他,好極早回來,然后才放心回家。
春節馬麗也沒有回家,她從沒跟金子說起過她的情況,金子也不問。除夕那天他們晚飯后去卡拉OK嚎叫了半宿,金子除了會唱一首《相思》就不會唱別的,最近剛學的《陪你一起看草原》,唱得就跟狼嗥似的。金子除了干活,一分鐘都不愿離開馬麗。馬麗的心思呢?金子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愛馬麗勝過紅兒,這就夠了,馬麗年紀大了些,但比紅兒會說話,也比紅兒成熟漂亮,這就夠了,他一個力工,人家不嫌他,這就夠了。過了初五,一些小活兒還真是不斷,每天都能賺個五十八十的,也都趕著掙趕著花,留不下。
農歷的二月初二剛過,金大海忙趕回了省城。他收到金子發的短信,說有朋友給他聯系了大連的活兒,他已經去大連了。金大海忙給兒子打電話,可兒子就是不接,后來干脆把手機關掉了。金大海回來去找藥店的老板曉泉,金子在他那工作的時候,他們的關系一直很好,想金子可能會跟他說些什么。
曉泉告訴金大海,金子是跟一個女人走的,但沒告訴他馬麗的名字,并一再叮囑金大海別告訴金子的事是他說的,那樣金子會恨他一輩子的。
金大海說,拜托你跟金子多聯系,告訴他妻子可以不想,我和他媽都可以不想,他不能不管女兒金春兒,找個后爹能對她好嗎?
曉泉說,我如果能聯系上他,一定照你說的勸他。
幾天后,曉泉還真跟金子聯系上了,他把金大海的話都照原樣說了,又勸說他許多別的話。
金子只給他回了一封短信,謝謝大哥,我不是不想回去,我也很想念家里和孩子,但我怕她傷心。
整個正月,金子晚上都跟馬麗在一起。馬麗最近聯系的人少了起來,她雖然喜歡金子,但也不想在他身上倒貼。金子既離不開馬麗,又怕父親回來見他拿不回一分錢生氣,心生憂愁。
馬麗說,我要去大連,你去不去?我韓國有親戚,我能帶你去。
金子高興極了,真能出國?我不是說過嘛,我為你死都愿意,你只要帶我,我哪兒都去。
馬麗說,你誰都不想,能不想孩子嗎?
金子說,不想,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啥都不想。
馬麗說,我沒錢了,路費是個問題。
金子說,沒事,我想辦法。
金子來到了血液采集站,化驗的指標棒極了,醫生夸他的血液質量真好,誰要是能補到他的血液,那可真是天大的福分。金子高興地說,那就多抽點,最少也要抽三千元的。
醫生說,那可不行,一次抽那么多,你會死掉的。
金子問,那最少要幾次?醫生說,你身體好,最少也得兩次吧,下月再來。
金子哀求道,大夫,我著急出門,就下星期,行嗎?
醫生說,看你身體好,依你吧,但你最近不能干活。
金子說,行。
粗粗的針頭插入金子那黝黑多毛的胳臂時,他整個身子本能地顫抖了一下,緊緊閉住了眼睛,腦海里浮現出他跟馬麗第一次干那事兒的情景,粗大的標著黑色刻度的針管太像自己褲襠里的家伙了,只是這個東西是冰涼刺痛地插入。金子想,抽血和干那事兒差不多,挺舒服的。第二次抽血后,金子卻感到了天旋地轉,腳下軟軟的,像踩著棉花,又像是喝醉了酒。這個隆冬大雪天里都要敞著懷走路的熱辣漢子,突然變得異常地怕冷,頭縮進油臟的軍大衣領子里,侵襲進他皮膚的寒風像千萬柄鋒利的刀片在他骨縫間剮割著。
過了春節,農民返城務工,學生回省城上學,火車站的人群擠攘得喘不過氣來。金子排了整半天的隊,真夠幸運的,當天晚上的一輛慢車還有余票,售票員問,臥鋪還是硬座?
金子說,一張臥鋪,一張硬座。金子覺得他是個男人,他不能讓他心愛的女人委屈了。
金子和馬麗來到了大連,先在站前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了。晚上的房事一塌糊涂,兩次大量抽血之后,他變得無精打采,心有余而力不足。馬麗說,我為你得罪了那個警察,我不得不出來混,原先一直是他在罩著我。
金子問,那咱們不出國了?
馬麗說,出什么國呀?我還得做事。
金子問,那我干什么呀?
馬麗說,你幫我到站前拉客。
金子說,我干活養你,賣血也行,你別做那個事兒了,我會傷心。
馬麗說,指你能掙幾個錢兒。你明白嗎?我不能一輩子只吃一道菜,再好,也會膩煩的。
金子想了想說,我想跟你過一輩子,如果不成,就離開你,讓你也傷心。
我靠賣身養活你,你還讓我傷心?沒良心的。馬麗用手指著自己的胸口,我這樣的人還會傷心嗎?
馬麗接著教導金子,你找個發夫妻保健品宣傳單的活兒,做掩護,只給下車的單身旅客,哪個旅客熱心地和你閑聊,十有八九就是咱們的道中人啦。你可拉扯他到僻靜處跟他談價格。
金子問,啥價?
馬麗說,你看我這貨色,怎么也不能低于一百元吧。
金子知道馬麗是在暗示對他有多么恩惠,他一直是在享受著五折的價格。
金子不情愿,又不舍得離開她,這幾天晚上馬麗對他頗不滿意,昨兒一夜整個兒就是一個背靠背。
生意比金子想象的容易,他每天給馬麗拉客三個是最少的,吝嗇計較的有,更多的嫖客還是蠻慷慨的。一個月下來,金子估摸著馬麗最少也能賺到一萬五千塊。馬麗每天給金子的錢除了火車站到旅店的往返車費,所剩無幾。想金春兒已經開學,這時候是家里支出最多的時候,就鼓足勇氣說,姐,借我兩千元錢,行不?金春兒要交借讀費和書費。
馬麗說,我把錢都交給一個朋友幫我辦去韓國的手續了,手里緊著呢,你有吃有喝的就行唄,等下月再說吧。
金子最近不用再去車站接客了,馬麗的相好多得都經常撞車了,有個中年男人好像挺有錢,給馬麗在老虎灘的海邊租了個公寓。金子現在每天的活兒就是給馬麗和她的相好叫外賣或去干洗店送衣服,每天早上去倒掉衛生間使用過的廁紙。馬麗再不讓這個農村傻小子靠近她的身邊。
金子憔悴了許多,看上去像三十七八歲的樣子,臉上有了皺紋,鬢角也有了零星的白發。夜半躺在客廳的沙發上,聽著臥室里時斷時續傳來興奮的叫聲,金子知道馬麗夸張的叫聲是在提醒他,她不需要他為她去死,她可不是那么狠心的人,她需要他悄悄地離開,不提任何要求地悄悄離開……
春末夏初的時節金子回到了省城家里,看兒子氣色晦暗精神萎靡的樣子,父親金大海一時間不知說些什么。
金大海把金子的媽招了來,照顧孫女金春兒和兒媳,他是拼了老命了,都六十多歲了,他本來只干砸墻、砸洞和鉆眼下線的活兒,現在什么扛水泥、裝沙子、抬家具都搶著干,最近他靜脈曲張更厲害了,原先只是小腿肚子的毛細血管一團團地擰在一起,現在都發展到大腿的根部了。去醫院看過,醫生說得手術。金大海說,不行。現在家里沒勞力,一家四口人呢。
可能分別得太久,金春兒瞧金子的眼神有點陌生,她怯怯地說,爸,學校明天要交借讀費。金子說,管你媽要去。
金子的妻子鳳兒躺在家里還沒完全好,上個月紅博廣場糖酒會閉幕后,鳳兒去搶拆展臺和卸架子,她也真能干,扛回的木方、門板估計兩年也燒不完,她被一個突然倒下的大柱子砸了腰,現在勉強剛能下坑,家政早就把她給辭退了。
作者簡介:肖剛,男,1965年春天出生,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作品散見于《飛天》、《詩林》、《小說林》、《人民日報》、《北方文學》、《青海湖》、《中國詩人》、《歲月》、《三月三》、《黑龍江日報》、《黑龍江畫報》、《新晚報》等報刊。1993年獲《飛天》詩歌、散文大獎賽三等獎,2000年獲《詩林》詩歌創作優秀獎,2011年獲中國首屆旅游散文大獎賽二等獎,2011年獲全國散文論壇大獎賽三等獎。著有詩集《航行》,詩文集《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