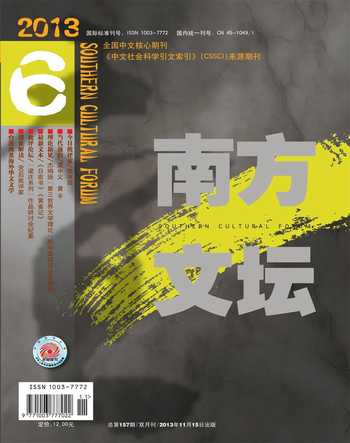罪與罰
沉寂四年之后,蘇童終于發表了長篇新作《黃雀記》(《收獲》2013年第3期),再次引起文壇的關注和廣泛的贊譽。小說重新回到了蘇童寫作的地理坐標——“香椿樹街”,“南方屹立在南方,香椿樹街則疲倦而柔軟地靠在我一個人的懷抱里。多少年過去了,我和這條街道一樣,變得瘦弱而又堅強”①。潮濕、寧謐的香椿樹街,對于蘇童似乎有著地理與精神的雙重意義。當初蘇童從“香椿樹街”出發,成為聲名卓著的當代文壇的重量級作家,二十多年后,《黃雀記》選擇重回“香椿樹街”,延續“香椿樹街系列”,本身就表明了這部小說之于蘇童的特殊意義。
一
蘇童的作品從《妻妾成群》《紅粉》《米》《我的帝王生涯》一直到幾年前的《河岸》,總是與歷史書寫緊密相關,以個人化的敘事不斷地切入歷史、表現歷史、闡釋歷史,個體生命沉浮于歷史的幽暗深處,賦予蘇童小說迷魅般的魔力。這部《黃雀記》卻似乎不再著迷于歷史的敘事,而將目光投注到了并不遙遠的80年代和80年代的“成長故事”,講述了發生在80年代的一件青少年強奸案以及當事人的成長與碰撞。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或成長小說是西方文學史上重要的小說類型,從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漫游時代》,到《大衛·科波菲爾》、《湯姆·瓊斯》,再到《鐵皮鼓》,都是在時空的轉換中描寫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主人公經歷了巨大的精神危機之后,最終長大成人,人格完善。這種類型的成長小說,在中國似乎并不多見,而《黃雀記》讓我們看到了與西方成長小說相通的精神氣質。主人公成長階段的迷茫、激情、浮躁,同時,又難以脫盡的單純、怯懦與善良,都在《黃雀記》中不斷呈現。小說中的保潤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少年,正經歷著青春期所帶來的蛻變。而經歷了十年牢獄生活之后,保潤的打扮讓他粗野的底層身份昭然若揭。面貌的變化或許只是淺層的,沒有改變的是他善良本性。兒時的沖動造成了他命運不可逆轉的偏航,經歷了少年時期的迷茫、激情、浮躁,他沒有像仙女那樣恨這個世界。他找到柳生并不是為了報仇,只是想讓柳生帶他去井亭醫院看望祖父。他對于親情,抑或說是人間的感情仍抱有期望,所以當祖父記不起他來時,他憤怒了,他木然了,他也想要失憶了。他說,“我還稀罕感情嗎?早不稀罕了。”②表面的暴力不能掩飾他內心的溫柔,當仙女因為妊娠反應在他懷里突然吐了起來的時候,“保潤任憑她的嘔吐物滴落在身上,茫然,……我在你眼里那么惡心嗎?”無力的反問抵消了他所有偽裝的仇恨,他的真實感情在此表露無遺。保潤放棄了自己的“復仇”計劃,還給她提供了一個安身之所養胎生產。“我們清賬了,不算朋友,也算熟人。”十年的牢獄之災僅僅通過一場貼面舞就化解了,僅僅因為知道仙女懷了孩子就煙消云散。
與保潤相比,柳生的一生看起來順遂,實則危機暗涌。他在水塔里強奸了仙女,他家能憑借著金錢打通的關系擺平公安和仙女家,讓保潤頂罪坐牢。可是法律上的自由并不代表生活上的自由,更不用提精神上的自由了。“他僥幸躲過了一場牢獄之災。他的生活被僥幸所定義了,……你的幸福全是撿來的,不要骨頭輕,你必須夾著尾巴做人。”從此他變得謙卑而世故,他接替了保潤的職責去井亭醫院照顧祖父,開始新的生活,一度也過得風生水起。可是他的命運不會僅僅停滯在這里,宿命般地與仙女重遇,又重新把他拉回到了本以為擺脫了的過去。
如果說保潤、柳生的成長經歷,基本上還不脫命運的軌跡,那么仙女(十年之后蛻變成了白小姐)的成長可謂波瀾迭起。仙女是被領養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缺失以及承擔了父母角色的爺爺奶奶的溺愛導致了她的野蠻驕橫。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使她不得不潑辣不講理,又使她極端的自私。她的人生雖然看起來金碧輝煌,霓虹炫彩,其實那閃爍著的光芒卻是指向虛無。三位主人公中,仙女的改變無疑是最大的,她從一個天真、野蠻、貪玩還帶著一些壞腦筋的小女孩,成長為一個美麗性感卻沒有羞恥心的人。一次意外懷孕,使她回到了這座曾發誓不會再回來的城市,在這里她再一次輸得一敗涂地,被所有人拋棄,只剩下柳生和保潤對她不離不棄。在他們細心的關愛和無形的感化下,白小姐重新又變成了那個曾經的她——仙女。命運在這里再次輪回。
可是,三個人的命運卻不會如愿朝著幸福的終點奔跑。他們的成長歷程不盡相同,或曲折,或順暢,或荒唐,都在青春的迷茫中,體驗著心靈的成長。三個人交織在一起、混雜不清的悲劇人生都早已注定,任憑誰都無法逃脫。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時代的巨變、人性的不測、日常生活的慣性,融入了蘇童對1980年代的思考,三位主人公的成長故事不再是偶然的命運故事,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義,讓我們看到了六七十年代香椿樹街上的少年長成之后,在80年代的必然命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黃雀記》才是“香椿樹街系列的一個延續。”③
二
《黃雀記》分成保潤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個部分來講述,這既是三個不同的敘事視角,又清楚暗示了三個人不一樣的人生經驗和情感體驗。保潤的春天是初生而又青澀的,柳生的秋天是市儈而又成熟的,而白小姐的夏天是強烈而又無可遮蔽無法逃離的。這些在他們的故事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其中第一部分《保潤的春天》是整部作品的鋪墊,作者有意展開故事豐富的橫截面,著力刻畫人物成長過程中的青澀、欲望與焦灼。可以說這一部分的時間是靜止的,命運的列車是在緩慢前行的。成長期的保潤、柳生和仙女都在茫然憧憬著自己的人生,為他們三個以后糾纏不清的命運埋下各種伏筆。精巧的結構暗含著作者預設的伏線,完美地交叉重合而又分離,人物命運的交織由無數看似巧合的必然緊緊牽引。三個敘事視角互為補充、互為鏡像,既線性描摹了人物的命運軌跡,又立體呈現了時代巨變。
保潤和柳生的初識其實就充滿了宿命性。他們是在井亭醫院認識的,保潤擅長用繩子捆綁病人,柳生以撮合保潤與仙女為條件讓保潤去捆他犯了花癡病的姐姐。仙女與保潤去溜旱冰而保潤賭氣先走,使仙女欠了他八十元旱冰鞋的押金。保潤為了討錢,把死不認錯的仙女綁在了人跡罕至的水塔里,導致了強奸事件的發生。保潤替柳生頂罪坐牢的時候,柳生曾說等保潤刑滿釋放,他們兩個“能和平就和平,要是不能,我跟他同歸于盡”,不料最后竟然一語成讖。保潤對于仙女青澀的愛情一直保留在心底,與仙女和解以后不僅沒有因為仙女扔了祖父找了后半輩子的手電筒而責怪她,還在淤泥里找尋的時候采了朵蓮花給仙女。在保潤的眼中,仙女永遠都是那個出淤泥而不染的她。最后,保潤誤以為柳生和仙女走到了一起,嫉妒和醉酒使他在柳生的新婚之夜捅死了柳生,自己重又回到了牢里。保潤與監獄之間的緣分其實是他不可逃避的宿命。正如蘇童所說,“他走出(監獄),最終還是要回去(監獄)。第一次是別人施加給他的冤案,第二次是自己的選擇。”④保潤與柳生因為仙女而拉近了關系,因為仙女而命運逆轉,最后還是因為仙女保潤刺死了柳生。仙女作為兩個人命運的交界線與聯結點,她的故事在小說中有著重要的銜接作用。
柳生與仙女的命運則更讓人唏噓。他們兩人因錢認識,又因錢擺平了兩人看似不可能化解的矛盾,之后她消失了。再次的相逢也是充滿了緣分,柳生為了贖罪,還人情債,擔負起了到醫院照顧保潤祖父的職責。正是在醫院,他遇到作為富商代表的白小姐。這樣的線索安排看起來毫不費力,順理成章,其實卻隱藏了作者精心的構思,使他們的重逢不露聲色。柳生剛開始對白小姐仍是心存幻想的。可當他經發現白小姐生活不堪的一面,發現他“像一只兔子被她的籠子收納了,他鉆進了兔籠,也許已經被她提在手上了”,從此柳生對于白小姐就只有愧疚之情。當對白小姐憐惜不再,只剩下責任,只剩下罪孽感時,柳生真正開始了贖罪之旅。他在白小姐落難時候給她提供了一切保障,讓曾經漂泊的白小姐第一次對這個城市有了歸屬感,讓她黑暗的人生似乎第一次找到了長明的光源。“她犟不過命運,她的命運由繩套控制,那詭異的繩套在一個個男人手上傳遞,最終交到了柳生手上。”她放下自尊,試探地問柳生愿不愿意和他一輩子在一起,可是柳生的回答傷透了她的心,她發誓從此不再見柳生,直到沒過多久柳生在自己結婚的大喜日子被醉酒的保潤刺死,白小姐才發現,他欠她的還清了。他終于被救贖了。
小說不同的敘事視角,讓我們看到命運之手對人物命運的絕對掌控,命運的輪回某種程度上也達到了修飾結構的目的。保潤、柳生和仙女的一生帶有濃厚的宿命色彩,“這么多年過去了,有個魔鬼仍然在他們三人之間牽線搭橋,多么精巧的手藝,多么邪惡的手藝……無法脫身。”他們的命運就好像是在坐旋轉木馬,不停地回到原地,回到最初的地方,比如井亭醫院的“水塔”。這是當年仙女被保潤用鐵鏈綁著,被柳生強奸的地方。這里又是菩薩的香火堂,給人燒香贖罪的地方。當白小姐討債失敗、無家可歸的時候,她回到了這里;當保潤出獄后不想回家面對空落的房子、冷落的人情時,他回到了這里。這里是保潤想要與白小姐跳小拉清債的地方,也是他被救贖的地方。水塔在三個人的命運中不僅代表了他們最想忘卻的記憶,也代表著希望與未來,贖罪與原諒,代表著他們共同擁有的秘密。小說的最后,當仙女產下紅臉嬰兒無處容身時,她再次回到了這里返璞歸真成為原來的那個干凈純潔的她。
小說不同的敘事視角,構成了小說結構的時空錯位,彼此映射,互為鏡像。小說中三個人二十的生活都有一段未知的人生被作者掩藏,而通過另一種方式來告訴讀者。保潤在監獄中的日子是我們所未知的,我們并不明白他在里面經歷了什么,但是我們知道監獄生活改變了他,獨獨留下了那個善良的保潤。而仙女始終生活在這座城市所編織的漁網之中,離開時沒有真正離開,回來時也沒能真正回到這個城市。她與這座城市分別的那些年里的經歷,不可避免地決定了她回來以后的人生軌跡。對柳生來說,我們不了解的是他與仙女和保潤交往之外的人生。其實仙女從來沒有真正踏入過柳生的生命,她只是占據了一小部分,卻以為那一部分就是全部。最終她才明白,除了她之外,柳生的生命中還有其他人,比如他新婚剛懷孕的妻子,此時的仙女看似無法接受柳生結婚的事實,其實是無法接受柳生的生活不是以她為圓心在運轉。
福克納《喧嘩與騷動》的結構一直備受推崇,小說四個部分由不同的敘事者來講述,康普生三兄弟班吉、昆丁與杰生各自講一遍自己的故事,再以黑人女傭迪爾西為主線講剩下的故事,四個部分、四種敘事,互為補充,深刻表現了小說“時間性”的主題,也顯示了福克納對康普生家族以及美國南方社會墮落的哀悼。而《黃雀記》的敘事結構與敘事視角,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通過保潤、柳生和仙女三個人的復合式敘事結構模式,生動傳達了蘇童對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巨變的憂傷與不安。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就在于,都表現了社會巨變之下,個體的欲望與痛苦、希望與絕望。加繆曾經稱贊福克納提供給我們一個古老的但永遠是新鮮的主題:盲人在他的命運與他的責任之間跌跌撞撞地朝前走,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悲劇主題。保潤、柳生和仙女這些鮮活的人物,何嘗不是在命運的驅遣之下跌跌撞撞地前行呢?
三
《黃雀記》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于隱喻的嫻熟使用,通過對意象與隱喻的精心設計和運用,作者有效地處理了個體與社會、傳統與當代、歷史與經驗、寫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使整部小說成為一個充滿隱喻的文本世界。
小說名為《黃雀記》,可是“黃雀”這個意象并沒有在文本中直接出現。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黃雀作為所有幸與不幸背后的陰影,作為小說中隱形的力量,一直在左右著人物的命運與故事的走向。“黃雀”是災難,是恩賜,是命運,它是故事背后的強大推動力。如果保潤沒有和仙女一起去看電影溜旱冰,仙女就不會欠他八十塊錢,保潤也就不會因為討不到債一怒之下把仙女綁起來,直接導致了仙女被強奸。如果不是因為對保潤心生不忍,柳生就不會替他照顧祖父,不會經常出現在井亭醫院,也就不會在院長辦公室重遇白小姐。可是,沒有“如果”,只有“黃雀”的盡情操控。他們三人的生活陷入了命運的怪圈,不同的人生在“黃雀”的左右下相互交織,難舍難分。“黃雀”隱喻著對于未來的不可知,也許此刻還滿心歡喜走上了正軌,難以料到在下一個路口生活卻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甚至改變一切。“黃雀”成為文本中似有若無、又無處不在的迷魅般的存在。
小說中另一個重要的意象是失魂。小說中祖父、柳生、白小姐都經歷了失魂,失魂對于不同的人隱喻又各不相同。作為小說中的“幽靈”,祖父“是一棵瘋癲的不老松,以家族的名義幸存于世”。作為家族中唯一常在的人,他失了魂卻找到了自己。他失掉的與其說是與這個時代不相合的東西,不如說是失去了這個時代讓人迷失的東西,他反而可以游離在家族與社會的悲劇之外,在井亭醫院這個屬于他的樂土上自在地生活,像一個幽靈一樣,某種意義上,他自己已成為這個社會的魂。
柳生的失魂其實是贖罪。柳生說,“你不在,我的魂就在,你回來了,我的魂就丟了”。仙女的出現不斷地提醒自己曾經的道德的負罪。正是因為心存對仙女的虧欠之情,所以柳生一直試圖贖罪,彌補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他為仙女做的一切其實都是在自我救贖,想要擺脫自己的愧疚之情。小說的最后,仙女說永遠不想再見他,柳生反而頓感輕松,似乎完成了贖罪,終于可以過不受良心譴責的日子了。仙女的失魂是在社會的熏陶下變成了出賣肉體的白小姐。十年之后她再次出現時說,“世界上沒有仙女了,名叫仙女的少女一去不復返了”。柳生死后她聽到了鬼魂的聲音,覺得他們在“向她發出熟悉的吶喊”。于是,“她看見了自己絳紫色的魂,……他們緩緩上升,與天上的白云融合在一起。……跟著她,上橋,下橋。”“她接受河水的訓誡,洗一洗”,河水在這里代表了潔凈與脫俗。她想要還給自己和世界一個本真的自我,最終她又找回了自己的魂,于是曾經消失的仙女真正回到了這座城市。
如果說“失魂”是每個人的體驗,那么“打結”的隱喻則是保潤更具個性化的經驗。打結是保潤的拿手好戲,綠色的尼龍繩甚至成了他的標志。打結在小說中隱含了束縛與捆綁的意思,結的名字再好聽,也是為了限制被綁人的行動自由,所以不管舒服與否,對于當事人都是一種限制。這種束縛與捆綁,直指小說主人公所成長的社會氛圍。小說中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隱喻外,還有一些意象也帶有鮮明的寄寓色彩,比如仙女曾經飼養的兩只兔子其實就是她和柳生,它們“睡在保潤的籠子里”,在命運不斷的交錯中前進,相依相偎。水塔上的兩只烏鴉似乎代表了柳生內心中市儈與黑暗的一面,它們是柳生強奸罪的唯一目擊證人,以至于柳生后來連聽見它們的叫聲都會心虛,仿佛是不斷提醒他要贖罪來求得內心的安定。
《黃雀記》鮮明的人物形象、巧妙的敘事結構和豐富的意象隱喻,使得這部作品成為一部極為精致圓潤的長篇之作。“香椿樹街”,既喚醒了我們對蘇童風格的記憶,又激活了蘇童無限的寫作潛能。我們閱讀虛構、閱讀歷史、閱讀隱喻,充分體會到了作者操控長篇的敘事能力,以及小說之于現實的敘事力量,讓我們在現實與虛構的辯證往復中重新體驗到了閱讀的快感。
【注釋】
①③④《新長篇〈黃雀記〉出版,蘇童五十天命重歸“香椿樹街”》,載《時代周報》2013年6月6日。
②引文均見蘇童《黃雀記》,載《收獲》2013年第3期。不另注。
(陳逢玥,蘇州大學文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