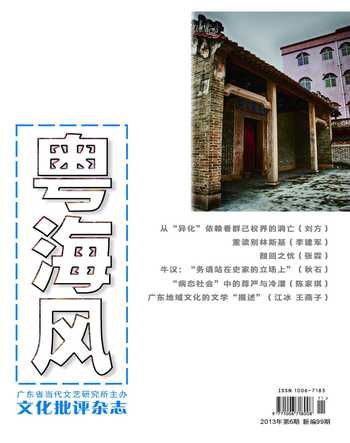重讀別林斯基
李建軍
1
5月26日,是別林斯基辭世的日子,而2013年,則是他逝世的第165個(gè)年頭。在這個(gè)文學(xué)風(fēng)尚不斷變換的時(shí)代,別林斯基已然是一個(gè)黯淡的名字;在那些趨新求異者的眼里,他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也早就過(guò)期失效了。但是,在我看來(lái),別林斯基是自己時(shí)代文學(xué)的引路人,是普希金等大師的知音,是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偉大作品的助產(chǎn)士。他的堪稱(chēng)經(jīng)典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不僅極大地提高了俄羅斯民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水準(zhǔn)和文學(xué)鑒賞力,而且,還對(duì)世界文學(xué),尤其是中國(guó)的發(fā)軔期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
順著活躍于19世紀(jì)三四十年代的幾乎隨便哪一位俄羅斯大師的路徑,可以走近別林斯基的世界,就會(huì)在俄羅斯文學(xué)的遼闊原野上與他邂逅。記得剛上大學(xué)的時(shí)候,我喜歡上了那些讓人開(kāi)心和發(fā)笑的作品,喜歡上了喜劇文學(xué)和諷刺小說(shuō)。果戈里的小說(shuō)和喜劇,更是讓我喜歡到了入迷的程度。果戈里的絕妙的諷刺,總是叫人忍俊不禁,甚至常常使人笑出聲來(lái)。
后來(lái),我便很留意關(guān)于果戈里的評(píng)論和研究。我注意到,幾乎所有談到果戈里的文章,都會(huì)提到別林斯基的名字。于是,因?yàn)楣昀铮议_(kāi)始讀別林斯基的評(píng)論。他對(duì)果戈里的分析和評(píng)價(jià),幾乎全都是我“意中所有”。別林斯基的充滿熱情、詩(shī)意和洞見(jiàn)的評(píng)論,簡(jiǎn)直令我五體投地。
讀其書(shū)不知其人可乎? 那么,別林斯基到底是一個(gè)什么樣的批評(píng)家呢?通過(guò)閱讀波利亞科夫的《別林斯基傳》、屠格涅夫《回憶錄》中的《回憶別林斯基》、巴納耶夫的《群星燦爛的年代》及《巴納耶娃回憶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和米爾斯基的《俄羅斯文學(xué)史》等著作,我對(duì)別林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認(rèn)識(shí)。
在納博科夫被評(píng)價(jià)為“用包括俄語(yǔ)在內(nèi)的所有語(yǔ)言寫(xiě)就的最好的一部《俄國(guó)文學(xué)史》”中,著名的文學(xué)史家米爾斯基這樣評(píng)價(jià)別林斯基:“他是知識(shí)分子的真正父親,體現(xiàn)著兩代以上俄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一貫精神,即社會(huì)理想主義、改造世界的激情、對(duì)于一切傳統(tǒng)的輕蔑,以及高昂無(wú)私的熱忱。他似乎成了俄國(guó)激進(jìn)派的守護(hù)神,直到如今,他的名字幾乎仍是唯一不受批評(píng)的姓氏。……他對(duì)于那些于1830—1848年間步入文學(xué)的作家所做評(píng)判,幾乎總被無(wú)條件接受。這是對(duì)一位批評(píng)家的崇高贊頌,很少有人獲此殊榮。”[1]這樣的評(píng)價(jià)是很高的,也是很恰當(dāng)?shù)摹?/p>
在別林斯基成熟期的文學(xué)觀念里,文學(xué)不是一種屬于個(gè)人的孤立的偶然現(xiàn)象,而是與一個(gè)民族和全人類(lèi)的整體的精神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偉大的文化現(xiàn)象。由于將“共同性、相互聯(lián)系、依賴(lài)性和連鎖性” 當(dāng)作“文學(xué)的特點(diǎn)”,別林斯基便特別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生活和文學(xué)的“普遍性”:“誰(shuí)具有更多的普遍性,誰(shuí)就更富有生命;沒(méi)有普遍事物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雖生猶死。一個(gè)人具有普遍性,這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表現(xiàn)在下面一點(diǎn)上:他理解一切合乎人的天性的東西,一切構(gòu)成天性的本質(zhì)和特點(diǎn)的東西,他有權(quán)利對(duì)自己說(shuō):‘我是一個(gè)人,沒(méi)有任何人性的東西和我是格格不入的。對(duì)一個(gè)具有普遍性的人來(lái)說(shuō),個(gè)人的利益和世俗的需要是次要的東西,天性和人性才是主要的東西。”[2]別林斯基所說(shuō)的“普遍性”,就是一種高尚的、有教養(yǎng)的生活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是開(kāi)放的、包容的、利他主義的,而不是封閉的、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對(duì)別林斯基來(lái)講,文學(xué)即生活,談?wù)撐膶W(xué)就是談?wù)撋畋旧恚務(wù)撊绾螌?xiě)作就意味著談?wù)撊绾紊睢K裕粋€(gè)優(yōu)秀的作家,就是一個(gè)擺脫了低級(jí)的生活形態(tài)的人,就是一個(gè)鼓舞并引導(dǎo)人們高尚地生活的人:“是的,生活并不等于是有這么許多年吃吃喝喝,為官銜和金錢(qián)奔波勞碌,空閑下來(lái)時(shí),打呵欠,玩紙牌:這種生活比死還糟,這種人比禽獸還不如,因?yàn)閯?dòng)物雖然屈服于自己的本能,卻還要充分利用它天生可以用來(lái)生活的一切手段,勇往直前地完成它的使命。生活就意味著:感覺(jué)和思索,飽受苦難和享受快樂(lè);其余的一切都是死亡。我們的感覺(jué)和思想所包含的內(nèi)容越是豐富,我們飽受苦難和享受快樂(lè)的能力越是強(qiáng)大和深刻,我們就生活得越多:一瞬間這樣的生活,比麻木昏睡、渾渾噩噩、庸俗無(wú)聊地活上一百年,還要有意義得多。”[3]別林斯基試圖幫助自己時(shí)代的人們理解個(gè)人與祖國(guó)的關(guān)系、愛(ài)祖國(guó)與愛(ài)人類(lèi)的關(guān)系:“對(duì)于一個(gè)完備而健康的人來(lái)說(shuō),祖國(guó)的命運(yùn)總是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一切高貴的人,總是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他和祖國(guó)的親密關(guān)系、血肉聯(lián)系。……在他的靈魂里,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血液里,負(fù)載著社會(huì)的生活:他為社會(huì)的疾病而疼痛,為社會(huì)的苦難而痛苦,隨著社會(huì)的健康而蓬勃發(fā)展,為社會(huì)的幸福而感到快樂(lè)。……對(duì)祖國(guó)的愛(ài)應(yīng)該從對(duì)人類(lèi)的愛(ài)出發(fā),正像局部從普遍出發(fā)一樣。熱愛(ài)自己的祖國(guó),這就是意味著:熱誠(chéng)希望祖國(guó)實(shí)現(xiàn)人類(lèi)的理想,并且盡力促其實(shí)現(xiàn)。否則,愛(ài)國(guó)主義就將變成中國(guó)人氣質(zhì),愛(ài)本國(guó)的東西,僅僅因?yàn)樗潜緡?guó)的,憎惡外來(lái)的東西,僅僅因?yàn)樗峭鈦?lái)的,甚至于對(duì)于自己的丑陋和畸形也是顧影猶憐,賞玩不盡。”[4]別林斯基的這些觀念,完全是一種嶄新的新人文主義思想。優(yōu)秀的俄羅斯作家之所以?xún)?yōu)秀,偉大的俄羅斯文學(xué)之所以偉大,就是因?yàn)椤吧鐣?huì)性”和“人類(lèi)性”被當(dāng)作靈魂性和基礎(chǔ)性的東西,而這“靈魂”和“基礎(chǔ)”的形成,是與別林斯基的啟蒙主義引導(dǎo)分不開(kāi)的。
對(duì)生活的“社會(huì)性”和“人類(lèi)性”的自覺(jué)意識(shí),必然合邏輯地指向這樣一點(diǎn),那就是,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責(zé)任感和自覺(jué)性:“文學(xué)是民族的自覺(jué):文學(xué)像一面鏡子,反映著民族的精神和生活;文學(xué)是一種事實(shí),從這里面可以看出一個(gè)民族所負(fù)的使命,它在人類(lèi)大家庭中所占的位置,它通過(guò)它的存在所表現(xiàn)的人類(lèi)精神的全世界性歷史發(fā)展的階段。一個(gè)民族的文學(xué)的源泉,可能不是某種外在的動(dòng)機(jī),或某種外部的推力,而僅僅是一個(gè)民族的世界觀。……世界觀是文學(xué)的根源和基礎(chǔ)。”[5]正因?yàn)檫@樣,所以別林斯基對(duì)俄國(guó)文學(xué)的要求就特別嚴(yán)格,批評(píng)也特別嚴(yán)厲。他很少夸夸其談地贊美俄國(guó)文學(xué),也很少用“創(chuàng)造了輝煌”、“達(dá)到了高峰”、“寫(xiě)出了極品”、“制造了地震”等廉價(jià)的語(yǔ)言來(lái)吹捧俄國(guó)作家。他總是以更高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要求俄國(guó)文學(xué),總是以尖銳的語(yǔ)氣表達(dá)自己對(duì)俄國(guó)文學(xué)的不滿和希望。他說(shuō):“我們的文學(xué)過(guò)去并不輝煌,目前也很灰暗,可是我們絲毫也不應(yīng)該對(duì)未來(lái)絕望。……當(dāng)我們攻擊我們的文學(xué)的時(shí)候,我們只是想駁斥那種具有可笑的自我陶醉的看法的人,他們把少人看作無(wú)窮盡的多數(shù)人,真誠(chéng)地相信俄國(guó)文學(xué)凌駕于英國(guó)文學(xué)、德國(guó)文學(xué)、法國(guó)文學(xué)之上”[6]。俄國(guó)文學(xué)的健全發(fā)展和輝煌成就,與別林斯基的永不自滿的尖銳批評(píng),有著深刻的因果關(guān)系。正是通過(guò)這種尖銳而正確的批評(píng),別林斯基培養(yǎng)了俄羅斯作家的“世界觀”,培養(yǎng)了他們高貴的文學(xué)氣質(zhì),培養(yǎng)了他們對(duì)文學(xué)的莊嚴(yán)而樸實(shí)的態(tài)度。
當(dāng)然,就學(xué)術(shù)水平來(lái)看,別林斯基并非第一流的學(xué)者,就認(rèn)知能力來(lái)看,他也并不總是正確的。在政治上,他曾經(jīng)贊美過(guò)沙皇發(fā)動(dòng)的波羅金諾戰(zhàn)爭(zhēng);在美學(xué)理念上,他曾經(jīng)宣揚(yáng)過(guò)“純藝術(shù)”論;在文學(xué)上,曾經(jīng)貶低甚至否定過(guò)喬治·桑和席勒,對(duì)圣博甫的“歷史批評(píng)”,也曾做過(guò)不正確的評(píng)價(jià);從認(rèn)知方式來(lái)看,正像普列漢諾夫所批評(píng)的那樣,“一般來(lái)講,別林斯基在抱有妥協(xié)情緒的時(shí)期,往往濫用先驗(yàn)論的邏輯體系,并且輕視事實(shí)。”[7]然而,“他痛心而憤恨地回憶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誤,并運(yùn)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來(lái)補(bǔ)償這些過(guò)失。”[8]所以,在這樣的錯(cuò)誤和轉(zhuǎn)變里,人們所看到的,不是見(jiàn)風(fēng)使舵的搖擺,而是一以貫之的真誠(chéng)態(tài)度與自我糾正的勇氣,正像以賽亞·伯林所指出的那樣:“他的一貫,是道德上的一貫,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貫。”[9]
2
作為批評(píng)家,別林斯基遠(yuǎn)不是一個(gè)人人都喜歡的人,而是一個(gè)招怨樹(shù)敵甚多的人。他是專(zhuān)制政府和斯拉夫主義者的眼中釘,也是文學(xué)界許多人的肉中刺。他之所以成為不少人集矢的怨府,很大程度上,是因?yàn)樗臉O為罕見(jiàn)的坦率和正直,按照伯林的形象而夸張的描述:“他常像一只肉食鳥(niǎo),撲擊一位作家,酣暢盡言,將其人片片撕碎。”[10]不錯(cuò),敢于表達(dá)自己態(tài)度和主張的坦率性,敢于反駁對(duì)方觀點(diǎn)的論戰(zhàn)性,這就是一個(gè)優(yōu)秀批評(píng)家最重要的精神特點(diǎn)。上世紀(jì)中葉,德國(guó)學(xué)者馬克斯·本塞曾經(jīng)寫(xiě)過(guò)一篇題為《批評(píng)與論戰(zhàn)》的短文,馮至先生將它譯了過(guò)來(lái),發(fā)表在1944年昆明出版的《自由論壇》上。這篇文章的作者認(rèn)為,應(yīng)該將“批評(píng)”與“論戰(zhàn)”區(qū)分開(kāi)來(lái),因?yàn)榕u(píng)家區(qū)分作品的真?zhèn)危u(píng)定它的價(jià)值,而論戰(zhàn)家則以宣示和捍衛(wèi)真理為己任,“熱情飽滿,思想充沛,同時(shí)對(duì)人類(lèi)有強(qiáng)烈的愛(ài),他的生存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一個(gè)論戰(zhàn)家的態(tài)度必須是道德的”[11]。
這樣的區(qū)分,其實(shí)并不很科學(xué)。因?yàn)椋谂u(píng)家與論戰(zhàn)家之間,并沒(méi)有涇渭分明的界線。第一流的批評(píng)家,如別林斯基、勃蘭兌斯、魯迅、喬治·奧威爾,往往都具有論戰(zhàn)家的道德姿態(tài)和精神氣質(zhì)。克爾凱郭爾說(shuō):“生產(chǎn)者、新的創(chuàng)造者,永遠(yuǎn)需要場(chǎng)所,所以他是戰(zhàn)斗者。”事實(shí)上,批評(píng)家也需要有“戰(zhàn)斗者”的精神,因?yàn)椋挥芯邆淞诉@種精神,他才敢于坦率而尖銳地表達(dá)自己的意見(jiàn),才敢于顛覆固有的文學(xué)秩序,才敢于向文學(xué)界的權(quán)威們發(fā)出尖銳的質(zhì)疑。
作為一個(gè)新型的知識(shí)分子,別林斯基的從不為了“論戰(zhàn)”而論戰(zhàn)。他的“論戰(zhàn)”有著利他主義的積極的性質(zhì),有著穩(wěn)定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與明確的精神指向——為了實(shí)現(xiàn)人的解放與自由,為了捍衛(wèi)人的價(jià)值與尊嚴(yán)。別林斯基熱愛(ài)真理和自由,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是一個(gè)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和高尚的利他主義者。他反抗權(quán)貴階級(jí)和社會(huì)不公,同情那些受奴役與受損害的底層人。對(duì)他來(lái)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隨波逐流,或者,因?yàn)榭謶侄聊蛉鲋e,簡(jiǎn)直就是可恥的墮落。他將文學(xué)批評(píng)當(dāng)作追求真理和正義的事業(yè)。別爾嘉耶夫說(shuō):“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文學(xué)批評(píng)只是體現(xiàn)完整世界觀的手段,只是為真理而斗爭(zhēng)的手段。”[12]正因?yàn)檫@樣,在表達(dá)意見(jiàn)的時(shí)候,他的態(tài)度就特別坦率和勇敢,沒(méi)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和畏懼,總是表現(xiàn)出“角斗士”般的激情。
在一些人的錯(cuò)誤的觀念里,文學(xué)批評(píng)是一種低級(jí)的依附性的精神現(xiàn)象,是任何一個(gè)略有表達(dá)力的人都可以搞的事情。然而,在別林斯基看來(lái),文學(xué)批評(píng)卻是一種極有難度、極為復(fù)雜的工作,需要具備多方面的能力和修養(yǎng)才行。他在《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批評(píng)及其文學(xué)意見(jiàn)》中說(shuō):“批評(píng)才能是一種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評(píng)價(jià)的才能……有人認(rèn)為批評(píng)這一門(mén)行業(yè)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錯(cuò)特錯(cuò):深刻的感覺(jué),對(duì)藝術(shù)的熱烈的愛(ài),嚴(yán)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觀性——這是公正無(wú)私的態(tài)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誘引的本領(lǐng);從另一方面來(lái)說(shuō),他擔(dān)當(dāng)?shù)呢?zé)任又是多么崇高!人們對(duì)被告的錯(cuò)誤習(xí)見(jiàn)不以為怪;法官的錯(cuò)誤卻要受到雙重嘲笑的責(zé)罰。”[13]別林斯基無(wú)疑就是這樣一個(gè)具有這種“稀有”才能和“公正無(wú)私”態(tài)度的人,而他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則因此有了近乎完美的典范意義。
3
如果說(shuō),教育人是文學(xué)的固有功能,那么,文學(xué)批評(píng)則是強(qiáng)化文學(xué)的教育作用的重要手段。別林斯基明白這一點(diǎn),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批評(píng),改變?nèi)藗兊囊庾R(shí)結(jié)構(gòu),提高人們的鑒賞力,指導(dǎo)人們對(duì)藝術(shù)和文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他說(shuō):“我們的批評(píng)應(yīng)該對(duì)于社會(huì)起家庭教師的作用,用簡(jiǎn)單的語(yǔ)言講述高深的道理。它在原理方面應(yīng)該是德國(guó)式的,在敘述方式方面應(yīng)該是法國(guó)式的。”[14]所以,他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是深刻的,也是活潑的,沒(méi)有一點(diǎn)兒迂腐沉悶的學(xué)究氣。他在《論巴拉廷斯基的詩(shī)》中說(shuō):“我們必須指導(dǎo)人們的審美口味和關(guān)于典雅事物的理解,拓展人們對(duì)典雅事物的愛(ài)好。”[15]為了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他在幫助讀者理解和欣賞第一流的杰作的同時(shí),毫不寬假地批評(píng)了那些有問(wèn)題的劣作。他認(rèn)為,雜志應(yīng)該為讀者提供“批評(píng)”:“批評(píng)應(yīng)該是雜志的靈魂、生命,應(yīng)該是它的一個(gè)經(jīng)常持久的專(zhuān)欄,是一篇綿長(zhǎng)的、不中斷和不結(jié)束的論文。”[16]在為《望遠(yuǎn)鏡》、《祖國(guó)紀(jì)事》、《現(xiàn)代人》等雜志所寫(xiě)的大量的批評(píng)文章里,別林斯基深刻地分析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柯?tīng)栕糠颉⒖死茁宸颉⒉蟹赖热说奈膶W(xué)成就和局限,描述了俄羅斯文學(xué)的流變軌跡,指示出俄國(guó)文學(xué)應(yīng)該前行的方向——伯林高度評(píng)價(jià)他在這一方面的偉大成就:“他傳給別人一種真理神圣之感,從而改變了俄國(guó)人的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他改變了眾多俄國(guó)人思想與感覺(jué)、經(jīng)驗(yàn)與表達(dá)的品質(zhì)與格調(diào)。”[17]
在人們的印象中,別林斯基像契訶夫一樣,是一個(gè)沒(méi)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因?yàn)椤皹O其粗野地謾罵基督”,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銳批評(píng)和猛烈攻訐:“他在罵基督的時(shí)候從來(lái)不對(duì)自己說(shuō):我又能以什么來(lái)代替基督呢?……他極端地自滿,這已經(jīng)是他本人的討厭并可恥的麻木了。”[18]事實(shí)上,別林斯基有自己的“上帝”;他的上帝是這樣一個(gè)“理念”——“它不僅是智慧的,并且還是有愛(ài)心的!人啊,為你崇高的使命驕傲吧,驕傲吧”;在這偉大的“理念”里,正確的道路只有一個(gè),那就是“摒棄利己主義,把自私的我踩在腳下,為別人幸福而生存,為同胞、祖國(guó)的利益,為人類(lèi)的利益犧牲一切,愛(ài)真理和善良,不是為了求得報(bào)酬,而是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盡苦難,然后重見(jiàn)上帝獲得永生……”[19]他將這稱(chēng)作“永恒理念的道德生活”。由此看來(lái),陀思妥耶夫斯基對(duì)別林斯基的批評(píng),是很不準(zhǔn)確、很不公平的。
是的,別林斯基全部的文學(xué)批評(píng),都植根于這個(gè)偉大的“理念”之中;他的批評(píng)不僅是一種求真的認(rèn)知行為,而且是一種求善的倫理行為。他的文學(xué)在表達(dá)愛(ài)意和善念方面所達(dá)到的高度,一點(diǎn)也不比那些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低。他懷疑并排斥“基督”,但他用自己的“理念”和方式來(lái)行善。他特別關(guān)注政治和社會(huì)問(wèn)題,關(guān)心人類(lèi)的處境與幸福。所以,雖然別林斯基一度曾經(jīng)宣揚(yáng)過(guò)“純藝術(shù)”的主張,但是,進(jìn)入文學(xué)上的成熟時(shí)期,他便將自己的文學(xué)觀念放置在道德和倫理的基礎(chǔ)之上,將“善”置于“美”和“真”之上。在關(guān)于德羅慈陀夫的《道德哲學(xué)體系試論》的書(shū)評(píng)文章里,別林斯基用充滿激情和詩(shī)意的語(yǔ)言,體系性地表達(dá)了自己的文學(xué)倫理思想,闡釋了“道德法則”和“對(duì)人類(lèi)的愛(ài)”,甚至談及“靈魂”的“永恒的秘密”等倫理學(xué)范疇的問(wèn)題:“文學(xué)和藝術(shù)也是為最高的善服務(wù)的,而這最高的善同時(shí)也就是最高的真和美。”[20]根據(jù)這樣的文學(xué)理念,別林斯基所理解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就不再是一種狹隘的專(zhuān)業(yè)行為,而是近乎宗教信仰一樣莊嚴(yán)的偉大事業(yè)。
4
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直接客體對(duì)象是作品,直接主體對(duì)象則是作家。文學(xué)交流本質(zhì)上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學(xué)批評(píng)則是主體之間經(jīng)由作品展開(kāi)的對(duì)話和對(duì)抗。以開(kāi)放的態(tài)度承受他者的批評(píng),以對(duì)話的姿態(tài)回應(yīng)別人的質(zhì)疑,是每一個(gè)參與公共生活的現(xiàn)代公民的社會(huì)義務(wù)。
在作家面前,批評(píng)家必須保持不卑不亢的對(duì)話姿態(tài),要把作家當(dāng)作一個(gè)可以質(zhì)疑的對(duì)話者,必須向他發(fā)問(wèn)并陳述自己的真實(shí)判斷。與作家之間產(chǎn)生矛盾和沖突,難免會(huì)因此受到誤解甚至傷害,對(duì)此,批評(píng)家無(wú)須覺(jué)得委屈和不平,而應(yīng)該將它看做自己必須承擔(dān)的壓力和考驗(yàn)。
1834年,二十三歲的別林斯基寫(xiě)出了天才的評(píng)論文章《文學(xué)的幻想》。在這篇文章中,他表達(dá)了對(duì)依然處于幼稚階段的俄國(guó)文學(xué)的不滿,甚至認(rèn)為俄國(guó)“沒(méi)有文學(xué)”。他說(shuō):“文學(xué)是民族的自覺(jué),凡是沒(méi)有這自覺(jué)的地方,文學(xué)如果不是早熟的果實(shí),就是博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某一階層的人的手藝。”[21]為了幫助自己時(shí)代的文學(xué)擺脫對(duì)歐洲人的“模仿者”角色,他試圖改變批評(píng)界的那種溜須拍馬、只說(shuō)好話的風(fēng)氣。別林斯基對(duì)那種低三下四地討好作家的勢(shì)利的批評(píng)家深?lèi)和唇^:“到現(xiàn)在為止,我們的文學(xué)界仍舊流行著一種可憐的、幼稚的對(duì)作家的崇拜,在文學(xué)方面,我們也非常重視爵位表,不敢對(duì)地位高的人說(shuō)真話。碰到一位名作家,我們總是只限于說(shuō)些空話和溢美之辭;不顧情面地說(shuō)真話,我們就認(rèn)為是褻瀆神圣。”[22]他反對(duì)“文學(xué)中的偶像崇拜”:“什么東西曾是、現(xiàn)在是,我認(rèn)為將來(lái)還有很久一段時(shí)間將是極度妨礙在俄羅斯傳布文學(xué)的基本概念以及培養(yǎng)口味的主因?那便是文學(xué)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狂信常常總是社會(huì)幼稚的命運(yùn)。……要冒犯幾個(gè)芝麻大的小權(quán)威,我們還得擁有對(duì)真理的公正無(wú)私的愛(ài)以及性格的力量才行呢,大些的權(quán)威就更不用說(shuō)……”[23]別林斯基知道冒犯這些“偶像”,會(huì)有什么樣的后果,但是他無(wú)所畏懼:“跟社會(huì)輿論進(jìn)行戰(zhàn)斗,明目張膽地反對(duì)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我膽敢這樣做,與其說(shuō)是因?yàn)橛杏職猓銓幷f(shuō)是為了對(duì)真理的無(wú)私的愛(ài)。”[24]別林斯基受到了猛烈的攻擊。他被稱(chēng)為“冷評(píng)家”和“酷評(píng)家”。有人則編造謠言侮辱他的人格,試圖從道德上擊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
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態(tài)向作家說(shuō)真話,一針見(jiàn)血而又有理有據(jù)地指出問(wèn)題,是別林斯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基本原則。在別林斯基心目中,沒(méi)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評(píng)的,也沒(méi)有什么問(wèn)題是不可以談?wù)摰摹K^不討好任何作家,無(wú)論他社會(huì)地位有多高,無(wú)論他曾經(jīng)享有多高的文學(xué)威望。他批評(píng)以“俄國(guó)的伏爾泰自居”的蘇瑪羅科夫:“他的全部藝術(shù)活動(dòng),不過(guò)是可憐亦復(fù)可笑的裝腔作勢(shì)而已。……然而,這個(gè)可憐的劣等文士卻坐享了怎樣的盛名啊!”[25]他批評(píng)卡拉姆辛,認(rèn)為他的作品的主要缺點(diǎn),“在于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遠(yuǎn)沒(méi)有丈夫氣概的對(duì)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辯家的夸夸其談”[26]。他批評(píng)歐仁蘇的“聲名遠(yuǎn)揚(yáng)”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憐最平庸的作品”[27]。他毫不客氣地否定杰爾查文的全部文學(xué)成就:“杰爾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僅僅在細(xì)節(jié)部分鑲嵌著珍貴發(fā)亮寶石的不成樣子的粗笨玩意兒。”[28]他批評(píng)瑪爾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沒(méi)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學(xué),任何戲劇性;結(jié)果,小說(shuō)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們都從一個(gè)模子里刻出來(lái),差別僅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里都重復(fù)著自己”[29]。盡管時(shí)間已經(jīng)過(guò)去了一個(gè)半世紀(jì),但是,別林斯基的這些判斷和評(píng)價(jià),至今仍然被認(rèn)為是正確而可靠的。
5
別林斯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典范性,他對(duì)文學(xué)真理的無(wú)條件的熱愛(ài)與忠誠(chéng),近乎完美地體現(xiàn)于他對(duì)果戈里的肯定與否定兼而有之的批評(píng)上。在世界文學(xué)史上,像果戈里與別林斯基這樣的相得益彰的創(chuàng)作—評(píng)論共生現(xiàn)象,極為罕見(jiàn)。閱讀果戈里的作品,而不讀別林斯基的評(píng)論,就好比游覽巴黎而漏掉了盧浮宮。
果戈里的幽默和諷刺,不同于拉伯雷和莫里哀,也不同于薩克雷和菲爾丁,——他對(duì)自己筆下的人物充滿溫柔的憐憫,甚至深深地愛(ài)著他們,所以,他的諷刺就謔而不虐,有一種含著同情的詩(shī)意性的感傷,讓人在捧腹大笑之后,頓覺(jué)悲從中來(lái),心里別有一種酸楚而悵惘的感覺(jué)。對(duì)果戈里作品的這一特點(diǎn),別林斯基的闡釋?zhuān)瑴?zhǔn)確而深刻,令人拍案叫絕。尤其是1835年發(fā)表于《望遠(yuǎn)鏡》的《論俄國(guó)中篇小說(shuō)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說(shuō)》,激情飽滿,酣暢淋漓,不僅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含淚的喜劇”等經(jīng)典性的概念,而且還在開(kāi)闊的比較視野中,揭示了果戈里作品的“顯著特征”:“構(gòu)思的樸素、十足的生活真實(shí)、民族性、獨(dú)創(chuàng)性”,以及“那總是被悲哀和憂郁所壓倒的戲劇性的興奮”[30]揭示了果戈里“純粹俄國(guó)的幽默”的特點(diǎn):“平靜的、淳樸的幽默,作者在這里裝扮成傻子的模樣”,以及“詩(shī)歌的秘密”:“當(dāng)你一直讀到那悲喜劇的結(jié)局的時(shí)候,為什么會(huì)那么悲痛地微笑,那么憂郁地嘆息呢?這便是詩(shī)歌的秘密!這便是藝術(shù)的魔力!你看見(jiàn)的是生活,看見(jiàn)了生活,就不得不嘆息!……”[31];他認(rèn)為果戈里的中篇小說(shuō)的“純潔的道德性”,將“對(duì)世道人心發(fā)生強(qiáng)烈而有益的影響”,——“啊!在這樣的道德性面前,我是隨時(shí)準(zhǔn)備屈膝下跪的!”別林斯基的這篇評(píng)論文章,凡認(rèn)真讀過(guò)的人,莫不擊節(jié)稱(chēng)賞。正是通過(guò)別林斯基的引導(dǎo),讀者才更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了果戈里的價(jià)值,才理解了他的喜劇性作品的意義。
然而,后來(lái),果戈里卻出版了他的《與友人書(shū)簡(jiǎn)選粹》。在這本新作里,他自我作踐,貶低自己的創(chuàng)作成就,否定自己昔日的文學(xué)精神,并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獲得沙皇滿意的時(shí)候,您才會(huì)對(duì)這些作品感到滿意”[32];還贊美俄羅斯的官方宗教,贊美落后的沙皇制度和宗法制度。果戈里的這本“極為有害的書(shū)”,“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別林斯基。在他看來(lái),果戈里誤解了俄羅斯民族的“天性”,因?yàn)椤吧衩氐目駸岵皇撬麄兊奶煨浴盵33]這本書(shū)不僅降低了果戈里作為作家的身價(jià),特別是降低了他作為人的身價(jià)。作為一個(gè)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啟蒙主義知識(shí)分子,別林斯基認(rèn)為俄羅斯“最迫切的民族問(wèn)題就是消滅農(nóng)奴制,取消肉刑,盡可能?chē)?yán)格地去實(shí)行至少已經(jīng)有的法律”,然而,果戈里卻教導(dǎo)地主“向農(nóng)民榨取更多的錢(qián)財(cái),教導(dǎo)他們把農(nóng)民罵得更兇”,別林斯基說(shuō):“這難道不應(yīng)該引起我的憤慨嗎?……即使您有意要謀害我的性命,我也不會(huì)比為了這幾行可恥的文字更仇恨您。”[34]在《給果戈里的信》的開(kāi)頭部分,別林斯基說(shuō)過(guò)這樣一段話:“自尊心受到侮辱還可以忍受,只要一切問(wèn)題都局限在這里,我在理智上還是能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沉默不語(yǔ)的,然而到得真理與人的尊嚴(yán)受到侮辱,這卻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護(hù)下和鞭子的防衛(wèi)下把謊言和不道德當(dāng)作真理和美德來(lái)宣傳,這是難以沉默的。”[35]別林斯基就是這樣一個(gè)為真理和正義而戰(zhàn)的“論戰(zhàn)家”,就是這樣一個(gè)高尚而偉大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
6
別林斯基生于1811年5月30日,死于1848年5月26日,死得實(shí)在太早、太可惜了。在1840年3月24日致鮑特金的信中,別林斯基說(shuō)過(guò)這樣的話:“我將死在雜志崗位上,吩咐在棺材里,在頭旁放一本《祖國(guó)紀(jì)事》。我是文學(xué)家,我?guī)е⊥吹摹⑼瑫r(shí)是愉快而驕傲的信念這樣說(shuō)。俄國(guó)文學(xué)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36]為了俄國(guó)文學(xué),他不知疲倦地閱讀和寫(xiě)作,實(shí)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雖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別林斯基卻完成了許多人活到老年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他卻留下十三卷俄文本《別林斯基全集》,而由滿濤和辛未艾先生翻譯的中文版《別林斯基選集》,也有煌煌六卷,總計(jì)290多萬(wàn)字。書(shū)籍是作者的人格鏡像,是通向真理的林中小路。別林斯基的著作,就是他偉大人格的“客觀對(duì)應(yīng)物”,就是他不朽的紀(jì)念碑。有這樣的著作留存下來(lái),就意味著他的精神將薪火相傳。只要人們?nèi)匀粺釔?ài)文學(xué),仍然熱愛(ài)真理,那么,他就會(huì)作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偉大典范,而常常被人談起,就會(huì)受到人們永遠(yuǎn)的崇敬和懷念。
用別林斯基的尺度來(lái)衡量,無(wú)論是我們時(shí)代的文學(xué)寫(xiě)作,還是我們時(shí)代的文學(xué)批評(píng),都沒(méi)有達(dá)到令人滿意的成熟狀態(tài)。我們?nèi)狈e林斯基那樣的“論戰(zhàn)家”型的批評(píng)家,缺乏像別林斯基那樣把文學(xué)當(dāng)作圣物的純粹態(tài)度。我們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學(xué)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說(shuō)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開(kāi)批評(píng)的時(shí)候,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就像劉知幾在《史通·直書(shū)》中所批評(píng)的那樣:“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
在今天,紀(jì)念別林斯基,固然意味著對(duì)一個(gè)偉大批評(píng)家的追懷和致敬,也意味著對(duì)文學(xué)批評(píng)前行路向的重新確認(rèn)。別林斯基的批評(píng)文本里,有著引導(dǎo)我們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線”。要想改變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現(xiàn)狀,要想遏止寫(xiě)作上肆無(wú)忌憚地粗制濫造的風(fēng)氣,就需要具備像別林斯基那樣的“論戰(zhàn)家”的性格,就需要在我們的意識(shí)里注入敢于質(zhì)疑的勇氣,就需要在我們內(nèi)心培養(yǎng)善于“論戰(zhàn)”的能力。假如我們的批評(píng)家面對(duì)文學(xué),都能像別林斯基那樣執(zhí)著和熱誠(chéng),那樣嚴(yán)格和認(rèn)真,那么,我們時(shí)代的文學(xué)風(fēng)氣一定會(huì)更好。
(作者單位: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
[1]德·斯·米爾斯基:《俄國(guó)文學(xué)史》上卷,劉文飛譯,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228—229頁(yè)。
[2][3][4][5][6][36]《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滿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7月,第451、452—453、454—455、396、438—439、422頁(yè)。
[7]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美學(xué)論文集》(Ⅰ),曹葆華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206頁(yè)。
[8]巴納耶夫:《群星燦爛的年代》,劉敦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7月,第281頁(yè)。
[9][10][17]以賽亞·伯林:《俄羅斯思想家》,彭淮棟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96、195、222頁(yè)。
[11]馮至:《馮至學(xué)術(shù)論著自選集》,北京師范學(xué)院出版社,1992年6月,第211頁(yè)。
[12]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譯,三聯(lián)書(shū)店,1995年8月,第57頁(yè)。
[13][14][15][16][19][20][21][22][23][24][25][26][29][30][31]《別林斯基選集》,第一卷,滿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5月,第324、326、224、319、19—20、428、322、36、55、95、40、62、96、183、194頁(yè)。
[18]陳燊主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第842—843頁(yè)。
[27][28]《別林斯基選集》,第五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12月,第442、39頁(yè)。
[32][33][34][35]《別林斯基選集》,第六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12月,第471、468、466、464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