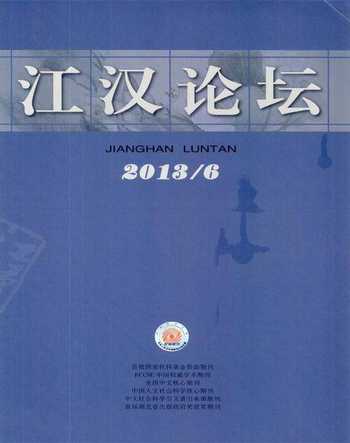明代商人的佛教信仰與義舉的關系
張三夕 張世敏
摘要:明代中期出現的商人碑傳文,是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這些新出現的傳記文學作品中記錄的義舉,通常被認為是諛墓之詞,進而導致它們的真實性受到懷疑。從商人的佛教信仰這個角度,對商人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進行探討,可以得知,傳主信奉佛教的碑傳文中,都記錄有佛教式的義舉;傳主不信奉佛教的碑傳文,幾乎都沒有記錄佛教式的義舉。這種對應關系說明在商人碑傳文記錄的義舉中,至少佛教式的義舉并非諛墓之詞。
關鍵詞:商人碑傳文;佛教;義舉;諛墓
中圖分類號:120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3)06-0118-04
通過對明代商人碑傳文進行深入探索,從商人為什么要施行義舉這個角度進行思考,我們幾乎可以為商人碑傳文中所記錄的所有義舉都找到動因。諸如政治權力的引導與強制,讓商人不得不施行義舉;受到中國傳統“市義”思想的影響,義舉成了商人換取其他資本的途徑。除此之外,三教在明代深入人心,仁、慈、善等教義是明代商人施行義舉的最大動力。在商人施行義舉的諸多動機中,商人的佛教信仰表現得最為突出。本文打算從商人的佛教信仰切人,集中探討明代的商人有沒有佛教信仰,商人的佛教信仰與義舉之間存在多大的聯系,商人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的可信度有多高等三個問題。希望以此達到對明代商人碑傳文有更加客觀、理性的認識。
一、明代商人的佛教信仰
佛教自產生之初,便與商人結成了緊密的同盟關系,對此,季羨林先生在《商人與佛教》中說:“釋迦牟尼雖然出身于剎帝利種姓,而且有時候以此自傲,但是他和他的繼承者和僧伽所代表的卻是商人和農民吠舍的利益。商人與佛教互相依賴,互相影響,商人靠佛教發財,佛教靠商人傳布,二者的關系有點像狼與狽,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而發展的。”然而,由于上世紀80年代以前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商人的研究還不夠深人,很多相關的文獻資料還沒有運用到研究工作中來,因此季羨林先生只肯定了在印度佛教與商人之間關系密切,認為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于印度,他說:“在中國,佛教與商人風馬牛不相及。因此,要談中國古代商人與佛教的關系,實在無從談起,因為二者根本沒有關聯。”
其實,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傳人中國的佛教就與商人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姚瀟鶇在掌握大量資料的基礎上,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在絲路上的商人,不少都是佛教的信眾,而中土商人在絲路商人中亦占一定的比例,因此,往來于絲路的中土商人中不少應是佛教的信徒。”③明清時期商人與佛教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也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肯定,并形成了一些成果,如郭文麗的《佛教倫理與明清以來江南工商文化精神》,李珍的《論儒釋道對徽商的影響》,趙毅等人合撰的《傳統文化與明清商人的經營之道》,這幾篇論文討論了佛教對于商人經營的影響。然而都存在著缺少直接證據來確證明清商人與佛教之間具有密切關系的遺憾。
汪道昆《太函集》卷二十八《汪處士傳》一文曰:
處士嘗夢三羽人就舍,旦曰得繪,事與夢符,則以為神,事之謹。其后,幾中他人毒,賴覆毒乃免災。嘗出丹陽,車人將不利處士,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覺之,處士自謂幸保余年,莫非神助,乃就獅子山建三元廟,費數千金。
汪處士與汪道昆是同宗,對于汪處士的情況,汪道昆當了如指掌。因此,汪道昆在《汪處士傳》中不僅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為修寺廟不惜花費數千金的虔誠的佛教徒形象,更說明了汪處士信佛的原因,即“自謂幸保余年,莫非神助”。這是中國古代人們之所以信奉佛教的最為普遍的原因。
鄭若庸《蛄蜣集》卷五《胡叔吉小傳》中的商人胡叔吉也可確定是佛教信徒:
居常敬奉緇黃二典,晨夜持誦,或葺治祠宇,圮途廢梁,則不惜傾橐。曰:“非以徼福田利益也。”⑤胡叔吉“敬奉緇黃二典,晨夜持誦”,可以證明他是佛、道二教的信徒,不過,從他標榜自己“葺治祠宇,圮途廢梁,則不惜傾橐”之類的義行,不是為了“徼福田利益”,完全符合佛教的思維方式來看,可知他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更加深刻。
自從唐代三教合流之后。中國人的儒、釋、道信仰就很難截然分開,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既然儒、釋、道三教能夠同時成為某一個人的信仰,難以截然分開,那么我們能做的就只剩下探討三教在商人心中的地位孰高孰低了。呂楠的記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在《湖山處士胡伯行墓志銘》一文中,呂楠說胡伯行:“配許氏,生子三。曰佛寶,曰道寶,皆天死。曰儒寶,尚幼。”⑥胡伯行三子,大兒子名佛寶,二兒子名道寶,三兒子名儒寶,可以說明儒、釋、道三教在胡伯行心中的排序是釋、道、儒。不過,胡伯行之事只能說明胡伯行本身先佛、道而后儒家,要想證明其他的商人也是如此,則需要其他證據。汪道昆在《太函集》中為商人李仲良寫的墓志銘可以說明當時的普遍情況。在此文的開篇,汪道昆即發表感慨:“泰茅氏曰:自道術裂而為三,儒者絀,佛氏滋甚。夫儒服先王之教,曰操功令以徇齊民,然而向者十三,倍者十七。西域去中國踔遠,言語謠俗不通,東渡以來,靡然顧化。其間長者子出,率以信心、直心、深心而得菩提心。”這說明佛教在當時已靡然成風,不僅商人最為推崇佛教,其他階層亦如此。
二、佛教信仰與義舉之間的關系
在明代商人的佛教信仰被證實的基礎上,接下來將探討明代碑傳文中記錄的商人佛教信仰與傳主的義舉之間的關系。在明代商人碑傳文中,大量記述了商人的善行與義舉,這些善行與義舉是否與商人的佛教信仰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呢?答案是肯定的,依據是:
第一,所有能夠確定傳主信奉佛教的碑傳文,一定會有義舉記錄。前文提到的汪處士信奉佛教,其義舉為:
處士善施予,務振人之窮,舉宗或不能喪,則置封域、予葬地;不能舉火,則置田予之租。出入遇僵尸,則屬傭人瘞之,予之值。嘉靖中歲,大旱,太守議發倉,處士則以不便于民,乃以策干太守。饑民自百里外待命郡中,即無留行,猶懼無及于死。假令坐斃以待升斗,如溝壑何?請易粟為金,就而散之四境,富民各輸金以助,不足,某請以百金先。太守用其言,民大稱便。既而又就里中設糜粥,飯饑人。上海亦如里中,中外多所全活。吳會洞涇橋壞,費百緡新之。歸則碣田、由溪各為橋,處士皆出百緡以倡義舉。
與汪處士一樣斥巨資修建寺廟的程次公,其善行與義舉亦與汪處士相近:
然其為術,好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悌,其纖嗇錐刀之末,雖不能與世之賈者異,而賑貧窶,周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以責。浮屠老氏之宮或頹廢,數解橐中裝以佐之。雖累千金不以靳。
又,汪道昆《明故處士李仲良墓志銘》中的李仲良,在信佛以前,未有善行與義舉的記述。一旦信佛,即有善行與義舉:
仲良自言,故以窶人子起賈豎中,不得比一逢掖,幸而喪葬婚嫁畢矣,寧能措措然為奴虜哉。開士喜公,得南宗東游建業。仲良一見,執弟子禮,就舍旁建精舍居之。師曰:“吾不示汝直指正宗,第于彈指間可超無學。”仲良大悟,遂專事西方,既從通公受凈土文,曰茹清齋持佛號。時或掩關趺坐常。歲侵,都民有殍,窮冬率就瓦官寺開講百曰,曰飯餓者數百人。季年益樂檀施梁津,除道不倦于勤。
信佛之前,未有善行與義舉,信佛之后,即有善行與義舉,說明李仲良的善行和義舉與佛教之間有直接的關系。
以上例證均來自明代商人碑傳類文章。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文獻來看,只要能夠確定傳主信奉佛教的明代商人碑傳文,都記錄有類似的義舉。筆者至今還沒有發現有傳主信奉佛教但沒記錄義舉的商人碑傳文。
第二,傳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與佛經中提倡的善行與義舉相合。以上所引商人碑傳文。所記載的善行與義舉大致可以歸納為賑貧飯饑、除道梁津、興修水利、棺斂尸殍、施藥救人、修建寺廟等幾個方面。這與《佛說諸德福田經》中所謂“七法廣施福田”基本上相合。“七法廣施福田”即:“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眾病;四者作牢堅船,濟渡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渡贏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做圊廁,施便利處。”
通過對比可以得知,“七法廣施福田”中所列的七項善行與義舉,唯有“七者造做圊廁,施便利處”一項在商人碑傳文中完全沒有被提起過,這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事。在找不到直接證據說明為什么商人碑傳文不記錄傳主“造做圊廁,施便利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做這樣合理的推測:廁所乃污穢之地,而碑傳文的風格是莊嚴肅穆,將廁所寫進碑傳文,會影響到碑傳文內部的和諧。此外,商人碑傳文中最常見的善行與義舉:賑貧飯饑,并沒有被《佛說諸德福田經》列為“七法廣施福田”之一,不過“賑貧飯饑”是佛教提倡的義舉,屬常識性的知識。佛教度人,其中內容之一就是要使眾生擺脫苦難。《六度集經》就要求佛教信徒能夠做到“饑者食之,渴者飲之,寒衣熱涼”。通過將傳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與佛經中提倡的義舉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它們之間幾乎是完全吻合的,這足以證明商人的義舉與佛教信仰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
三、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不可簡單地視為“諛墓”之詞
通過前文的論述。我們已經證實了明代能夠確定信奉佛教的商人,其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絕大部分是在佛教信仰的推動下,實實在在發生了的事實,而不是為了“諛墓”而杜撰的,這個觀點應該比較容易讓人接受。因此,傳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傳文,并沒有違背傳記文學應當遵循的真實性原則。但是,這并不能證明所有商人碑傳文對傳主義舉的記載,都不是“諛墓”之詞。原因是很多商人碑傳文并沒有明說傳主信奉佛教,卻記載有與傳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傳文大致相同的義舉。沒有確切的證據來證明這些商人的義舉是在佛教信仰或其他動機的推動下產生的,就否定此類商人碑傳文的“諛墓”傾向,是很難被人接受的。
由于商人在明代的社會地位并不高,因而明代商人有名有姓留下來的本來就不多,要想在某個商人的碑傳文之外,再搜集其他的文獻資料來證明他是否有佛教信仰,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能證明這些商人有佛教或其他宗教信仰,就不能為義舉找到合理的動機,因而似乎就沒有辦法為他們的碑傳文洗去“諛墓”的嫌疑。要解決此問題我們必須另辟蹊徑。如果在傳主為不信奉佛教的商人的碑傳文中,完全沒有佛教提倡的義舉的記錄,這應當可以進一步證明商人碑傳文中記錄的佛教式的義舉與佛教信仰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因此,傳主不能確定是否信仰佛教,卻有佛教提倡的善行與義舉,則基本上可以確定是佛教信徒,只是作者沒有明確寫出罷了。現舉例說明如下:
汪道昆在《太函集》卷六十一中有《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一文,其傳主程鎖可以確定不是佛教信徒,他在彌留之際交待子輩曰:
吾故業中廢,碌碌無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潛為人,今已矣。爾問仁、問學,業已受經,即問策幼沖,他曰必使之就學。凡吾所汲汲者,欲爾曹明經修行,庶幾古人。吾背爾曹,爾曹當事,自此始毋從俗,毋用浮屠,毋廢父命,吾瞑矣。
臨死之前的示兒之語,當非虛言。程鎖臨終前交待兒孫之語說明他非佛教信徒,要求兒輩必須不信佛教,死才能瞑目,更流露出了對佛教的反感。程鎖不信奉佛教,因而,墓表中雖然記有程鎖貸母錢薄取利息,谷價上漲時平價出售之事:“長公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母錢,貸下戶,秋倍收子錢,長公居息市中,終歲不過什一,細民稱便,爭赴長公。癸卯,谷賤傷農,諸賈人持谷價不予,長公獨予平價,困積之。明年饑,谷踴貴,長公出谷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但這類義舉并非佛教徒無目的的利他義舉,而只是儒賈的一種經營策略。與佛教信仰無關。程鎖賴此經營策略而使細民“爭赴長公”,與現在通常所說的薄利多銷的商業經營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
康海《對山集》卷四十三《鳳翔處士毅庵毛君墓志銘》一文記傳主毛雄:
十五被選為府學生,遭父喪,哀毀逾禮,葬祭一無紛華。時俗方盛興浮圖,決有弗為者,或以為棄親,共非笑之。高年公家方富盛,而克明又愛子也,顧何有弗為者,君百方婉詞諫止。
毛雄在父親去世之時嚴守儒家葬禮,寧肯背上“棄親”之名,也要諫止他的祖父高年公將佛教禮儀用到其父的葬禮上,由此可知毛雄不信佛教也是發自內心的。相應地,康海為他所作的墓志銘中也不見佛教提倡的義舉,只有儒家提倡的親親之義:“至于處宗族,接姻黨,恭而有禮,親而有恩,孝悌之實,信于鄉人。為妹擇配,深得婚嫁之體,不私貨財,不愧妻子,表然孝義人也。”當非偶然與巧合。
相似的例證還可以舉出一些,但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不過,王九思在《漠陂集》卷十二中為商人秦瓚作的墓志銘《明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秦公合葬墓志銘》卻不能不提。秦瓚“不事浮屠,婚葬營繕,不問術者,貧富窮通,不談祿命”。這說明秦瓚并不信奉佛教,但王九思在為他作的墓志銘中,卻說到了他有類似于佛教徒的善行與義舉:“賑貧贍饑,而造棺百余,給疫死者,祈愈父病。有所假貸,貧不能償,輒復貸之。且以券付郡守,作祠廟,出麥八十斛,以食役徒。”不信佛教的秦瓚似乎也有佛教提倡的善行與義舉,但細讀則可以發現。祠廟是供奉先祖神靈的祠堂,與寺廟完全不同;秦瓚“賑貧贍饑,而造棺百余,給疫死者”也有明確的目的,即“祈愈父病”。“祈愈父病”中的“祈”表明秦瓚的義舉肯定與某種宗教信仰相關,因而此例證并不影響前文所立之論,反而進~步證明了商人碑傳文中記錄的義舉,都是在一定的目的的推動下發生的事實,而非憑空虛構的“諛墓”之詞。只不過,佛教信仰才是這些義舉的最大動力。
行文至此,明代商人碑傳文中所記錄的傳主的佛教式的義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非“諛墓”之詞已基本上得到了證實。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追問。明代商人碑傳文在明代就被批為諛墓,為何現在流傳下來的商人碑傳文中,反而少見諛墓痕跡?筆者的解釋是,明代文人在為商人寫作碑傳文時,肯定有~部分人為了經濟利益而放棄文人應當堅持的原則,極盡諛墓之能事。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必然影響到他們的作品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水平,因而流傳下來的幾率比較低。能夠流傳至今的文集,其作者一般都嚴格遵循文人應當堅持的原則,對諛墓之事很反感。如為徽州商人寫下不少傳記、墓志銘的金瑤在《栗齋文集》卷八《范母吳氏傳》一文的開篇即曰:“余性喜作文,然不喜為人作狀傳,懼犯諛墓中人之戒。”堅持原則的文人,在自我標榜不諛墓的同時,也是這樣做的,如茅坤《歙州處士程次公墓志銘》一文說:“其所最難者,公嘗販粟湖中,以歲侵,價且翔,公第收其什一之息而不忍盡時價以取之。錢進士所綴而稱之者如此,其然邪,抑否邪!然間按公所從予游處覆之,當亦無相遠,庶幾乎。”茅坤此文是在錢進士行狀的基礎之上寫成的,行狀中說程次公販粟,當年收成不好,粟的價格上漲時,依然只取什一之利。茅坤并不敢完全肯定,所以他只說“庶幾乎”,使自己免于因不明真相而被動諛墓。
總之,從明代流傳下來的商人碑傳文來看,明代商人與佛教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佛教信仰是商人施行義舉最主要的動機之一,可以確定傳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傳文中,都記錄有佛教式的義舉:而可以確定傳主不信奉佛教的商人碑傳文中,幾乎都沒有佛教式的義舉。傳主的佛教信仰與碑傳文中是否記錄有佛教式義舉之間的必然聯系,證明了至少碑傳文記錄的傳主的佛教式的義舉,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不可簡單地視為“諛墓”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