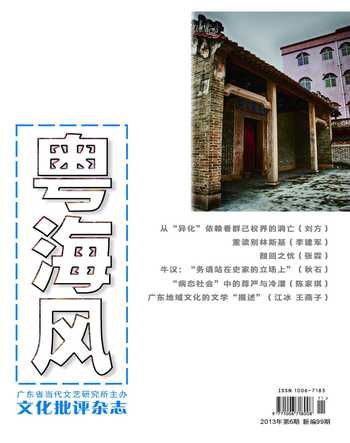“病態社會”中的尊嚴與冷漠
陳家琪
我的手機上早晚各能收到一次“新聞早晚報”,這是官方的正式報道。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9月25日),手機上的新聞依次有這樣一些內容:在北京擁有41套房產的“房姐”龔愛愛、靠劉志軍暴富的“高鐵一姐”丁書苗先后走上法庭接受審判;龔愛愛稱,自己在北京購房時,售樓小姐稱購房可辦理北京戶口,但自己只支付了購房費用,并未為辦北京戶口給他人任何好處,所以自己不構成犯罪。法院將擇日宣判。有質疑說“房姐”擁有眾多房產,但與此前對“表哥”楊達才的審判不提及手表一樣,“房姐”眾多房產的來源等問題并未涉及,他們更關注的是其房產和財產來源,希望有關方面能有所說明;丁書苗則當庭認罪,她非法經營達1858億余元,非法獲利20余億元,為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買官”、“撈人”行賄4900萬余元,向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外資項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行賄4000余萬元;地下捐精者折射出中國大規模“精子荒”的現狀和焦慮,他們中部分人直接與女方發生性關系,每次捐精要給蛇頭1000元;調查稱近九成人不看好“以房養老”;中紀委9月2日開通上線并公開接受網絡舉報后,20天的舉報數量達15253件,日均超過760件;報告稱我國灰色收入超6萬億元;江西南昌公安局將對新建縣樵舍鎮被洗衣機絞死的兩女童進行尸檢;上海一名女嬰,出生僅一周,因患有疾病,回家途中,被爸爸和奶奶拋棄在路邊隱蔽的小樹林中,可憐的孩子在又冷又潮濕的草叢里堅持活了三天三夜,最終被發現送至醫院,不治身亡;滬大學生每月網上支付867元;女兒雇兇在家門口殺父;男子跳橋輕生路人苦勸成功;落馬貪官的N個怨:怨“老婆不好”、怨“不懂法律”、怨“身處染缸”、怨“人情往來、怨“別人重貪”、怨“情人有情”、怨“別人更貪”、怨“工作牽累”、怨“不被理解”……近期“中石油窩案”集中爆發后,四川明星電纜董事長李廣元、前總經理沈盧東及財務總監楊萍,相繼“失去聯系”;專家稱,說小孩患白血病與愛喝飲料有關,這二者之間其實“無證據”;山西芮城副檢察長梁永安嫁女舉辦豪華婚宴,接連四天設宴100多席,并收受大量禮金,被免去檢察院黨組成員職務,建議免去副檢察長等職務;巴基斯坦發生7.8級地震;肯尼亞恐怖襲擊事件結束72人亡;廣東深圳寶安區源記印刷廠員工被扣如廁費……
所有這一切“新聞”,嚴格來說已經算不上“新聞”了,一則時間已經過去了很久(新聞界盛行的說法是要在新聞上爭第一秒);二則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我們誰都知道還有許多更可怕、更殘忍、更血腥、更無恥,也更具有“新聞”價值的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只是不知道或知道了而不敢說而已。
于是,中國幾乎成了一個“無新聞”的國度,因為任何“新聞”,哪怕再驚天動地,也無所謂,發生不發生、知道得早還是晚,甚至知道不知道都變得無所謂了。就是政治局開會時的爭論,別人提及,無論真假,也只是哼哈兩句,既不會動什么真情,更不會產生想深入下去作進一步探究的理論興趣。
我首先承認這與電子媒體的發達有關,它使得人們的神經有了一種普遍的麻痹感;但我更想追問的是:自己這樣一種漠不關心的心態到底是怎樣養成的;盡管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而言,我是一名對各種社會理論的探討都應該深感興趣的讀書人。
應該,事實上也是有興趣,但為什么如此冷漠?
在閱讀上面這些“新聞”時,我幾乎是一目十行、隨意瀏覽,不露聲色地就打發過去了(為了寫這篇文章,才打開又看了一遍,因為恰好昨晚的新聞還未刪除,這本身就很少見),因為幾乎天天都一樣;不是說就沒有了那些歡天喜地、鶯歌燕舞的好消息或“正面”新聞,打開電視,依舊歌舞升平,就與上面那些新聞一樣多,或者說更多、更密集,但依舊讓人無動于衷。
歌舞晚會、迎來送往、參觀學習、交流經驗之類的節目已經有幾年未看過了。
我稱之為一種“社會病態”的冷漠,一種已經滲入人的骨髓的冷漠。
我很怕我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會以為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本該如此,歷來如此。
問題是得讓人聽到那些嚴肅的、不滿甚至憤怒而又不失理論水準的批評。
我很想對自己何以變得如此之冷漠進行一番分析,但這里面馬上面臨兩個陷阱:第一,什么叫“社會病態”;第二,分析,特別是對自己的分析,當然是一種“反思”活動,但“反思”,按照阿克塞爾·霍耐特的說法,很有可能走向一種被稱之為“反思性變形”的心理狀態。對西方人來說,這種“反思性變形”主要表現為只從法律的形式意義上來理解自己的自由,于是把法定的自由看成是自由的全部;在社會關系的法制化已經非常強勢的情況下,出于減輕負擔的理由,這種只把自己作為法律實體,只在法律的范圍內關注主體的互助與合作就會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特征[1]。
于是,“反思性變形”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病態”,只不過是一種較為高級的、通常為知識分子所常有的“病態”而已。就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病態”而言,霍耐特說,它通常可以理解為“第二階段障礙”(second-order disorder),即偏執、固執、只顧及自己、很難自控的壓抑感與沒有方向的情緒性發泄。我覺得我們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暴戾之氣已經遠遠超出了這樣的范疇,我們當然應該把它理解為一種“社會病態”,而不僅僅只是個人性格、心理上的缺陷或障礙。人們通常會從兩個角度看待個人的“惡”:僅屬個人的心理“特質”,或社會的普遍“情景”所造就。當年恩格斯分析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時,就認為英國工人們的搶劫、盜竊,女人們的偷竊、賣淫就應該怪罪于社會情境,因為國家“它把這些已被剝奪了面包的人變成了也被剝奪了道德觀念的人。”[2]這本來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解社會之“惡現象”的一個基本思路;哪怕就是個人心理上的“特質”,也通常會歸結為“社會存在”的決定作用。
在霍耐特,造成“社會病態”的大體思路是這樣的:任何社會都會出現有“不公正”的現象;但如果這種現象危及的是個人生活的基本安全,那么這就是國家強制所保障的法定自由權的缺失。這種缺失首先等于事實上取消了每個個體的自我保護空間;只有在這個空間內,個人才可以按照善良愿望對自己的人生目標進行評估、考察和實驗;這是一種任何力量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沖決的“保護墻”。只有在這個“保護墻”后面,人才可能有勇氣在道理上提出理由,比如對“房姐”、“表哥”的審判為什么會與“房”、與“表”無關,中石油(或上海的幾位高院法官嫖娼)為什么發生的是“窩案”,而不再是單個人的違法作案。所有這些追問的前提,是追問者自己站在“保護墻”之后。沒有了這層“保護墻”,人也就可能放棄掉這層“保護層”在保護你的同時所使你無法脫離的社會義務。人除了納稅以外再沒有、也不可能盡自己其他的社會義務,這就是問題之可怕,仿佛社會變得與自己無關一樣。其次,這種社會義務具體來說也就是每個社會成員都能獲得以同等權利進行社會參與的機會。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如果我們把“保護墻”理解為以法的形式來保護個人的生活或安全是否會受到傷害的話,那么我們必須意識到僅有法的保護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法的保護沒有在任何形式上表現為一種個人自我實現的領域或地方,也不可能為主體提供任何一種實現自己的財富或目標的機會。就是說,法的保護或法定自由與我們現在已經說慣了嘴的“夢想的實現”沒有任何關系。一個沒有法治的社會也就是一個沒有“私人自治”之可能的社會。“私人自治”的核心就是一個人可以自我反省,重新思考自己個人的喜好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必須保證每個人都有一個僅僅屬于個人的“隱私區域”。但有了這樣一個“區域”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社會參與。對于如我們這樣的讀書人來說,以為一旦滿足于這樣的“法定自由”、“私人自治”和“隱私區域”,就很可以閉門讀書,不理睬社會義務之類的概念了,這既可以理解為是“社會病態”之冷漠的原因之一,也可以理解為是在此種狀態下對個人尊嚴的另一種變了形的維護。當然形成此種狀況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信任,特別是社會公信力的嚴重喪失,人們生活在某種焦慮、不確定、不知道明天會怎樣的惶恐不安之中,等等。
南懷瑾老先生早年詩作《務邊雜拾》云:“揮戈躍馬豈為名,塵土事功誤此生。何似青山供笑傲,漫將冷眼看縱橫。”這里面有足夠的“笑傲”,幾乎演變為中國傳統文人典范化了的尊嚴與超脫。
但這與“社會病態”中的“法定自由”有關嗎?
我們真的能“笑傲”、“冷眼”到如此的地步嗎?
盡管我們的“法定自由”還遠遠談不上完善,但更多的讀書人已經在精神上漸漸遠離了社會的現實。毛澤東時代的讀書人確實談不上什么最低限度的尊嚴(遑論傳統的名節、骨氣)。所有在今天被稱之為“大家”的人在1949年后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我們今天并不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也不難想象;而且就連想裝出不知道的樣子都不可能。當然,我這里指的是如我這般年齡大小的人。我們確曾有過不讓讀圣賢書、要批判古裝戲的年代,然而現在似乎又一切走向了反面,以為只要想讀什么書就可以讀什么書,想怎么研究某個專門問題就能怎么研究,這就已經足夠,而且這才是知識分子的本色。胡適就做過這樣的夢,要“拒絕政治,不談主義,認錯,死心塌地學人家”。與胡適的年代不同,那時面臨的是國破人亡,現在是普遍感受到的現代性危機。而這種危機又多少與西方近幾百年來的存在與發展有關(西方人自己的反省已經汗牛充棟)。于是反抗或抵制現代性危機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回到古典,特別是中國的古典,再讀古人,重溫舊夢。我完全明白這一切是多么地有道理,特別對我們這樣一代真的相信一切的一切都必須以毛澤東思想大破大立的人來說,能重新讓讀(而不是批判)那些古書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阿倫特在談到斯大林時說,斯大林后,就出現了兩種普遍性的社會情境,一種是“什么都是可能的,任何事也都是可以做的”;另一種情況就是回顧歷史,總想發現獨立于行動者目的和意圖的“客觀意義”,于是就會對實際發生的事視而不見,“他贊同蘇維埃帝國的工業化或傳統俄國外交政策的國家主義目標,卻忽視了斯大林極權主義獨裁統治的具體特征。”[3]
但,以同等權利進行社會參與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又與所謂的尊嚴有何關系呢?
霍耐特告訴我們,一個人一旦進入法律所規定的個人狀態,就不可能對生活目標實現的前提、實現生活目標所需要的行動進行反思。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可能使人陷入相互攻擊的狀態而無法作為第三者仔細傾聽并理解對方的言論;離婚自由的權利也可能使婚姻伴侶只想到財產的分配而忘記了他們以往共同生活的經歷;如此等等,都說明主體的權利訴求常常只是一種“一時的例外狀態”,這種狀態其實只是一種生活流程中的“暫停”。請注意:“打官司”、“訴諸法律”,只是日常生活正常流程中的“例外”與“暫停”,這是一個很深刻的道理。正是在這一“暫停”中,個人才有可能意識到存在于每個相關主體相互間的日常生活關系其實更多的是“非法律關系”,或者理解為“前法律關系”。這種“非法律”或“前法律”的關系告訴我們:只有依靠相互的體諒與合作,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才能繼續傳承下去。“法定自由”應當造就一種個人自由的模式,但它既不能為這種模式提供生存的條件,也不能使它維持下去。個人自由的模式說到底依靠的是道德實踐中的合作主體而不是由法律建立的社會關系。
然而現在的問題卻變成了:作為一種“社會病態”,我們發現我們時時處處都生活于各種法律所建立起的社會關系之中,包括對“中國式過馬路”的懲罰、城管行為方式的規范、多長時間不探望父母應怎么怎么樣、轉發什么郵件500次以上、中學生發帖對公共事件的詢問、質疑就會擾亂社會秩序,飛機上發生了什么就會怎樣、高鐵或動車上什么行為是違法的等,一切人際關系都變成了法律關系,而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實踐,相互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卻變得異常困難、危險和緊張。
霍耐特的基本意思是要告訴我們,除過接的、法定的消極自由(對個人權利的維護)和間接的、反思的積極自由(自我實現的善的理想)之外,還有社會的自由,比如友誼與愛情,那是一種社會化或客觀化的自由,它體現為相互間的獻出與認同,而不是法律的維護與自我的實現。
這種社會的自由說到底是一種非法律、非制度化的社會實踐過程,它所針對的首先就是冷漠;因為只有通過別人目的的實現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如黑格爾一樣,他也把這種社會實踐過程稱之為“以現代的機制化了的倫理為結束點”。
霍耐特特別強調了黑格爾的社會自由思想,他顯然比別的現代的自由思想,與前法律、前理論的社會機制與社會經驗有著更多的相同性,因為在黑格爾心目中的個人,其自由程度更多依賴于他們所處的環境與行動領域:“主體越是能夠感受到他們的目的被那些與他們有關的人所支持,最起碼是被容忍,那么他們就越是能夠感受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是一個他們自己個人得以發展的空間。”[4]霍耐特認為這是一切有關個人自由理論的典范;在黑格爾心目中,是用“在自己那里,卻又是在別人中間”這樣一種類似于直覺的語言表述出來的。
所有這一切,當然與霍耐特所想表述的承認理論有關。對這一點,我們可以暫且按下不表,我最為關心的還是當代那種中國文人的變了形的尊嚴。
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或者把個人的尊嚴直接就等同于國家的尊嚴,認為自己與國家一體,特別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如何才能“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或者把二者完全割裂開來,因為太多的經驗讓我們知道了“兔死狗烹”的道理。任何一個讀過幾本古書的人都知道中國知識分子“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與悲慘下場。其實不用讀多少古書,一面是“革命不斷吞噬著自己的兒女”,另一面就是每個人都踴躍從政,以為自己可以解民族于危難之中,“文革”以來,我們誰不這樣?
還是南懷瑾:“憂患千千結,山河寸寸心。謀國與謀身,誰識此時情。”
中國之士,怎么可能從“謀國與謀身”的糾結中掙脫出來?
一面是理論上的“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把儒家學說神學化;一面在實際施政措施上又是“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這大約也就是今日許多學人心目中的“復興之夢”。
無論是“存亡國,繼絕世”,還是“霸王道雜之”,看似眼睛朝內,其實都是為了對付外在(這里的“內”、“外”其實并無界限)的“敵人”,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唯一依賴就是民族感情或曰民族本性中的“命”。
如果既不這樣,又不似南懷瑾先生那樣“冷眼”,更不必如現在的“道德榜樣”那樣在“社會倫理的機制化運作”之外踐行個人的道德理想,那么是否還有著另外的個人意義上的人格尊嚴呢,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理論問題。
讓我們還是從黑格爾說起。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第253節中說,一個人在家庭中是有尊嚴的,因為他屬于一個整體,而這個整體本身又是普遍社會的一個環節,他對于自己這個整體(即家庭)是無私的,所以他在家庭里也獲得了承認,他在他的等級中具有他應有的尊嚴(這里的等級二字是打了著重號的);但當一個人來到社會上,比如在同業公會里,他不可能全身心地付出,因為身邊都是各自心懷不同目的的他人,所以他就沒有了等級尊嚴;并由于他的孤立而被歸結為營利自私,他的生活和享受也就變得不穩定了。因此,他就要用外部表示來證明他的成就,借使自己得到承認。這種外部的表示是沒有止境、沒有限度的,因為對他來說等級并不存在,他也談不上按他所屬等級的方式來生活。總之,他無從建立一種相當于他等級的、比較普遍的生活方式。
以上這段話基本上是原文照抄,其中重要的兩點是:第一,人生活在不同的等級中,他的尊嚴既非來自某個具體的“他人”,也非來自抽象的“社會”,而是來自他所屬等級對他的承認,而所謂的“等級”,就指的是一種普遍化了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觀念、感興趣的共同話題等);第二,當一個人在自己的等級中是孤立的,或根本就不屬于或尋找不到自己所屬的等級時,他就只能靠自己的外部成功來贏得尊嚴。這種外部成功的標志是無止境的,甚至幾百個億都不足于證明他的成功;而且他的成功一定是以別人的失敗為代價的。這也就是市民社會(所謂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競爭秘密。
這一秘密后面更大的秘密就是人際間的疏離與冷漠;惟有的,就是所謂“法定自由”對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維持與保護了。
我們以前認為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缺乏人情味,就指的是這種“法定自由”的限定與規范。但在這種限定與規范之外的“非法律”或“前法律”的日常生活的主流,卻是我們所知甚少或者根本就無從了解的。這些年出國的人多了,大家才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覺。但對為什么稱“法的關系”為生活常態的“例外”或“停頓”(只有這樣才涉及傳統的價值與意義),從理論上去思考的人并不多。
對個人來說是這樣,對任何一個企業來說也是這樣。《粵海風》要出滿百期了,《讀書》還在辦,而且風格依舊,還有《書城》,各自的難處自當遠遠大于我們個人所要維護的東西。對這些刊物而言,除了用外在的“成功”(也幾乎是無止境的)來標識自身的尊嚴外,還能怎樣在“同業公會”中獲得自身的尊嚴?當然,這又取決于此類“同業公會”是否屬于一個整體,是否能以同等資格在參與信息交流中調節各自的潛能。這是霍耐特所認為的不要僅僅把自己視為一個“法律實體”的第一步措施;第二步就是在自由思想的領域里把主體的互動與交流視為一種“即時”的義務,而不是“無限期地推延”。
對我們這些讀書人來說,依然有著不同等級中的承認形式,為了獲得這種承認,努力也依然絕無止境。有些人更多獲得了能用外部成功來證明自己已獲得承認的資格,當然最強有力的資格一定是從國家手里獲得的。而另有一些人,或者說更多的人,則不得不以扭曲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尊嚴。于是就有了我在前面所說的冷漠,或者理解為不介入、不理睬、不表示、不動聲色。有的在埋頭寫作,更多的人在冷眼旁觀。通過媒體發出聲音,讓更多的人認識自己的人,畢竟也是一種不甘寂寞的方式,其中不乏具有社會良知的人,但他們顯然無法獲得以國家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認可。
問題在于尊嚴屬于一種主觀價值,它既不是某種絕對不可放棄(如生命、食物或者財產)的道德原則,又不得不具有某種依附性,即事實上不得不來自某種實體性存在的認可(這兩點參照了Dr.Philippe Brunozzi的說法),于是,黑格爾所說的“等級”,在哈貝馬斯那里也就成為了一種“身份的認定”。社會既然可以把某種身份賦予你,當然也就可以剝奪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發現身份、尊嚴、人格、等級,其實都不得不依附于某種“普遍性平等原則”下的“特殊性差異原則”之上:沒有普遍性原則,當然也就無平等可言;沒有了平等,何談尊嚴;但沒有了“差異性原則”,個人的獨特性如何得到包容?沒有了包容,當然也就談不上尊嚴。把這個原則引申一下:所謂的社會參與主要是政治參與,政治參與中的普遍性(每個人都能以同等權利參與社會政治活動)與特殊性(不同的參與方式與多元理念)就應該是從黑格爾到霍耐特所理解的機制化了的倫理尊嚴了。
所有這一切都并不是多么深奧的理論,只要冷靜下來,想想直接的自由(什么東西在維護著我們,又維護著我們的什么)、間接自由(在維護著我們的東西之外,什么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善),然后再想想社會的自由(相互、共同、彼此的交往與實現,在自己那里,卻又是在別人之中),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首先是讀書人,真的已經沒有了什么共同可交流的話題。誰的文章能發表,發表在何種等級的刊物上,會獲得什么稱號,給予多少獎勵,種種不同的以國家面目顯現出來的承認(表彰)方式,早已使個人所要維護的尊嚴不得不隨波逐流而去;因為誰都知道什么話可說,什么話不能說,說了也發表不了。這就給任何可能的爭論框定了一個不公平的背景。
在此情況下,恐怕也就只有了“漫將冷眼看縱橫”式的自我尊嚴了。
如果國家利益、民族團結就是最大的道,最高的天,而這樣的天道就體現在“階級斗爭”與“改革開放”的對立統一上,那么這種尊嚴與冷漠說不定就是最無害的主觀道德。盡管社會自由、公共道德,機制化了的倫理常規和義務都已經變得越來越陌生,而且越來越沒有了多大意思。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
[1]參見《自由的權利》一書,第140頁前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4月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56頁。
[3][4]阿倫特著《過去與未來之間》,中譯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4、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