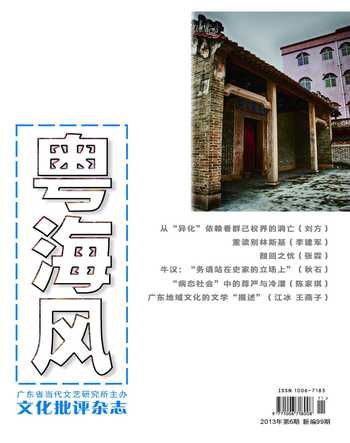重談考據學
考據,這一傳統的研究方法,和我們漸行漸遠。據說,一篇即使有學術分量考據學論文,也很難找到發表的園地。甚至有人預言,考據已被時代拋棄。如此,應加快申報中國傳統考據學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步伐;否則,將愧對我們的祖宗。
其實不必,考據學不僅有著光榮的歷史,也承載著推進現代學術的責任。考據學實在太古老,和我們的文化傳統相伴。《禮記·禮運》云“以考其信”,考信即檢查核實以取得可信的證據。可見,考信就是考據。需要通過考核的手段才能獲取可信的證據,則意味著社會生活及其相關文獻中真偽雜存。《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為什么虞夏之文可知呢,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說,因為《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諸篇,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也就是說,要講清楚虞夏之事,必然要依靠《尚書》文獻的記載,才能考信。
孔老夫子在《論語·八佾》中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也。”而《孟子·盡心下》卻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彼此好像有點矛盾。孔子說有書能征引即可考證事實,而孟子說有書也不行,不能完全相信書上的記載。文獻、書,今天所謂材料。孔子感嘆有材料才能言說,沒有材料可供征引則不能隨意解說;孟子則斷言,材料有真偽,只有通過甄別后才能使用,如果隨便引古書材料加以闡述論證,會出差錯。其實兩者是針對不同的文獻背景而言的,本質上一致,一是重文獻,二是重辨偽。兩者結合起來就能搞清歷史事實。
現代考據學與傳統考據學有一定差異,在舊學時代,由于經學占統治地位,考據學很容易產生皓首窮經、支零瑣碎的弊端,而現代考據學有了學科意識,而且講究用不同學科的知識、成果和方法去完善傳統考據學。[1]近年來學術界出現許多用考據學方法解決學術問題的成果。這里僅用自己近年來從事的一些專題研究為例,說明文獻考據學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時也以此說明當代學術研究中學科交叉的必要性、重要性。
一、考古文物與文獻互證
文物的出土面世,必然有助于學術的發展,如漢簡出土對《詩經》研究的推進,對孔子詩學的進一步闡釋就是最好的說明。
在儒家的詩學理論中,很長時間內“神話”是缺席的,孔子認為學詩的功用之一是“多識鳥獸草木蟲魚之名”。重客觀、重實物,而“不語怪力亂神”,所謂“怪力亂神”卻能啟發人們的想象力,“怪力亂神”也是人類在某一階段對世界認識的反映,因其神秘,并不容易講清真實世界與想象世界之間的內在關系,故孔子不言。
《莊子》的開篇是《逍遙游》:“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這樣的描述當屬于“子不語”之列。
《莊子集釋》引方以智的觀點說:“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為大魚之名。”《爾雅》云:“鯤,魚子。”韋昭注《國語》亦云:“鯤,魚子。”成玄英疏云“何以鯤化為鵬而南飛”,“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啟明之方;魚乃滯虛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舍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徑耳。”且不論莊子“鯤化為鵬”的哲學內涵,只就“鯤”與“鵬”之間的關系而言,也是眾說紛紜,鯤為魚子乃其一義。試問:至小之魚子化為至大之鵬反映了古人怎樣的思維方式?成玄英的疏解至少啟發人們思考“凌虛之物”和“滯虛之蟲”的關系。這一關系在莊子以前已經出現,李白《蜀道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其中,魚鳧是古蜀國的君王,顯然他和堯、舜、禹的單名不同,一個君王的名字是用魚、鳧兩種動物復合而成的,如成玄英所言是“凌虛之物”和“滯虛之蟲”的組合。從《莊子》所述“鯤化為鵬”來看,魚和鳧之間所對應的關系也應是由甲化為乙的關系。從莊子文中可知“鯤”和“鵬”之間微妙處在“化”,而“魚”和“鳧”之間最微妙處亦在“化”,因“化”而具有神秘性。而“魚”能化為“鳧”不僅是神秘的,而且因神秘具有了超凡的能力和權威,這樣的人在初民中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群體秩序中占有了統治權,成了君王。
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有一把金權杖,它的上面繪有“魚”和“鳥”的圖形,被認定為古蜀國君王魚鳧的佩帶物。這進一步確定了古蜀國君王以魚鳧為名的準確性,也證明了古史傳說的可靠性。[2]因此,莊子把鯤化為鵬作為論述自己思想的起點,其意義不同于一般。所謂“鯤化為鵬”的認識在莊子那里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遠古人類認識世界的特殊視野和方法。在學術研究中,不語“怪力亂神”阻礙了人們獲得對上古世界的完整認識。從研究方法上看,用出土文物和紙上文獻相印證,也是學者們一直重視的研究手段。
二、宗教文化與文獻新證
四聲的發現常和佛教傳入中土聯系起來,其中重要的線索是由“詠經則稱為轉讀”而來,因詠經而有聲調相協的要求。但真實的情況如何,尚要考察。佛教“轉讀”之“轉”為何義?轉讀不是簡單的“詠經”,而是重在“轉”,“轉”一般釋為“囀”,這樣就把“詠”和“囀”當近義詞組對待,可惜找不到原始文獻提供的支持,而用文獻考據法,這一問題會獲得全新的認識。
轉讀之“轉”,可和“譯”對應。《出三藏記集》卷七:“轉之為晉。”卷九:“直令轉胡為秦。”卷十三《支讖傳第二》:“即轉胡為漢。”卷十:“提婆于是自執胡經,轉為晉言。”“轉讀”之“轉”,又會和“傳讀”、“傳譯”之“傳”義近而同用。“轉”、“傳譯”也指梵語和漢語之間的互譯,即梵語譯為漢語,或漢語譯為梵語。
四聲和佛教關聯還有另一種解釋,因梵唄而認識四聲。梵唄乃天竺歌贊,無關漢語漢音。事實上,梵唄可以不和漢字關聯,只是和梵音聯系。
從翻譯和誦讀佛經的實際看,一種具有表演性的佛經傳唱,應該以意思傳達為先,如果是長篇經文的傳播更是如此。因此,所謂“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就應該是性質不同的兩類傳播方式。《高僧傳·鳩摩羅什傳》載:“初, 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 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詠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合嘔噦也。”可見最初的“梵唄”是不能“改梵為秦”的,這是通例。“轉讀”與“梵唄”對應,是“經”與“贊”傳播方法不同的表述,“梵唄”體現了中土仍保留天竺歌贊的方法,“轉讀”字面意思雖然不能完全傳達出中土詠經的準確意思,但其概念一定是對當時某一現象的歸納,它與“梵”的對應,已充分體現出由“梵”轉“漢”的內容。用“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來描述和定名天竺“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是非常簡約的做法,富有智慧。“梵唄”表明在中土的歌贊部分是對天竺“唄”的原封不變的使用,“梵”不僅表明來源和屬性,也和“轉讀”相區別;“轉讀”表明在中土的“詠經”已不同于天竺的“詠經”,其中重要的內容是已將梵文的經翻譯為漢文的經,所詠之經乃漢文之經。[3]既然如此,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梵唄就不存在關系,至于四聲發現的機緣為何應另尋路徑去解決。
三、域外文獻與四聲關系
如果四聲和佛經轉讀、梵唄無關[3]的論證是以文獻考據破舊說,那么對四聲與吳音之間關系的論述,則是試圖去尋找另一種證據,以證明四聲的發現只是漢語內部兩種不同的發音方式所致。這一發現應發生在東晉到南朝宋齊階段,這一時期有一場漢語語言內部的沖突,其激烈程度以及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而這一沖突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獲,人們因之發現了漢語中一直存在而不為人知的秘密,漢語有聲調,進而在詩歌寫作上將漢字的讀音約定為四聲。在論述這一過程時,成書于1287年的日人了尊《悉曇輪略圖抄》成了考據中的重要例證,《悉曇輪略圖抄》云:“吳漢音聲互相搏,平聲重與上聲輕,平聲輕與去聲重,上聲重與去聲輕,入聲輕與同聲重。”[4]書中并附有一音位圖,讓人直觀認識到吳、漢音摩擦而有了漢字聲調的分別。這里的吳、漢音聲,即日語音讀中的吳音和漢音,可以理解為南方音系和北方音系。“相搏”,相搏擊,相互接觸、相互切磋,模擬發音,揣摩異同。這為我們提供東晉南北朝時“金陵”、“鄴下”音相互接觸,辨析聲調,產生比較音韻學的佐證。這種規律中古已經存在,故了尊所概括的南方音系和北方音系的比較關系可以施行于東晉南北朝的“鄴下”、“金陵”音的比較、辨析之中。吳音和漢音的音讀差別大致上反映了六朝時期的南方音系和唐朝長安音系在音韻上的發展變化。[5]這里有兩個事實需要強調,一是了尊《悉曇輪略圖抄》雖然成書于1287年,但其反映的規律卻早已存在于日語的音讀中;二是唐朝的長安音相對于南方音系可視為和東晉洛陽音同屬一個音系,都是北方音系。
四、音樂背景與文體形態
在詞和音樂的關系上,將之表述為一個過程極其重要:曲調、曲辭、詞譜階段。看下面一段學術公案,繆荃孫《柳公樂章校勘記跋》云:“宋人詞集,校訂至難,而柳詞為最。如《傾杯樂》八首,‘樓鎖輕煙一首,九十四字,分段;‘離宴殷勤一首,九十五字,‘木落霜洲一首,一百四字,均不分段;‘禁漏花深一首,一百六字,分段;‘凍水消痕一首,一百七字,分段;‘水鄉天氣一首,‘金風淡蕩一首,一百八字,‘皓月初圓一首,一百十六字,均不分段,或作《古傾杯》,或作《傾杯》。宜興萬紅友云:柳集‘禁漏一首,屬仙呂宮;‘皓月、‘金風二首屬大石調;‘木落一首屬雙調;‘樓鎖、‘凍水、‘離宴三首,屬林鐘商;‘水鄉一首,屬黃鐘調,或因調異而曲異也。然,又有同調而長短大殊者,只可闕疑。”[6]繆荃孫指出柳詞八首的字數和分段情況,實已提出疑問。而引萬樹語,以為字數不同可能是調不同而造成的,這只是部分釋疑。但也有同調而長短大不同的情況,如“‘樓鎖、‘凍水、‘離宴三首,屬林鐘商”,“樓鎖”九十四字、“凍水”一百七字、“離宴”九十五字。又如何解釋?事實上,樂曲調高的改變,并不影響其基本結構,與配合的曲辭字數也無關聯。一個曲子不同調并不影響與之相配合的歌辭字數的多少,即同一曲子不同調而歌辭字數可以相同,同一調子字數也可以不同。只能如前所述是按照演唱曲子的狀態創作的,即劉禹錫“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之意,這里有一個前提,白居易《憶江南》詞在先,而劉禹錫寫作在后,故白、劉二人所作詞式相同。如真依照《憶江南》原曲寫作,因對《憶江南》曲子的“曲拍”理解不同,依曲填的詞的結構、字數等未必相同。
柳永創作的詞“變舊聲為新聲”是真正依曲子的“曲拍”寫作的,故有一曲多調,一調又有字異、體異之特點。字多或少很容易理解,如上引民歌《月兒彎彎照九州島》,既可以唱成現在的7個字,也可以唱成3個字,又可以唱成9個字。字式方面的問題易于解答,而體式方面的問題會復雜得多,即現代意義的符干、休止符等確定在何處,而聽者又如何去感覺和判斷其所在的位置。于此可以簡單解釋繆荃孫的“分段”與“不分段”之惑。[7]柳永詞所反映的正是唐代曲辭配合的活態,是極為難得的材料。這種尋求歷史和邏輯相對應統一的方法,也可以理解為考據的方法。現在用方言考求漢字古音的音讀,也是這一方法的應用。
討論文獻考據學的當代運用,好像是沉重的話題,無法輕松。但有一種現象的出現又讓考據學者少許有些樂觀起來,有些現代文學研究者已在關注文獻考據學,并要建設現代文學的文獻考據學。多年前曾和中山大學黃修己先生討論現代文學研究中文獻考據的使用情況,他舉出一位魯迅研究學者在《魯迅粵港時期史實考述》中對所謂魯迅說“共產黨是火車頭”的歷史事實訂正,認為“就這一條考證,其價值也勝于長篇累牘的泡沫文章。這才叫真學問”。不僅如此,當代文學研究者也有強烈的愿望,要按研究古代文學的方式,進行長期的資料收集和積累,“重建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之間的歷史聯系,在學理上逐步完成相對完整敘述,使當代文學不僅是一個可批評的對象,同時也是一門歷史脈絡看得清楚的學問,這一長期、繁瑣和細致的研究工作,需要當代文學史同仁的共同努力。”[8]如此“長期、繁瑣和細致的研究工作”,大概繞不開文獻考據學的方法。
不管怎么說,考據是奔著問題來的,不必為考據而考據。以問題為導向的現代考據學,為學術研究的真實性、厚重性提供著材料上與方法上的支撐,為學術發展求真求實、去除浮躁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
[1]戴偉華、趙小華:《現代學術與傳統考據學——陳尚君教授〈全唐文補編〉及其相關成果的意義和方法》,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06年,第16卷第2期。
[2]戴偉華:《唐詩中“杜鵑”內涵辨析——以“杜鵑啼血”和“望帝春心托杜鵑”為例》結束語,《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3]戴偉華:《佛教轉讀與四聲發現獻疑》,《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
[4]大正藏卷八十四,2709號,657頁。
[5]戴偉華:《四聲與吳語》,《學術研究》2013年,第10期。
[6]繆荃孫:《柳公樂章校勘記跋》,《藝風堂文續集》,清宣統二年刻民國二年印本。
[7]戴偉華、張之為:《唐宋詞曲關系新探——曲調、曲辭、詞譜階段性區分的意義》,《音樂研究》2013年,第2期。
[8]程光煒:《當代文學六十年》主持人語,《文藝爭鳴》2013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