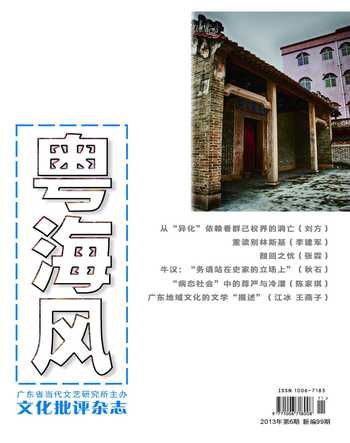《歐游漫錄》:徐志摩眼中的蘇俄
劉紀新 王玲珍
1925年3月,徐志摩取道蘇俄赴歐洲,在蘇俄游歷多日,兩個月后寫下游記《歐游漫錄》,記載了在蘇俄的見聞。這次游歷對于徐志摩影響很大,促成了他的思想轉變。此前,他曾經贊美蘇俄“代表人類史里偉大的一個時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徐志摩《落葉》)。此后,他卻轉向抨擊共產主義革命,并出現了《秋蟲》、《西窗》等具有一定反共傾向的詩歌。
在這個時期,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前往蘇俄,探尋這個新世界的真相。中國也出現了到蘇俄游歷、考察的熱潮,由此也誕生了很多游記,在這些游記中絕大多數都是贊美蘇俄的。與之不同,在徐志摩的筆下,蘇俄卻是一幅陰暗、混亂的景象,《歐游漫錄》為中國人帶來了一幅截然不同的蘇俄圖景。
文 化
作為一位詩人,徐志摩尤為關注蘇俄的文化狀況,在《歐游漫錄》中,他痛惜地看到俄國的傳統文化正在遭到鏟除。“在這大火中最先燒爛的是原來的俄國,專制的、貴族的、奢侈的、淫靡的,ancient regime,曳長裙的貴婦人,鑲金的馬車,獻鼻煙壺的朝貴,獵裝的世家子弟全沒了,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小說中的社會全沒了。……俄國的文化是蕩盡的了。”徐志摩在莫斯科期間曾經拜訪托爾斯泰的女兒,據這位年過六旬的老太太說:現在的書店里,托爾斯泰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徐志摩又問她:莫斯科還有哪些重要的文學家?她說:“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在《歐游漫錄》中,徐志摩記錄了一則趣聞:列寧死后,列寧太太到法庭上起訴早已去世的托爾斯泰,指責他的書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觀,與蘇維埃精神不符。她說,列寧去世前曾叮囑她一定要想辦法取締托爾斯泰的書,否則蘇維埃有危險。法庭判決列寧太太勝訴,把托爾斯泰的書全部毀版,并把已經印刷的書全部毀掉,用來生產再生紙,改印列寧的書。在今天看來,這件事既可笑又富有寓意。徐志摩特意向托爾斯泰的女兒問起此事的真實性,她只是含糊其辭,沒有做正面回答。
《歐游漫錄》不僅描述了俄國傳統文化被摧殘的狀況,而且也努力尋找新的文化,但是蘇維埃文化并不是徐志摩所喜歡的。在莫斯科期間,徐志摩曾經看過一部戲劇,并在《歐游漫錄》中詳細地記載下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部戲在藝術手法上應該屬于現代主義,舞臺正中懸掛著一只“可怖的大手”,象征命運或是資產階級,舞臺上頻繁出現各式各樣的鬼和尸體,讓徐志摩感覺這個戲如同一場“怖夢”。戲的主題是揭露資本主義的黑暗,社會沒有前途,生命沒有意義,工人、醉漢、賣淫女、強盜、孩子等下層人民都有相同的命運:要么在階級壓迫下生不如死,要么在革命中死去并獲得永生。這種完全為政治服務的作品,當然不是徐志摩所喜歡的,他寫道:“那戲除了莫斯科,別的地方是不會有的,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怖夢制造廠。”
為了遠離混亂的現實,徐志摩到墓園懷古,尋求安慰,可是夕陽下蕭瑟的墓園讓他更為凄惘。很多貴族的墓遭到損壞,“不少極莊嚴的墓碣倒在地上”,“好幾處堅致的石闌與鐵闌”被砸毀。此情此景,令徐志摩慨嘆:“階級的怨毒在這墓園里都留下了痕跡。”在契科夫的墓前,徐志摩憶起契科夫生前是一個喜歡幽默的人,不由得追問:“今天俄國的情形,今天世界的情形,他要是看了還能笑否?”
日常生活
作為一位詩人,徐志摩并不擅長理性分析,他更喜歡用詩人敏感的神經去體驗這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歐游漫錄》為我們留下了一幅生動的20世紀20年代蘇俄日常生活畫面。
這是徐志摩筆下的莫斯科:“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鋪是不見的了,頂多頂熱鬧的鋪子是吃食店,這大概是政府經理的;但可怕的是這邊的市價:女太太,絲襪子聽說也買得到得花十五二十塊錢一雙,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們四個人在客棧吃一頓早飯連稅共付了二十元。”“男子的身上差不多不易見一件白色的襯衫,不必說鮮艷的領結(不帶領結的多),衣服要尋一身勉強整潔的就少。”“工人滿街多的是,他們在衣著上并沒有出奇的地方,只是襟上戴列寧徽章的多。小學生的游行團常看得見,在爛污的街心里一群乞丐似的黑衣小孩拿著紅旗,打著皮鼓瑟東東的過去。”走在莫斯科街頭,徐志摩覺得自己有些窘,這種窘與在英國的窘不一樣。在英國他感覺自己仿佛是一個“外國叫花子”,在莫斯科,徐志摩的窘正好相反,不是因為“穿得太壞”,而是因為“穿得太闊”。
“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者報酬一律平等,帝俄時代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享有的特殊地位隨之喪失”[1]。不僅如此,由于蘇俄對知識分子采取嚴厲政策,“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則在經歷著政治和思想風暴的同時,體驗著經濟上的窘迫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種種困境”[2]。在《歐游漫錄》中,徐志摩兩次寫到莫斯科教授的生活。他們的房間簡陋、擁擠:“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張椅子,墻壁上幾個掛衣的鉤子,他自己的床是頂著窗的,斜對面另一張床,那是他哥哥或是弟弟的。”教授的個人形象更是窮困潦倒、落拓邋遢:“他只是穿著一件毛絨衫,肘子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發,一臉斑駁的胡髭”,“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大概就是他的被窩,頭發是一團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經爬梳過的痕跡”。
在《歐游漫錄》中,徐志摩還詳細記述了一位蘇俄時期的列車服務員。在蘇俄時期,人們改稱服務員為康姆拉特,類似于中國人所說的“同志”。不過,列車上的這些康姆拉特們服務態度極為惡劣,讓從未體驗過計劃經濟體制的徐志摩驚訝不已。其中一位因為蠻橫、霸氣外露,被徐志摩戲稱為“飯車里的拿破侖”。“他每回來伺候你的神情簡直要你發抖;他不是來伺候他是來試你的膽量……他也不知怎的有那么大氣,繃緊著一張臉我始終不曾見他露過些微的笑容……他的臉上籠罩著西伯利亞冬的嚴霜。”“他每回來招呼吃飯,就像是上官發命令,斜瞟著一雙眼,使動著一個不耐煩的指頭,舌尖上滾出幾個鐵質的字音……”這位康姆拉特的形象,讓我們回想起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服務行業的狀況。
徐志摩筆下的蘇俄,與20世紀30年代之后大批左翼知識分子筆下的蘇俄截然不同。一方面,因為徐志摩訪蘇時期正是蘇俄最困難時期;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重要的方面,徐志摩是“自由行”,沒有接受蘇俄政府的安排。與徐志摩不同,30年代左翼知識分子的訪蘇活動,大多受到了“蘇聯旅行社”以及蘇聯“外交文化協會”等機構的接待,他們的行程、會見的人、訪問的機構都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試想,如果徐志摩在這些機構的控制之下訪問蘇俄,他不可能與托爾斯泰的女兒自由交談,不可能隨意拜訪那些落魄的教授,也不可能遇到康姆拉特們惡劣的服務。
經歷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都還記得那時中國接待“外賓”的方式。那時,“外賓”要去哪里參觀,與誰會面,都是非常嚴肅的大事情,政府要做周密的計劃。“外賓”們根本不可能與老百姓自由接觸,他們也不可能看到真實的中國。可以做這樣一個設想,假如徐志摩沒有英年早逝,假如他能夠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自由地漫游于中國大陸,不知會有何種感慨?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1][2]張建華《20世紀20年代蘇聯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地位》,載《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