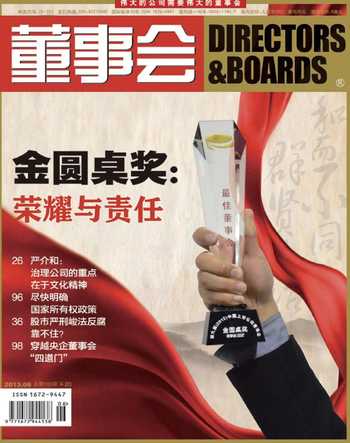“制度催生小人”是悲劇
何志聰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資本市場逐步發展壯大,特別是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較好地解決了公司治理制度層面的缺陷,促進了資本市場的成熟。然而,中國式的權力尋租卻隨之而來,較大地弱化了這次改革的成果,許多問題隨著2009年公司上市節奏加快而集中爆發。
從那時起,中國資本市場監管更多地被貼上“牌照”的標簽,上市融資需要牌照(券商保薦),資金投資也需要牌照(私募或QFII)。“牌照”就意味著審批,審批就意味著市場化過程的速度放緩。
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一方面從市場監管來看,表現出極強的“剛性”,即在規章制度的條條框框及程序中辦事,有時甚至是人為的所謂“公事公辦”;另一方面,從企業決策來看,表現出極強的“柔性”,企業發展的任何“微動作”無論是戰略制定、企業并購還是業務運營,都是一個柔性的事件,商業機會可能稍縱即逝(比如融資與并購),今天的機會等到明天可能就轉化成了風險。“剛性”與“柔性”掌控得好,就叫做剛柔相濟,攜手共贏;掌控不好,就是剛柔不濟,兩敗俱傷。掌控是否平衡需要在不同發展階段調節尺度(可喜的是,我們看到最近兩年這種平衡點已經在發生位移)。
當前,中國的資本市場表現出來的恰恰是“剛性過度”,破壞了企業發展自身所具有的“柔性”。從而,某種意義上出現了“制度催生小人”,即企業為了迎合這種“剛性”,而被迫扭曲企業發展路徑或者節奏,比如我們所看到的的一系列短期行為,包括財務虛假、內部交易、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問題。
僅僅依靠規則、程序、評分評級、窗口指導等,難以幫助上市公司去改變其所處的“生態環境”,或許我們可以從上市公司的利益相關者著手,幫助企業構建和完善其治理體系。
治理體系重點要解決其核心要素,即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問題,引導各利益相關主體,規避短期行為、重視長期行為。上市公司利益相關者,從內而外,一共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從當前實踐上看,股權多元化和管理層持股仍然是治理短板,大股東“一股獨大”現象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較為普遍,企業內部無法形成利益一致的捆綁機制。在國有企業中,大股東“一股獨大”容易發生干預上市公司事務、關聯交易違規等問題。在民營企業中,“一支筆”現象嚴重,虛假上市、財務造假等案例不斷涌現。
第二個層次,即上市公司的內部監督機制,涉及眾多主體,包括會計師、律師、財務顧問等。這些主體與上市公司接觸過密,利益相關,再加上其違法成本極低,很容易喪失公正性和獨立性,從這點看,監管層有必要提高行業門檻和集中度,培育知名品牌,同時從制度層面明確和提高其違法或失職成本。
第三個層次,即外部監管,呈現出多個層次,包括證監會、交易所和當地的證監局。僵硬的行政化管制束縛了上市公司的手腳,也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各種成本,如何將“權利置于陽光之下”,簡政放權是證監會改革的一大趨勢。
總體而言,中國資本市場的成熟和發展并非能一蹴而就,很多制度變革需要考慮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各階層利益及技術條件的成熟,但我們可以從如何幫助上市公司構建治理體系這些基礎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在外部市場不斷成熟的環境下,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