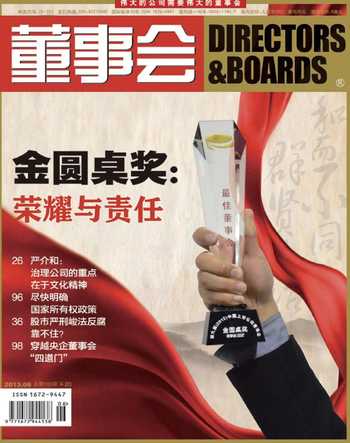挖掘董事會戰略潛能
Chinta Bhagat Martin Hirt Conor Kehoe

通常的年度戰略調整,并不需要委員會在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的情境下提供評估,更不需要產生新的見解作為回應。這種機械的年度董事會戰略進程,缺陷是普遍的。于是,該公司董事會放棄了年度的例行流程,代之以更加深入、但無須頻繁的參與形式——大約每三年進行一次,同時還在每次董事會會議中投入一些時間,根據進程和關鍵指標的變化對戰略進行壓力測試。
某個傍晚的董事會會議室里,全球基礎設施行業一家龍頭公司建筑業務的負責人坐立不安。具有行業背景的一位董事對其所作資本回報率預測的前提表示質疑:這一行業設備的租賃比率(相對于自有)將保持相對穩定。董事會主席似乎也對持續性的假設充滿信心,這一持續性將影響競爭環境和財務業績。但那位董事不以為然,“以我的經驗,租賃比率將隨著經濟周期不斷變化,我認為如果考慮到那些確實已在發生變化的要素,整個評估會合理得多。”
一種不安的沉默籠罩著會議室:董事會成員的觀點非常重要,但其他董事似乎不夠熟悉該行業的變化與經濟狀況。最后,董事長總結道,“約翰提出的問題,不僅對我們的建筑業務,甚至對我們的整個戰略都很關鍵。所以,我們不打算今天解決這一問題,但必須確保在場外的戰略會議上得出結論。”他同時讓CEO將這一議題知會某些優秀員工。
當公司董事和高管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時,這種令人不悅的談話在全球很多公司的董事會會議上,變得越來越普遍。確保公司戰略成功,是董事會的重要職能,也是衡量其掌舵能力的最終標準。然而,新的治理責任與快速變化的競爭環境,需要更深、更好的董事會戰略參與,但大量公司在這一問題上受到普遍挑戰。
董事會的多重戰略挑戰
對入門者來說,時間安排就存在問題。大多數董事會每年召開六至八次會議,往往難以超越合規性相關話題,而確保規劃戰略所需的喘息空間。最近對董事會成員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他們通常將額外的時間花費在兩三個挑選的戰略上。另一個相關調查結果是:44%的董事認為,他們的董事會只是在審查和批準管理層提出的戰略。
為何參與如此有限?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專業知識差距:只有10%的受訪董事認為,他們完全理解其公司經營所處的行業動態。其結果是,只有21%的人聲稱對現行戰略有完整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董事會成員(注重長期)和頂層高管(注重短期)之間存在著視域的不匹配,缺乏協同可能削弱董事會原本在有效信息交流中戰略決策的能力。一家亞洲鋼鐵企業的CEO說,“我們的董事長已有效履職了十年,而我只能算三年。如果我拿出看似超越當前周期的戰略,肯定不會出現超過我期望的結果。我應該為創造長期股東價值和他并肩工作。但我應該如何完成這項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近期一項研究表明,涉及資本重新分配的積極、重大戰略舉措,相比被動的舉措,能夠提供更高的長期股東回報率;但在不足三年的短期內回報率較低。
還有一項挑戰是,經濟加劇波動促使許多企業重新思考他們的戰略節奏。因此,戰略制定變得日益非日程化、非程式化,越來越像一個涉及董事與高管之間的頻繁、定期對話的“征程”。為了保持聯系,董事會必須在這一征途上加入到管理層中來,同時管理層必須帶著董事會前行,同時避免出現混亂,或者演變成更糟的“影子管理”。
轉變,從三個問題開始
那家全球基礎設施行業的龍頭公司有這么幾個主要業務單元:建筑、水泥制造、基礎設施項目所有權和經營權(主要是電廠),以及剛剛起步的房地產業務。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該公司積極在新興市場擴張,直到亞洲金融危機迫使其拋售一些風險較高的資產,并促成了一家大型機構投資者基于基礎建設長期利益的股權投資。經過幾年的巨大成功和持續波動(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該公司的增長陷入停滯,從而觸發了董事會對公司戰略的一次徹底審查。
董事長與CEO討論了這件事,一致認為公司不得不采取新的路徑。一些董事會成員是新任的,尚在努力應付管理一家復雜的跨國、跨行業公司常存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有幾個基本問題被擱置了,這些問題本可以引發一次完全成熟的重組和改造(涉及分拆部門、資本重新分配到新的領域)。
通常的年度戰略調整,并不需要委員會在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的情境下提供評估,更不需要產生新的見解作為回應。這種機械的年度董事會戰略進程,缺陷是普遍的。于是,該公司董事會放棄了年度的例行流程,代之以更加深入、但無需頻繁的參與形式——大約每三年進行一次,同時還在每次董事會會議中投入一些時間,根據進程和關鍵指標的變化對戰略進行壓力測試。
正如該公司所做的,當沒有萬全之策能夠引導公司行動時,董事會成員及高管不妨問自己三個簡單的問題,以便提高參與的質量,并確定為達到目標應采取的實際步驟。
1.董事會是否足夠了解行業動態
多數董事會會議將大部分戰略決策時間用于審查計劃,但只有相對較少的董事覺得,他們對自己公司運作所處的行業動態、甚至公司本身創造價值的方式有全面理解。要解決此問題,同時避免膚淺,董事需要時間——有時需要沒有管理人員在場,這樣他們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業務的結構、經濟狀況以及如何創造價值。他們應利用這段時間提前領會這些問題,而不能總在戰略對話中落后一步,或一味接受管理者的偏見和他們根深蒂固的思維成式。
該基礎設施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從研究業績開始——僅僅聚焦于跨經濟周期的投資資本回報率,然后研究影響投資資本回報率的所有價值驅動因素。而管理層總是耗費大量時間在收益增長和利稅前盈利上——這兩個指標雖然重要,但只能片面地反應公司的整體表現。董事會通過獨立會議、兩次與CEO的正式討論,為戰略管理的后續對話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結果表明,那位對建筑業務的設備租賃自有率假設表示質疑的董事會成員是正確的,不只該業務如此,其他大部分業務單元也是如此。這就意味著來自建筑業務比來自水泥業務的預測回報更高、更持久,但水泥業務有著較高的利潤、也更容易被理解,同時總體規模更大。這一觀察使董事會對所有這些業務單元都有了近距離的認識,同時更全面地評估建筑業務單元的項目管理人才隊伍,優良配置有助于熨平波浪起伏的風險曲線。
2.在對某一特定戰略進行討論前,董事會、管理層之間是否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由于對行業及公司狀況有了基本認識和清晰理解,董事會處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上與高管開展更有意義的對話,最終幫助他們更加靈活地準備、更精準地提供戰略備選方案。董事會成員應以股東的思維定式來進行這些對話,以達到幫助管理層通過考慮新的、甚至意想不到的觀點來拓展其思考。
在那家基礎設施公司,這樣的討論是董事長發起了。他說,“到目前為止,我發現評估行業和公司經濟狀況的過程很有啟發。這使我想知道:如果一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打算立即執掌這家企業,他們將怎么做?”這一問題的破壞性本質顛覆了討論框架,從“我們還能對這些業務做什么”變成“我們是否還應該做這項業務”。它使大家認識到,水泥業務要求公司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競爭力水平——這一水平實際上也不太可能通過有機發展而達到。這一認識最終引致這家基礎設施公司剝離水泥業務。
在這種討論中,管理層的作用是導入關鍵內容:對競爭對手、可能會影響業務的關鍵性外部趨勢詳細審查,以及對公司可運用的、使自己脫穎而出的特殊能力進行評估。對話的目標在于,對公司可用以產生強勁回報的技術、資源,延伸出更深入的、分享式的理解,而不僅僅是隨波逐流。
但還有一點很重要,這類對話暫不應做出戰略決策,那是下一步驟的任務。
3.董事會和管理層是否對每一個戰略選項都進行了討論和落實?
董事會和管理層之間對于商業、經濟狀況以及競爭的活躍討論,往往以爭議結束。隨后,CEO和高層團隊制定一個計劃,然后提交給董事會審批。這是通常情況。其實,管理層可以花一點時間,制定一系列有力的戰略選擇,然后這些戰略選擇,被帶回董事會上討論和決策。
那家基礎設施公司,實際場外戰略會議,在兩天中舉行,以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完全集中于對戰略選擇及相關資源分配進行討論和決定。在各種辯論中,兩個選擇脫穎而出。一是,是否減少公司最具潛力的業務——建筑業務中的人才和資金,以分配在兩個高潛力市場以并購為主導的整合計劃中。另一個是,是否退出房地產業務。董事會和管理團隊都相信必須就此問題進行一番清晰的對話,因為它們在很長時間內已成為一種莫名的不安的來源。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有意義、高質量的強制性談話富有挑戰,特別是當董事會不習慣運用這種方式,并對董事長組織討論的能力有較高要求之時。建構參與過程和協同動力,同時保持有益的緊張度是至關重要的。此外,董事長既不能壟斷討論,又必須有力制止各種沒有意義的跑題。
在那家基礎設施公司進行場外會議的最后一天,董事會和管理層花了一些時間討論了如何進行執行監督的問題,這引導了關于“什么時候需要做好什么”的有益協商。該公司還創造了探討資源分配這一最終議題的時機,以確保做出決策后沒有人被遺忘。那位有行業背景的董事還向CEO闡述了路徑依賴、資本人員的調配及高級的行業周期曲線等。
將戰略選擇的討論延伸至執行監督的議題,是有力而不尋常的一步。通常,這并不是必然的。但董事會有時會忽略,高管要調和董事會及自身所做的深刻改變的承諾,與耗費著管理層日常經營的時間之間的矛盾,是多么困難。這時常是場外戰略會議意想不到的結果。如果戰略會議在財年末召開,就很難保證在年度預算被審核之前有足夠的時間來充實這些計劃、在關鍵業績指標之間建立聯系。
戰略規劃通常很復雜,而隨著董事會更深入的參與,又變得更加不易——它引入了新的聲音和專家們的爭論,并帶來了管理團隊和同樣想尋求最佳答案的董事會之間的緊張感。然而,這種方式的戰略規劃在順利完成后,其價值是難以估量的。它不僅會引發更清晰的戰略,還能促成更大膽、更具信心的戰略舉動,并始終保持資源得以投入到關鍵決策的協同效應。
(麥肯錫)